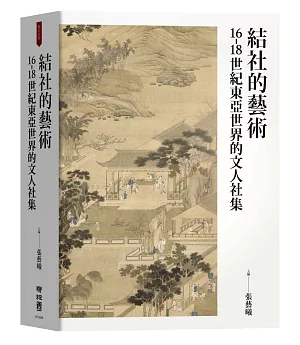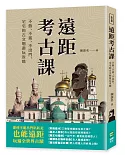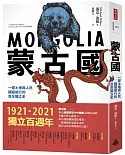序
幾年前,藝曦來研究室找我,請教我關於編論文集的事,他當時計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王昌偉、許齊雄教授,以及台北大學的何淑宜教授合作,以文人社集為題,集合眾人之力來編論文集。他當時問我,此時此刻是否仍適合編論文集,以及這類論文集對學界是否能有貢獻,而這是他最關心的部分。我當時建議藝曦,必須堅持幾點:論文集的主題必須明確,每篇論文都必須圍繞這個主題提出各自的創見。
在過去幾年間,為了讓各篇文章作者能夠聚集一起開會討論,他們先後申請蔣基會與科技部的經費補助,兩次會議的舉行也得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呂妙芬所長的協助。為了能夠有更充裕的時間寫作論文,他們把時程拉長到三年,且在著手進行之初,分散各地的成員也不辭路遠,來台共同討論,直到今日,終於有論文集的問世。
這本論文集以16到18世紀的文人社集為題,時段集中在明中晚期及清初。明中晚期的社集活動十分精采而多樣,而經歷明清變局以後的清初社集的性質與活動也很值得探究。當時社集活動盛行的程度是很難想像的,清初順治皇帝還曾特別關注近來名流社會,並說慎交社「可謂極盛」,提到孫承澤是「慎交社」中的人物(《清稗類鈔》、《雲自在龕隨筆》等書)。在進入清朝之後,仍有黨社中人,希望透過新朝的力量打擊對方。
這本論文集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不少文章都能夠不受限於社集這個主題,把社集放到整個時代大脈絡下,從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文化轉型等面相切入,讓原本看似平凡無奇的社集顯出獨特的意義。
這些文章,有的談社集跟地方官員的到任去職的消長關係,顯示某些看似宴遊的詩社,也可能有實質的政治意涵與目的。有的討論社集與地方家族的聯繫,有的利用大量族譜資料說明不同性質的社集與地方人際網絡、家族生態的關係。也有的注意到社集與城市空間,以及明末文人藉由社集展演的取向。另有幾篇是談社集與詩派、與八股文、與經學風潮的關係,這些看似傳統的題目,但都能夠得到讓人耳目一新的結論。另有一篇談明末及清初的士風之別,在此變局中的文化轉型是很值得深入的課題。另有兩篇文章,則是將眼光擴大到與士階層密切相關的其他階層或領域,包括醫者及書畫鑑賞。過去我們雖可多少看到一些醫者結社的資料,但藉由這篇文章,才讓我們了解到醫者與文人社集之間有那麼密切的關係。
這些文章各有主題,也跨越不同地域,除了南北兩京、揚州,以及浙江等地以外,還有江南以外的江西、福建、廣東等區,展現這個團隊廣泛討論各地社集的企圖。另有兩篇關於日本與越南的社集的文章,亦顯示這本論文集對東亞周邊各國的關心,而且從更多元也更整體的眼光,以中國為中心看整個東亞世界的社集發展。
我在多年前寫作過幾篇明代思想生活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幾篇文章跟明末蕺山學派及清初講經會有關,當時我注意到明末出現不少以經、史或讀書為名的社集,這類名稱的社團在此之前很少見,但在明末卻大量湧現,而且不少都很有影響力,像江南的復社、浙江的讀書社都是很好的例子。對於這類社集的出現,我認為這與經史之學,尤其經學的復興相關。不過,近幾年我有更進一步的觀察,除了心學以外,至少還有文學復古運動等各種思潮條件共同促成。尤其是文學復古運動,由於主張必須臨摹古代的詩、文,進而蒐羅古代典籍,所以對古籍的刊刻流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方面,這個運動雖然倡導復古,但所復的不限於儒家經典,所以相對於之前的學風帶來了解放。復興經學則是到了明末才正式提出的,所以我們必須認真看待明末經學的復興,它有其時代的特殊意義,而且帶來的影響極大。
以此為例,我們在討論明代中晚期及清初的歷史,必須用更宏大的眼光談。我很喜歡「察勢觀風」這個詞,當某個風潮起來的時候,就像是一陣風吹拂而過,一個時代的各方各面、或多或少都會受這股風潮的影響,而且往往是多層次也多方面的交互激盪,來回往復。若是遇到像明清之際的大變局時,這類變動會更加複雜。研究者有必要察其勢而觀其風,除了所研究的對象以外,還必須把研究對象所處的風潮及各種動盪變化都一齊納進來討論。此外,歷史的發展往往會有不同力量同時在競合著,所以社集不會只是社集,而會跟這個時代的其他因素結合發酵,也可能彼此排斥,但即使是排斥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這本論文集所做的可說是一種「察勢觀風」,而且把社集放在時代脈絡中查考,作者們能夠以更全面的眼光掌握所研究的課題。如今論文集分別在兩岸出版社出版,讓人為這本論文集對明清之際社集研究有所貢獻而感到欣喜。
王汎森
導論(節錄)
16、17世紀,即中國的明代中晚期及明清之際,各地以士人為主,成立許多大大小小的社集,在此之前雖然也有一些社集的記載,但在數量上都沒有這段時期多,於是吸引不少研究者的關注。過去的研究較偏重在江南一帶的社集,復社的活動尤其受到注意。江南的文獻極豐富,社集的相關資料亦多,加上復社有確定的成立時間、目標與宗旨、成員,以及社集的活動,所以復社及其周邊社集,諸如幾社、讀書社、南應社及中江社皆為人所熟知,而其詩文活動或政治運動,始終是學界的研究重點所在。相較之下,其他地方的社集往往只有很零碎或極片段的資料留下,造成研究上的極大困難,即使近幾十年仍有一些精彩的研究論著問世,但資料的稀少與零碎,仍是研究者所須面對的困境與難題。
社集是一群人的集合,像郭紹虞便把社集定義為文人集團。社集跟個別士人或文人不同,個人可以有很多面相,但當一群理念相近的人共同結為社集,便在某方面有所交集,而被凸顯的這個面相便會成為該社集的特色,當同一類的社集在一段時期大量出現,便可能跟某種思想文化風潮有關。也因此社集不只是社集,還必須跟社集所處的時代脈絡及其思想文化風潮放在一起考慮。
明中晚期思想文化史領域的三股風潮,分別是以前後七子為首的文學復古運動、陽明心學運動,以及以江南復社與江西豫章社為首的制藝風潮,因應這三股風潮,則有詩文社集(主要是詩社)、心學講會,以及制藝文社的流行。明中期是文學復古運動與陽明心學運動的興盛期,於是詩文社集與陽明學講會臻於極盛,直到萬曆末年左右,聲勢才被新興的制藝風潮與制藝文社所凌駕而過,迄於明亡而止。
文學復古與心學運動在詩文及心性學說上各有主張及創獲,而兩波運動的共通點,即帶來參與階層的擴大。心學普遍流行於一般士人之間,而因心學有向下層走的傾向,所以即連布衣、處士、農工商賈也有不少參與講學的例子,這方面以泰州學派走得最遠,但不僅限於泰州學派有此傾向而已。文學復古運動也有擴大參與的趨勢,復古派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原則,由於講究摹擬,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於是過去被視為雅的詩文,如今吸引更多士人,甚至布衣、處士、宗室、僧道,共同參與在這類詩文社集中。
參與階層或範圍的擴大,使得這兩波運動並不只是停留在心學學說或詩文寫作,而有其外在效應。近來的許多研究指出,在心學流行高峰的一世紀間,心學對許多規範的鬆解,給予多元的價值發展空間,脫離過去來自官方或程朱學的約束規範。還有許多人利用講學講會以及各種策略手段,進行社會教化或社會福利事業,而讓儒學的聖人形象具體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如錢基博所言,文學復古運動頗類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因對古代文化的嚮往而蒐獵古代典籍,加上明中期以來出版業的興盛,使得許多已知或未知的古籍得到刊刻出版的機會,過去珍貴而罕見的古籍,變得唾手可得,人們所閱讀的書籍大量增加,知識範圍也大幅擴大。許多古籍的重刻流行,加上心學訴諸本心而不受先儒註解的約束,使得人們對儒學經典的解釋多元化,而儒經以外的其他典籍的流行,甚至弱化了儒經對人們的規範能力。諸子學的復興就是此時很值得注意的現象。當時流行的諸子學書籍,除了《老子》、《莊子》以外,還有先秦以來的其他子書,不少人會以這些子書來重新解釋儒學經典,隱然把諸子學與儒學並列,甚至有凌駕儒學之上的傾向。也因此,在心學與復古運動流行的高潮,也是一些人對這兩波運動批評最激烈的時候。理學陣營既有周汝登與許孚遠的九諦、九解之辯,也有以顧憲成(1550-1612)、高攀龍(1562-1626)為首的東林書院講學,主張回到官方認可的程朱學。文學陣營有公安、竟陵先後起而批評復古派。
不過,儘管許多士人都捲入到這兩股風潮中,但畢竟大多數人都不是嚴肅的心學家或詩文作者,所以即使精英士人倡導回歸程朱學或主張性靈文學,也未必能夠徹底解決儒學經典解釋的多元化及規範弱化的問題,這給了制藝(即八股文)發展的空間。在心學與復古派流行的高峰期,制藝只被視為是一種寫作的技巧,並未被賦予多少文學性,所以無論是心學或復古派的士人,都把心學、詩文跟制藝區別開來,甚至頗有醜詆制藝的言論。但大約到萬曆中期以後,開始有一股新的呼聲,試圖把制藝作為新文體,以這個新文體重新整頓風氣。
制藝即經義之學,亦即對儒學經典的義理詮釋之學,明末士人沒有直接走入清代的考證學,而是以制藝來解經。由於先儒如朱熹對儒經的註解,雖然簡要精當,但未必能夠傳達儒經的全部意涵,所以必須以各種旁敲側擊的方式,一邊回到儒經當時的時空背景,一邊放到今日所處的時空下來思考與理解其內容。如果說朱熹的註解是骨幹,則當時士人透過制藝寫作所想做的,便是賦予這些骨幹豐富的血肉。也因此,明末士人所從事的制藝寫作,既是因應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衍生的挑戰而起,但從經典解釋的角度看,又是承自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而來。所以當時一些人甚至要求制藝必須融合理學與文學的成果,一如江西新城涂伯昌指出,今之士人與昔之士人的差異,在於理學已明與理學未明,而在理學已明之世,士人除了明理以外,尚須具備文學修辭方能完美闡述經義。因此,制藝雖以闡釋經義為主,但同時也是經學、理學與文學的三合一。
詩古文辭、心學語錄與八股文,本屬於不同文體,與此相關的士人及社集活動,過去會放在各自的文學史、心學史及八股文史的脈絡下進行討論,但在心學、文學復古與制藝寫作這三股風潮中,不同性質的社集間常有競爭關係。對個別士人而言,心學、復古派文學與制藝三者間不必是競爭關係,所以某些士人可以同時跨在不同陣營,既接觸心學,也同時寫作詩文與制藝。但若是組成社集,社集會凸顯群體共同的認同與作為,就必須放在三股風潮的競合中來考慮詩社、心學講會及制藝文社。一如18世紀的法國,既有貴族女性主持的沙龍(salon)聚會,也有Baron
d’Holbach組織的以男性為主的聚會,儘管成員有重疊,但兩種聚會間卻有競爭關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