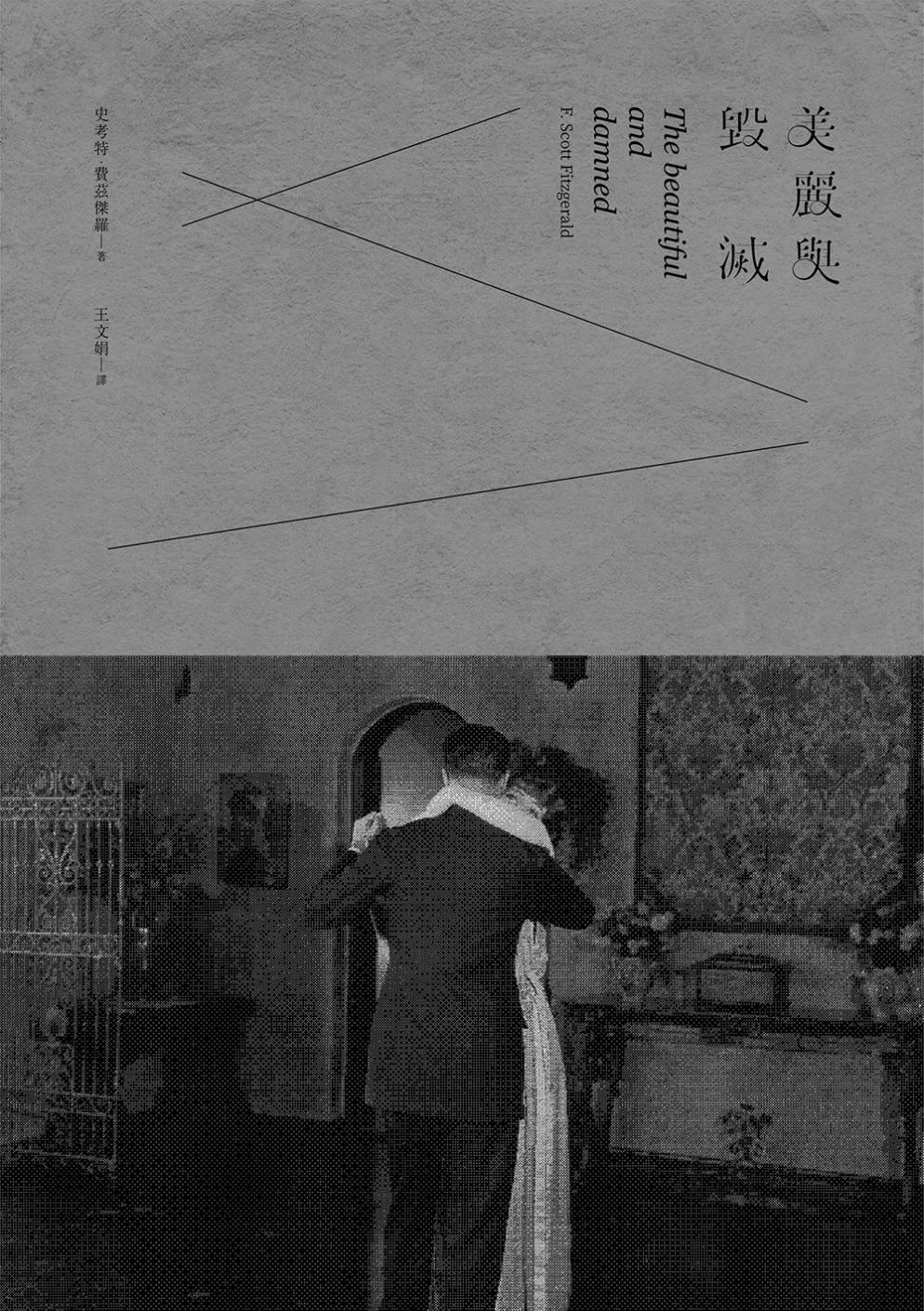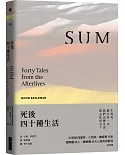推薦文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政大新聞系助理教授 柯裕棻
人人都說費茲傑羅的小說寫的是「美國夢」,他代表「爵士時代」的浮華金粉,他筆下的年輕人美麗而且浪蕩,狂舞如同華燈之下的飛蛾。仔細探究他小說長存的主題,更會發現,美國夢的背後是無比的失落、悔恨、不斷的破滅和錯過。故事表面是榮華富貴的晚宴和空談,故事背後則充滿了噬人的現實。乍看之下,金錢彷彿像打水漂兒的石頭那樣,扔進水裡去了,美麗優雅的人物浪擲千金只為了愛情,愛情可貴,金錢可拋。然後,漸漸地,愛情在人生裡蹉跎了,消失了,銀子仍然水一樣地流淌出去,這時一切都更卑微了,像水一樣從手中滑失的,除了金錢、愛情之外還有似水的流年。
費茲傑羅的小說裡,年輕的愛情與人生是甜美又黏膩,像冰淇淋,若不及時大啖一口,只怕它在現實的熱度裡融化了,流了下來,沾得滿手都是,非常困窘,非常不堪,於是開始心生厭惡,想拋開,想找東西擦手,忘了曾經多麼渴望這個滋味。或者,吃著吃著,心裡著急了,於是貪婪大口吃下去,吞嚥手上的一切,來不及明白那味道,來不及記清楚,然後就什麼也不剩了。追求過的,幾乎到手的,原來都遙不可及,買不到,留不住。
將這個感覺寫得淋漓盡致的人,究竟有怎樣的人生呢?
費茲傑羅是個纖細而且敏感的美國中西部小孩,他出生於中西部偏北的明尼蘇達。可能因為如此,他筆下鮮明的前台一定是東岸的紐約大都會,笙歌處處,極盡虛榮之能事,但是中西部卻始終是他小說的重要背景。那種重要性幾乎是先行成立無庸置疑的,他對此背景著墨不多,可是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必定有一個位於中西部的老家。
中西部在美國文化的想像上,始終是個不可忘卻的圖像,這個遼闊的平原是美國之心,是想像中穩固美好的家園,孕育大無畏的肥沃夢想,這裡有非常傳統的美國價值觀,有清教徒習性的規律和秩序。生長自這樣的土地,費茲傑羅滿懷夢想來到東部就讀普林斯頓大學,二十四歲寫就的第一本書《塵世樂園》(1920)就揚名立萬,一夕成名後,如願與滿立的法官之女賽爾妲結婚。兩年後寫出了《美麗與毀滅》(1922)。二十九歲寫《大亨小傳》(1925)。五年後,妻子精神崩潰進了療養院,他自己也因酗酒而精神崩潰。三十八歲寫了另一個長篇《夜未央》(1934),不受好評,從此一蹶不振。四十四(1940)歲死於心臟病,幾年後他的妻子也在療養院中葬身火海。
果然是這樣的人生,美麗與毀滅。濃縮的,不遺餘力的,放縱的才華和毀滅的慾望,一路從雲端跌落深淵。
海明威曾在巴黎遇見費茲傑羅,並且寫過關於費氏夫婦的文章。當時費茲傑羅已經頗有名氣,並且為雜誌寫商業化的稿子,以賺取稿費。在海明威眼中,費茲傑羅長相秀氣略有倦容,但是非常神經質,他的妻子賽爾妲則是活潑美麗,有一雙鷹眼,據說費茲傑羅夫婦不斷喝酒,舉止乖戾,經常醉醺醺的,海明威當時認為,費茲傑羅如果再這麼放蕩下去,恐怕再也無法清醒,再也寫不出好東西來了。事實上,海明威幾乎說對了,費茲傑羅一生之中寫了上百篇短篇小說,但是長篇小說僅有四部半,最後力圖振作的一本沒寫完就過世了。
費茲傑羅曾經說他自己寫的故事,看來是關於東岸紐約浮華世界的眾生,但骨子裡是中西部的故事。隱藏在他記憶裡那片嚴寒的冷漠的大地,融化於白雪中的童年,造就了他畸形的人格,也使他對浮華世界不適應。他眼裡的東部既是觥籌交錯,又是鬼影幢幢而且黯淡荒謬,充滿墮落的可能。他這麼說,無疑是個很大的反諷,他因為不適應這樣的繁華,所以浪擲青春,揮金如土,一個來自中西部的小孩在花花世界裡迷失了,可是他再也不能夠像從前那樣,搭上火車就回到松柏長青的家園。隨著現實的逼近,塵世樂園已然失落,誰也不能找到安逸的故鄉與極樂的未來。
有人從費茲傑羅三十歲之後寫不出好作品這個狀況批評,認為他只是個運氣好的傢伙。可是他二十幾歲寫的這幾本小說,已經呈現一個精密複雜的世界,有深刻的情感和隱隱的不安,面對這個世界冷酷的鐵則則顯得慌張,彷彿預見了自己的下場。他筆下的人物不少來自他自己的人生片段,他的女主角幾乎都是他深愛的妻子的翻版。如此,則更令人心驚了,他的作品自傳色彩濃厚,卻代表一整個時代,他寫的都是幻象與破滅,卻被認為是美國夢的作品。他人生後半潦倒,人們記得他的永遠是「爵士時代」的繁華放浪。
這是多麼詭詐的人生巧合,一如他筆下的故事。一個天才就這麼折損了,人生就這麼過去了,令人感嘆,也不知道是他的筆活出了他的人,還是他的人成就了他的筆。
人間墜落:陷溺的青春年華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蔡秀枝
當超越世間的美墮入塵世轉而成為人間佳麗,當閒散的紐約上流社會貴公子安東尼.派屈遇上心儀的美麗女子葛羅莉亞.基爾柏而終成眷屬,當夢幻與浪漫的仙境逐漸變成日常生活中撙節的採購與入不敷出的財務壓力,陷溺終於成就了《美麗與毀滅》(1922)裡青春年華的輓歌主題。在費茲傑羅繼《塵世樂園》(1920)後出版的第二部小說《美麗與毀滅》裡,璀璨的社交光影與酒宴中淺薄對話的堆砌鋪就了吸納生命光彩的華美殿堂。這個虛空浮華的殿堂吞噬財富並燃燒生命。日日流連酒宴派對的安東尼與葛羅莉亞夫妻除了盡情燃燒青春與財富,也在他們華美流年漸逝的灰暗日子裡,經歷某些慌張、驚懼的時刻,深刻感受過生命裡的陷溺與恐怖威脅,雖然他們生命之歌裡的陷溺總是被他們所逃避、以別的概念來置換、或是在彼此或深或淺的清晨懺悔裡被掩飾、隱藏、甚至假意遺忘。
臨淵陷溺
費茲傑羅《美麗與毀滅》一書裡最大的成就是在於他以一種令人心驚的、具有衝擊性與毀滅性的、既真實又虛幻的經驗書寫(例如:安東尼的慣性酗酒和葛羅莉亞的夜半驚夢),來描摹刻畫美與陷溺(做為毀滅的先驅)的拉扯。在費茲傑羅的筆下,生命猶如一段瀕臨深淵的旅程,藉由因欲望而生的陷溺這個巨大的漩渦將美吸納、麻痺、淹沒、甚至摧毀。
在第一章「安東尼.派屈」裡「天堂的回憶片段」這個小節裡,費茲傑羅摘錄呈現了一段「美」與「聲音」的對話。此時每百年會重生一次的「美」正在等候室等待她的再次重生。「她美麗的身體便是她靈魂的本質」,這是費茲傑羅對於美的描述。而藉由葛羅莉亞這位美麗的女子,費茲傑羅將超越的、屬於抽象概念的美與形諸人間的、物質的、肉體的美具型化。葛羅莉亞是個美麗佳人,她對於自身形貌的美麗有著全然地自知與自信。美麗是葛羅莉亞據以傲視並睥睨一切的前提,而青春則是承載她的美麗的基底。她相信美麗將會為她贏得浪漫的愛情、無憂的婚姻與富裕安全的一生。
然而對於安東尼來說,葛羅莉亞的美是一種人類經驗裡的恆久存在,如太陽般耀眼、聚集並散發光與熱。即使葛羅莉亞的一個眼神,或者僅是她口中的一個句子的片段,都有著魔力能夠讓他因此看到美所綻放出的某些光芒,「使他目眩神迷於其中所有的美麗與幻象」。她的美彷彿在一瞬間照亮他—於是僅只一瞥就能成就他心中的一念永恆。對於安東尼這個把大把日子都消耗在酒館、飯堂、公眾或個人社交場合裡各種可能的逸樂的清貴上流知識人(哈佛畢業生)來說,葛羅莉亞帶給他的感動與浪漫情懷遠遠超越了對肉體的欲望。葛羅莉亞的美是超脫世俗的、非人間的永恆。她是他的救贖。
但是這個精神的救贖,最終仍是失敗了。安東尼因為自己種種的不成熟、懦弱與逃避,將她一次次傷害,最終將她折損陷溺在空有財富但青春已逝、浪漫愛情皆無、又不受丈夫敬重的婚姻境況裡。這樣一個失去美好青春、必須漂染頭髮(因為過去金沙偏紅的頭髮已經變成沒有光澤的淡棕色),而因此看起來有些骯髒不潔的葛羅莉亞,為了後半生的經濟來源,而必須陪伴坐在輪椅上精神有些失常的安東尼。
其實在安東尼初遇葛羅莉亞時,他就已經瞭解他自身問題的所在:他軟弱、沒有勇氣、害怕孤獨、無所事事、並且沒有任何成就。他批判其他人的平庸,想像自己是心智清晰、老練而才華洋溢、是一個憑藉著祖父的財富建立起顯赫地位的重要人物。但是他內心其實是非常焦慮的,因為他擔心他可能沒有任何天份、僅是個凡夫俗子、甚至是個傻瓜,而更可悲的,可能要「靠雞尾酒來建立他的事業」。安東尼沉迷於飲酒的習慣最終導致他人生的沉淪與陷溺,而陷溺的導火線的最初引爆,就讓葛羅莉亞對他由愛生恨。事情的發生是在某個夏日,安東尼整個下午都只是閒坐在馬利安家喝威士忌,之後葛羅莉亞堅決回家,執意將安東尼從與馬利安的對飲中拉走,後來又在離開馬利安家的路上拒絕讓他去另一位友人家續飲。這舉措讓安東尼向來懦弱的意志力有了極大的反彈。安東尼認為他的快樂被葛羅莉亞的自私所剝奪。而為了要宣示他作為丈夫、她的主人的權力,他因而在火車站台上對葛羅莉亞謾罵與惡意動粗,以阻止她坐上火車回家。火車站這凶暴的一幕讓葛羅莉亞對他的愛產生了變化。雖然安東尼希望藉此折損葛羅莉亞的意志與驕傲,但是卻只是折損了她對他的愛,讓她更加痛恨他。從此之後,酒精作為交際、歡樂、與麻痺神經之源,取代了美的光與熱,成了他內在無法拒絕的欲望,因為酒精是他拒絕面對人生的避難所。安東尼終究是無法藉由葛羅莉亞來改變或提升他所認定的「無意義的人生」。相反地,經由婚姻的結合與婚後生活的實踐,安東尼在他無意義的人生裡的種種逸樂與饗宴飲酒,再加上葛羅莉亞對物質與流行元素的需求與歡樂、富裕、美麗人生的夢想,讓他們的生活漸入黑暗,迭起爭執,終致陷溺毀滅。
安東尼的無所事事與夫妻倆無止盡的派對飲宴,不僅逐漸掏空安東尼父母遺留給他的財富,也使他們的生活慢慢變形。他們害怕孤獨,也無法在家中兩人獨處,於是出門、看音樂喜劇、與無趣的朋友用餐飲酒就成了他們為了解救無趣人生與無聊婚姻生活而不得不進行的活動。他們瘋狂的飲宴、參加或召開派對讓年老的亞當.派屈祖父大失所望,因而拒絕讓安東尼繼承他的遺產,而爭奪遺產的官司訴訟則讓他們窘迫的財政更加惡化。安東尼雖然被迫勉強去工作,卻都無疾而終。他藉酒精來躲避人生,掩飾懦弱,然而酒精也是造成他失去葛羅莉亞的愛、失去祖父千萬財產的繼承權、讓他的生活無以為繼的肇因。酒精是安東尼生命裡的陷溺之所,然而他在接受徵召令入伍後,與營區附近的桃樂絲.瑞克洛福特(多蒂)的這段戀情,更是他對於浪漫愛情、婚姻與美(葛蘿莉亞)的背叛,是壓垮他神智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法院宣布他遺產官司審判結果的那天下午,多蒂尋到他紐約的寓所,安東尼終被狂怒與凶暴吞噬而發狂。
青春為舟
在《美麗與毀滅》裡,葛羅莉亞少女時期的愛情與婚姻觀是猶如一朵兀自綻放的花:驕傲而自我,為存在而存在。葛羅莉亞在日記裡表白:她的婚姻將是以世界為舞台而演出的一齣華美而動人的戲劇,但是也因此她堅決地表示她的生命是絕對不會用來孕育與繁衍下一代。青春是葛羅莉亞的美的載具,而衰老或任何會玷污或褻瀆美或威脅青春的東西都是她生命裡的陷溺與毀滅力量。
葛羅莉亞是在一次瘋狂派對中似真似幻地經歷了一場恐怖的暗夜威脅。那是發生在他們租下的位於馬利塔的灰屋裡,當時樓下的醉鬼正喧鬧著,她躺在樓上的床上,窗外風雨與閃電交織,之後是恢復平靜後溫柔的雨滴和輕拂過葡萄藤蔓間的風,她在半睡半醒間感受這兩股力量的勢均力敵,然後被一股慾望糾纏,胸口窒悶壓迫卻無法掙脫……她只想要在破曉的陽光下貼近她逝去的母親,因為她的母親站在世界的中心、風雨的中心,既安全、又溫暖和強壯……但是她卻又突然全身僵硬彷彿感知到有人(被她的表哥理查.卡拉美帶來派對、不明來歷的陌生人豪爾)站在她的房門邊靜靜得注視著她,她的週身因此充斥著恐怖與不潔的威脅。
如果安東尼無聊、無意義的人生裡滿是他對自身能力的懷疑與畏縮,因而踏上酗酒與背叛愛情和婚姻的悖德之路,那麼葛羅莉亞的悲劇人生裡的陷溺與毀滅,則是實際環境裡流行的、豐富物質享受的缺失,和屬於男性粗暴的、對於美的精神性與肉體性的侵害與威脅。唯有棄離滯悶壓抑的狂飲派對、回到世界的中心、回到母性溫暖安全的空間,葛羅莉亞才能避免男性對她的環伺威脅與傷害。灰屋裡這個夢境與實境相參的經驗,預示了葛羅莉亞的實際人生將在這兩種勢力的壓迫與交纏下成長。葛羅莉亞從一個婚前沒有任何家事經驗的少女輾轉變成努力撙節經費購買食物的三十歲女人。因為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她只能在安東尼的語言、情感、甚至身體暴力之下,強力支撐自我意識,以與之抗衡。她有美貌與社交能力,但是並沒有智識、經濟或專業上的能力。她早先曾想讓布洛克門安排她演出電影裡的一角藉以開闢家庭財源,但是卻被安東尼阻擋。當她終於再次拜託布洛克門而獲得試鏡機會時,卻黯然發現二十九歲的她已經青春不再。
葛羅莉亞的美曾讓安東尼為之迷戀,但是這充滿妒意下的迷戀僅只彰顯了父權體制下的男性對女性的擁有權而非愛與尊重。在家庭經濟已經十分困窘之下,安東尼依舊跑到小酒館買醉,當他下意識想找以前的情敵布洛克門借錢時,竟藉酒發洩妒意並與布洛克門扭打。在人生的深淵上,結婚七年之後三十三歲的安東尼失去了他青春、智力、財富與健康,只能在酒精的迷醉下在公共場合無理取鬧與行使暴力,陷溺在人生的漩渦之中而無法自救。當他最終贏得祖父的遺產卻變得精神異常時,葛羅莉亞往日的年輕貌美也早已經因為她波折的人生裡的數度浮沉而失去光彩,那曾經引起安東尼燃燒起迷戀之心的永恆之美,也早已消逝無蹤。
唯有距離能讓美繼續保持其超凡。然而當距離不再、財富驟失、責任被逃避、意志被摧毀、愛戀與婚姻的道德被踐踏時,美麗與青春年華終將一步步瀕臨毀滅。
美麗人生⋯⋯
譯者 王文娟
歷來解讀史考特‧費茲傑羅(1896-1940)的小說,總要拿作者的真實人生來平行比對,而體例介於虛構和自傳之間的《美麗與毀滅(1922),自也不能免俗。就費氏的寫作歷程來看,他的第一本書《塵世樂園》(1920)的暢銷,為他贏得了婚姻;而婚後龐大的上流生活開銷,則促使他提筆寫作本書,以擺脫因負債造成身心日益沉重的陰霾。
費氏似乎有意藉書寫,尋找現實問題的答案。例如,本書的男、女主角安東尼‧派屈和葛羅莉亞‧基爾柏,不論外在形象、教育背景或個性,甚至婚姻問題,活脫就是他和妻子塞爾妲‧賽瑞的翻版。他們的兩人世界猶如一座孤島,一次世界大戰乃至於社會職場的真實鬥爭,都與這對夫妻距離遙遠,只單單透過金錢的管線傳輸養分,這些管線在書中以不同的形象出現,如安東尼有錢的祖父和成功致富的好友墨瑞,以及面目模糊的上流社會人士⋯⋯等,也因此書名的「美麗」,其實隱含著一個極為絕對而一廂情願的假設,那就是財富等同於成功:只有「很」有錢,這對夫妻才能在眾人間活得理直氣壯,稱職地扮好紳士和淑女的角色,並隨心所欲地從事體面工作、旅行和戀愛,這樣,生活才是「美麗」的;反之,若是缺錢,必須時時為金錢而工作,那就是「毀滅」的開始,整個世界都成為一種對立而敵意的存在,成為(被)羞辱、輕蔑、嘲諷的對象,並根本地撼動兩人的安全。因此,祖父遺產的得到與否,成為貫串全故事的針線、男女主角失去青春美貌和不腳踏實地工作的藉口,以及最後的救贖,其中的痛苦和為逃避痛苦的放縱、耽溺於享樂、酗酒、自毀,清醒之後的懺情,皆是費茲傑羅赤裸裸的生活寫照。
既然如此,看待這部作品便猶如看待作者其人,不是去評斷技巧優劣,而應探討他在書寫中呈現的質地為何。費茲傑羅無疑是感性的,屬於擅長描述和抒情的寫作者,特別是在觀察人物、探究戀情的分合悲喜和失落,文字尤為優美而準確。
好比他寫歷經貧窮磨難的男女主角,對重燃愛火的期待,是「愛將如不死鳥,從遺骸中再度重生它神秘而難以捉摸的精魄。」或者是安東尼尚對真愛仍矇懂無知時,無意間看到窗外一個陌生紅衣女子的鮮活想像:「⋯⋯他注視她有好一會,感覺體內似乎有什麼在翻攪,那種無以名狀的感覺,可能源於午後陽光的溫暖味道,或紅色本身具備的狂喜鮮活吧。安東尼一直覺得女子是美麗的——突然他領悟到,這是因為她的距離,不是靈魂的稀有和珍貴所造成的隔閡,而是塵世中真真實實的距離。他們之間相隔的是秋天的空氣、層疊的屋頂,和濁雜的聲音;然而在某個不能理解的瞬間(它反常地卡在時間之流中),安東尼被喚起的情感狀態,不同於他所曾經驗過最深刻的吻,而更接近某種愛慕之情。」
可是,在這麼抒情的字裡行間,卻又同時夾雜著另一個聲音,那是某種世故的裝腔作態,全然以自我為中心,去質疑外在世界與自己的不和諧處。雖然他點名挑戰的知識傳統和社會現狀(多半表現於安東尼與好友墨瑞和狄克的交談),皆為西方文明的一脈相傳,卻很可惜的都流於淺薄,就像遊走於知識名牌的萬國博覽會,缺乏深度,也無法對書中人的生命困境提供解套的可能。或許也就是因為費氏不能準確抓到議論的中心,卻又想要強作議論的能人,便開始在文字上做工,寫出糾纏而語意複雜的長句,這也是翻譯此書最大的難處所在。
當然,這絕非是費茲傑羅獨有的問題,卻是一般早慧而年輕寫作者的通病(本書是他的第二次出手,年紀才只有二十六歲。);而大戰後懷疑一切、及時行樂的時代氛圍(史家稱為「爵士年代」),自也難辭其咎。不過,有一種鮮明的質素,卻自始至終標示著費氏近二十年的寫作高度,那就是他檢視自己的驚人誠實。就像反覆循環的宿醉中難得清醒時分,帶著頭疼、反胃和強烈的自我嫌惡,近乎殘酷地自省和自剖;在八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令人動容,以致於不忍去質問,他的美麗人生因何毀滅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