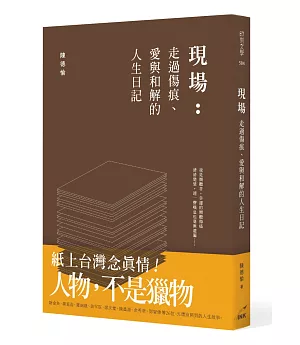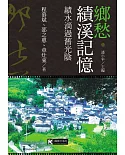推薦序
人魚公主盪小舟看風景
新聞書寫中,人物書寫看似簡單,實則最難。
說它簡單,是因為被訪者就端坐在訪者面前,聽言、觀行、發問一陣子後,一幅略具輪廓的速寫理應不難完成。說它最難,是因為聽、觀、問這三項採訪工作的執行,都涉及底蘊,也關乎技巧;底蘊淺的訪者,可能聽而未聞,或觀而不察,技巧不足的訪者,發問即使再多,也可能一題也切不中要害。
當然,人物書寫的另一難度,與敘述風格有關。一篇好的人物書寫,一定是一篇好的新聞文學,結合了「好新聞」與「好文學」兩個要素;海明威雖然說「搞文學的人當記者,猶如自殺」,但他自己是個反證,新聞文學更是。
一九六○年代崛起的「新聞文學」(Literature of Journalism),之所以至今仍是西方新聞書寫的主流,就是因為當初建構這個流派的人,如卡波提(Truman Capote),如梅勒(Norman Mailer),都有混血身分,他們既是記者,也是作家;他們寫的非虛構紀實報導,如卡波提的《冷血》,如梅勒的《長夜行軍》,都是新聞經典,也是文學經典。
隸屬新聞文學陣營的記者,在採訪與寫作時都特別重視場景、細節與對話,這三者是新聞追求「事實」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文學追尋「真理」缺一不可的要素。當然,新聞文學並非橫空出世的一個流派,它的師承是二十世紀初期的「扒糞新聞」(muckraking journalism)。扒糞新聞雖是調查新聞,但那些專挖「鍍金年代」政商黑幕的記者,卻個個身懷文學技藝,如寫《屠場》的辛克萊(Upton
Sinclair),如寫《參議院叛國》的菲力普斯(David Phillips),皆然;他們因而創造了「揭發文學」(exposure literature)這個名詞,並以此名詞定位他們所開創的新聞書寫類型。
由此可知,在西方新聞史中,不管哪一種類型的新聞書寫,文學自始至終都是形於外的一種技藝,也是藏於內的一具魂魄;即使是在數位媒體當道的這個年代,稍具典範意義的新聞書寫,如「紐約時報」網站幾年前轟動一時的「雪崩」(Snow Fall)專題,仍屬於新聞文學的類型。
反觀台灣,新聞文學或人物書寫卻始終屬於弱勢的書寫類型,大學新聞系所未將其列為必修課程,各類型媒體也鮮少對其鼓勵重視。美國有創刊至今已四十五年的《時人》周刊(People
Magazine),發行量每周約三百多萬本,而台灣新聞界自幾十年前一本「大人物」雜誌旋起旋滅後,迄今缺乏一本以人物為本位的媒體;既沒有新聞文學淵源流長的傳統,也缺乏人物書寫的代代相傳,這就是台灣新聞史的過去與現在。
但所幸在新聞史的邊陲地帶,這幾年卻出現了零星幾點星火,少數記者踽踽獨行,以人物書寫的形式讓新聞報導閃爍著隱隱約約的文學火苗;走在這列隊伍前面的人有董成瑜、房慧真等,踵接其後的就是《現場》這本書的作者陳德愉。她們都是新聞界少數會說故事的人,都有記者的敏銳,都有小說家的細膩,她們寫的那些人物故事都是新聞,也都是文學。
陳德愉剛當記者不久後,就出版過一本小說《一九八七年那條人魚公主》,當時她只有二十多歲,被人戲稱是「九頭身怪怪美少女」,但怪怪美少女其實骨子裡是個叛逆美少女,小說字裡行間顯現的卻又是個滄桑美少女,「終於,我也成為被他們輕視的對象了」,「即使,已經成為被憎恨的大人,即使,知道自己其實是個垃圾,也要努力裝出莊嚴不可侵犯的樣子」,就像陳德愉寫黑嘉嘉那篇文章中的一句話「回憶…就像覆盤」,滄桑美少女對叛逆美少女那個年代的覆盤,結論就是一句「終於」,以及兩句「即使」,但在革命與愛情均告幻滅後,這一句終於與那兩句即使,卻祇是巨大虛無中的一個分號,並非句點;叛逆依然凌駕虛無,美少女或許稍老一些,但她的文字老得更多。
認識陳德愉的人都知道,她講話速度奇快,有時候快到連標點符號都插不進去,但她文字的節奏卻很緩慢,緩慢到會出現這樣的句子:「當她與松鼠一同工作,埋頭對木材又刨又削之時,老人們就隔著一面牆大唱卡拉OK,他們粗糙有力的歌聲,順著山坳來的風,吹過田野,到了另一些坐在家門前乘涼的老人的扇子上;太陽在茄定鄉的田間也遲鈍了,拖著一片霞遲遲掛在天邊不走,就像是來陪伴老人們渡過餘生的」(櫻花妹行腳台灣奇遇記),短短一段文字,其中有場景,有聲音,有隱喻,有感觸,這就是新聞文學的基本要素。
當然,類似這樣的文字:「余秀華講起話來,每個字都使盡力氣,眼睛時而睜大時而瞇成一條線,嘴巴時而向左笑,時而向右笑,全身跟著擺動;猶如一陣暴風呼嘯,將整個余秀華膨漲起來,像顆隕石般向對方擲去」(撞擊中國父權神經的余秀華),更是「聽言」與「觀行」後的範例書寫,文字比影像更鮮活更逼真。
陳德愉人物書寫的另一特色是,她選擇的被訪者多數都是「光環沒照到」的那些人,完全違逆了「名人即有流量」的採訪法則,但她筆下這些非名人的故事,命運的跌宕起伏,生活的歡笑悲愁,卻絲毫不遜於五彩繽紛的名人故事;「人物訪問的深度和寬度,取決於記者本身的深度與寬度。你的河道有多寬闊,裡面的水就可以有多浩蕩」,這是陳德愉書寫人物多年後的心得,其中有強大的自信,也有嚴厲的自期。
從一九八七年一路游來的那條人魚公主,這幾年在浩蕩的河道中,「盪小舟看風景」(陳德愉語),看盡岸上形形色色的人群,而遠方,還有更遼闊無邊的汪洋大海,在等待她。
王健壯
(本文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
自序
我是一個傾聽者
二○一四年,我在南投縣幾個地區進行挨家挨戶的拜訪,範圍包括了九二一地震的主要災區中寮鄉,客家聚落國姓鄉,原住民部落等等。
我每天早上六點出門,趕在鄉親下田前,坐在桌旁吃早飯時去敲他們家的門;中午烈日當頭,從事體力勞動的人要找個陰涼處休息了,我就四處看看,有沒有在大樹下、騎樓內聊天的阿姨阿伯,走上前去自我介紹;傍晚他們回家休息了,就是我的黃金時間,我會沿著村內的小路,一間間房子走進去問,可有願意讓我進去坐坐的。
村民們一概都非常和氣,願意讓我進門。他們會舉著大大的白鐵茶壺,倒茶給我喝,讓我坐在客廳藤編的長椅上,伸伸久走酸痛的腿。他們也都很害羞,我們常常你看我我看你的傻笑半响,我爛透了的台語實在很難說更多的話了,在簡單的自我介紹與問候後,只能眨巴著眼睛看著他們。
在這些荒山野嶺,公車到達不了的地方,一個陌生的女人來到你家真是稀有至極的事,國姓鄉有個阿嬤告訴我,四十年來不曾有人來這裡拜訪過──無論如何,他們竟都對我掏心掏肺了,茶壺提起,茶湯落喉,便是落落長。
就這樣,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故事,我數一數,應該去過幾千戶人家,見過上萬人,聽過幾千個人的人生歷程了,在他們的家裡。
在聽他們說人生故事時,我覺得自己變得很微小,小到可以化進桌上的茶湯裡。我常常反省,自己到底能不能解決人家的問題啊?雖然我滿腹熱誠但是也沒有把握,事實上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專注地傾聽他們說話──然後我驚訝地發現,原來我的長處,是傾聽。
無論對方告訴我什麼,我都可以乘著語言穿越時空進入他的世界,甚至能感覺到他的感覺。在那個時間空間裡,我就是說故事的人。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經歷毫無困難地進入我的心,清清楚楚、連一聲嘆息也毫無遺漏。
這些是真的。
一對修道的富翁夫婦在深山裡蓋了房子,打算在此風景優美的鄉下修練終老,沒想到,房子建好不久,太太竟然先走了。
他家的房子非常豪華巨大,磨石子外牆、木作屋頂高展上升;在一個路面經常有坑的荒涼鄉道上,出現這樣一個巨大的豪宅著實令人驚異。兩公尺高的大門敞開著,蘭花密密地從大門排到客廳口,每一朵都有碗口大。
我順著那濃得不得了的花香走進大廳。一個穿著深色西裝、卡其長褲,整整齊齊的男人,獨自背對大門坐著,看著牆上的投影片──上面有一個美麗的中年女人,提著帽子,淺淺對他笑著,是他的太太。
我坐到他的身邊,他開始告訴我,如何與太太認識的,經歷了無數的艱苦創業,太太平常喜歡什麼討厭什麼……
講著講著他就哭了,看到一個老爺爺哭得這般傷心,我一時間也慌了手腳。
然後他抬起頭,問我:「妳想見見她嗎?她就在後面房間裡。」
原來,老先生捨不得與妻子分離,將妻子冰在冰櫃裡,藏在深山的華麗大宅中。
有兩個小女孩,一個九歲、一個十三歲,相依為命獨居在深山裡,最近的公車站要走半個小時,一天只有幾班車。
越南籍的母親被父親打跑了,不久,愛喝酒的父親也「喝酒喝死了」。兩個人的生活靠台中的大伯接濟,大伯不時送些食物與生活用品來,偶爾給她們一點錢。
我在黑夜裡提著手電筒上氣不接下氣爬到這小房子門口,敲敲門,僅及我的腰高的小女孩,在門後面露出半個小臉。我睜大眼睛盯著小妹妹,她非常緊張地看著我,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我問鄰居阿嬸,為什麼不通報有關單位?
阿嬸很為難地看看我,斷斷續續地說:不通報,她們再怎麼樣還是住在自己的家裡,若是通報了,不但姊妹會分開,房子也可能給人占去…。
我拉住小女孩的手,小小的,有一點點冷,想要牽走她──但是不行,身旁的阿嬸伯母齊聲拉住我,她們說不行,兩個小女孩有親戚還有財產。為了這些,兩個小女孩必須繼續孤單地住在這黑森林中。
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太太,坐在自家門口燒紙錢,是鄉下最常見的那種透天厝,一樓車位處擺著靈堂,上面掛著兒子的照片。白髮人送黑髮人,我想這一定是很傷心的,默默地坐到她身邊,但是她一邊摺紙錢,一邊對我大罵兒子,說他「死得好」。
她細細告訴我死者的劣跡劣行,「吸毒、賭博、欠債,一回家就要錢打老婆打小孩,然後把她也打了……」,最後這孽子吸毒過量某天暴斃了,全家人都鬆了一口氣。
說著說著,她突然張著缺了好幾顆牙的嘴,低低哀鳴起來,真的是哀鳴,不是哭,是嗚嗚的叫聲從深喉嚨裡發出來,眼圈乾著沒有一滴淚。孤兒寡母,多少年來是靠著指望著這孩子才能活,說來說去都是朋友帶壞了啊!
他們總是講著講著就哭了,自己撞破頭就算了,看著自己最愛的人頭破血流更是痛心難過,可是,無論多麼不捨得、多麼不甘願,都已經無可挽回了。我總是看著他們的眼睛,聽著他們的話語,讓他們的傷痛進入我的心。常常他們流淚,我也流淚。
離開南投回到都市工作好幾年了,但是,每當街頭的燈火一顆顆亮起來,人潮喧騰地預告夜晚歡樂來臨,在那比白日更刺眼的光裡,我總是忍不住想到百里之外山上的那兩個小女孩,正在漆黑不見五指的山上相依為命。她們好嗎?有好好地長大嗎?我甚至找了一個好心團體在她們家的附近設立了一所免費的課輔班,內心期待著有人看顧她們;但是,實情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她們好不好,她們的一切彷彿我心中的兩個洞,永遠空著,永遠使我感覺到自己的無能,自己的挫敗。
每個傷痛的來源都不同,那些懷念的、悔不當初的、人生的遺憾,被經年累月的辛苦打磨過淚水汗水浸泡過,一顆顆寶石一樣閃著光亮。講故事的人像是朝著我心中的深潭丟寶石,一顆顆咚咚咚地落進潭水;每一個迴聲都讓我知道,我是多麼微小,在這個世界上我能做的,只有盡己所能。
有一位老爺爺,少年時調皮頑劣,被許多學校退學,後來遠赴異鄉,經歷了五十年艱苦的奮鬥,好事壞事都做了,終於事業成功生意作得很大。他浪裡來浪裡去,年輕時爭勇鬥狠,可是最後卻一生平安,直到七十歲得癌症。
面對死亡,他告訴我,這一生最大的遺憾是「一直擔心自己的媽媽早過世,沒有看到自己發財的這一天」。說著說著,七十歲的老人的眼中慢慢地盈滿了眼淚,淚珠卡在稀疏的睫毛上。
我看著他哭,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心裡突然浮起這段話:
「傷痛教人認識真正的自己。有時候我們好像痛到快死了,但死去了一點點,才算真正活著。」
這話是好萊塢超級英雄電影「死侍」裡,一位盲眼老婆婆說的,她拿這段話來安慰女友過世,擁有不死之身的的超級英雄。我對所有超級英雄電影的情節永遠都記不清楚,經常張冠李戴,把這個英雄的遭遇套到另外一位英雄的身上去,卻對這位沒有幾場戲的老婆婆印象深刻,她對「超級英雄」的忠言,彷彿就是對全人類的啟示:不死之身不能使你活著,傷痛才使你活著。
「傾聽傷痛可以教導過去、訴說未來。」
我是一個傾聽者,我的心裡充滿了人們告訴我的真實故事,那是用生命的傷痛粹煉而成的寶石。我希望我的傾聽讓他們擁有面對未來的力量,我希望讀這本書的讀者可以分享這些力量。
活著,多麼不容易,人生總是事與願違。寶石實實在在,又硬又冷,要咬著牙全身使勁才握得住──澈骨辛酸的滋味,證明我們活過。
感謝上報王健壯董事長,擔任他的記者二十年,我雖然不斷地在寫作這條路上開小差,他從來沒有放棄過鼓勵與鞭策我。印刻的初安明總編輯、江一鯉副總編、可愛編輯敏菁,沒有你們的幫忙,這本書是生不出來的。
感謝爸媽與妹妹們,一直在我身邊加油打氣;體貼的壯壯分擔了許多家務,讓媽媽可以專心工作;擁有赤子之心的文忠,激勵我精神抖擻不被傷痛擊倒,永遠走在前往與虎克船長一決勝負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