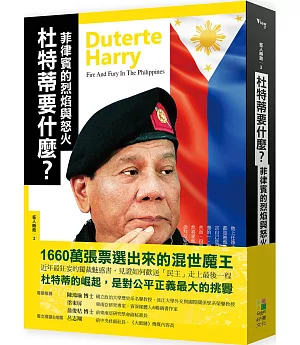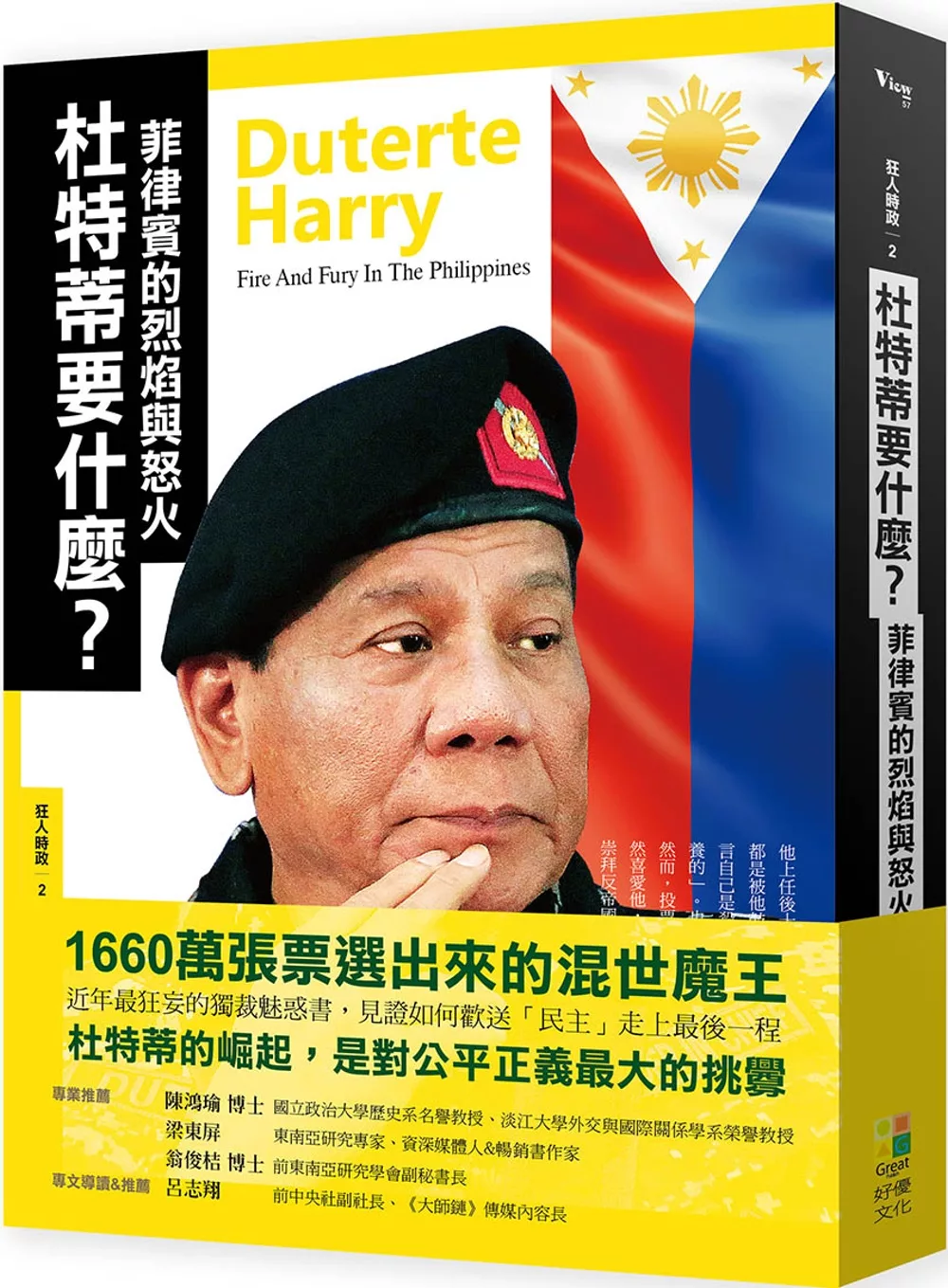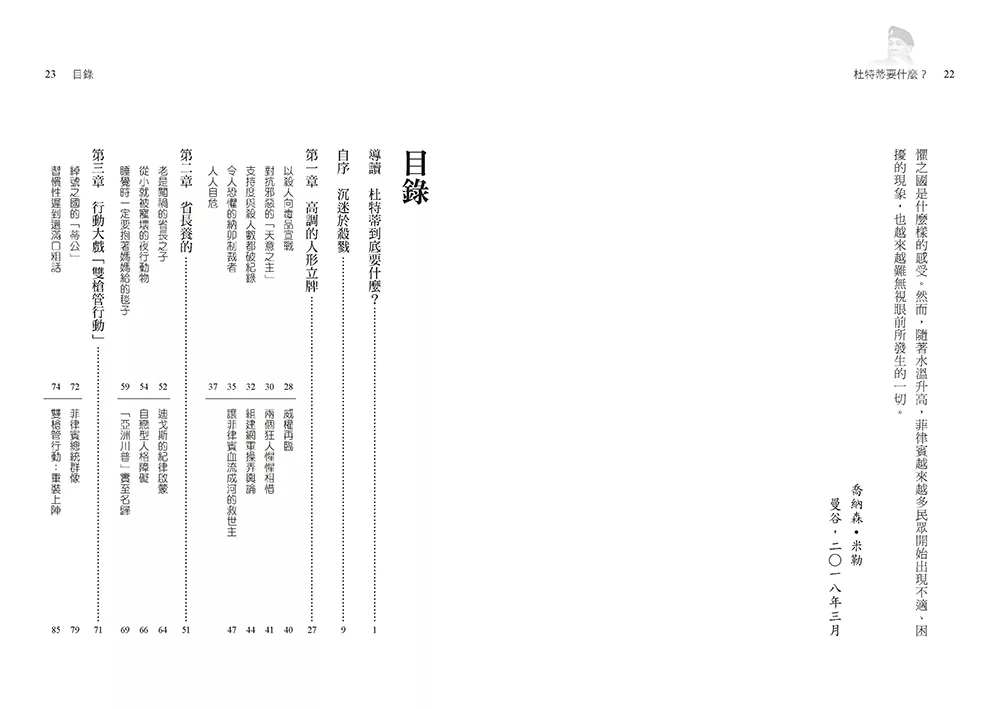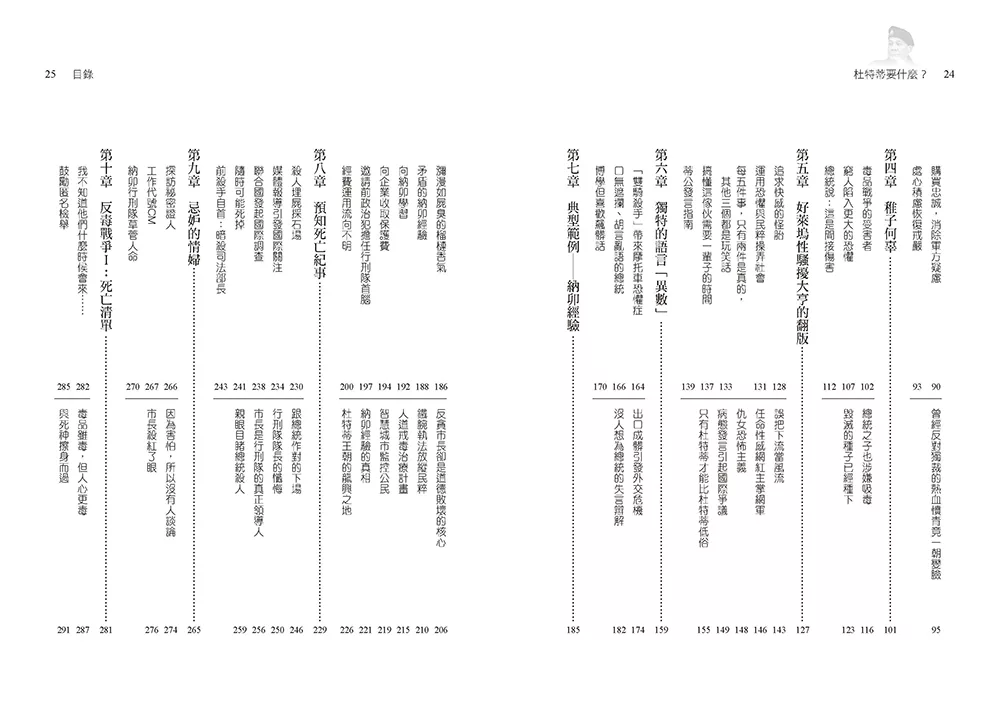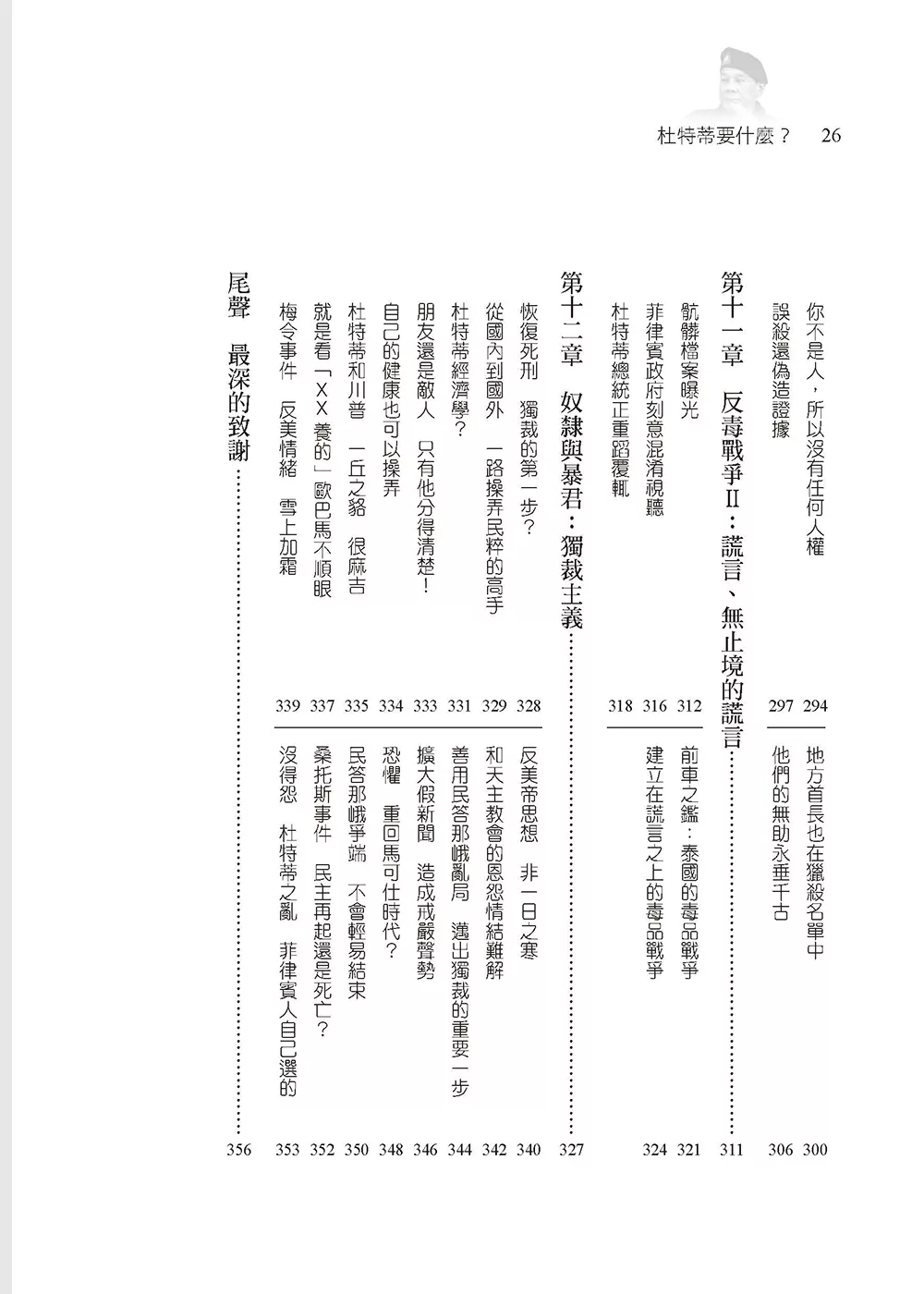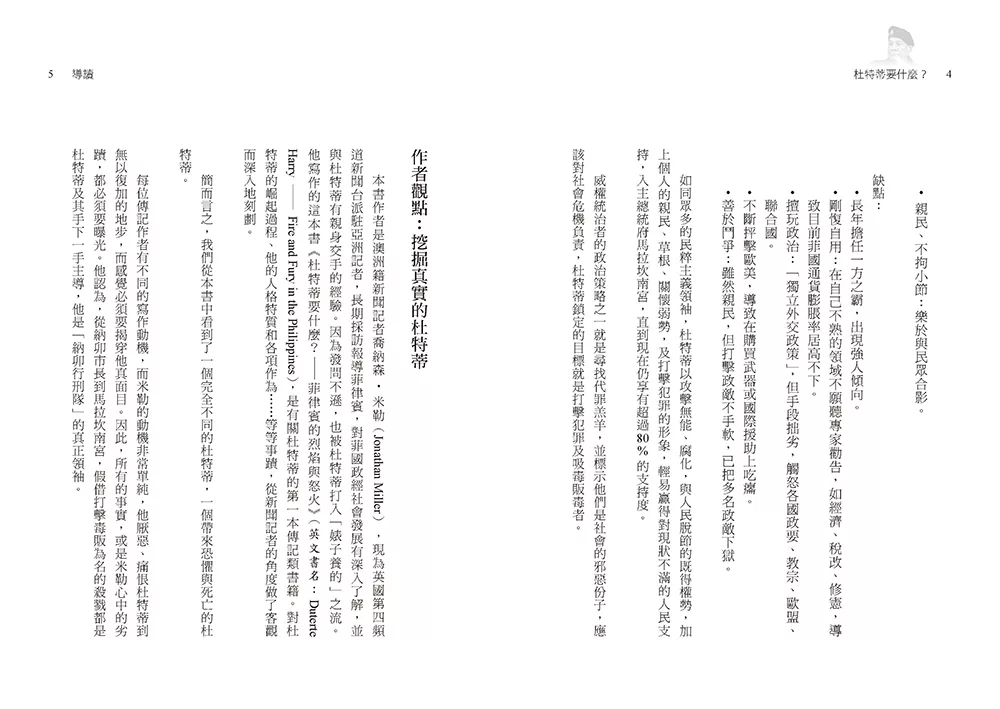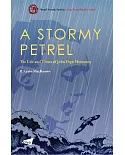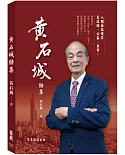序
沉迷於殺戮
喬納森‧米勒
「骯髒哈利杜特蒂」橫空出世
差不多在《第四頻道新聞台》派遣我擔任駐亞洲記者、重返菲律賓的時候,民答那峨島(菲律賓最南邊的島嶼)出了一位特例獨行、「出口成髒」的市長──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宣布將競選菲律賓總統。
他擁有獨特的街頭魅力和吸引人的粗野無禮,菲律賓人稱之為「流氓魅力」(gangster charm),並為其瘋狂。杜特蒂在辱罵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是「婊子養的」之後,還能在這個幾乎與梵蒂岡一樣虔誠的天主教國家中免受懲罰,讓我開始愈加關注杜特蒂這個人。
市長杜特蒂似乎認為自己可以消遙法外,他表現出與民眾打成一片的模樣,像個叛逆的局外人,無暇追求成為那些被他鄙視為「馬尼拉帝國」的腐敗寡頭政治家和王朝菁英。他喜歡槍枝、女人和摩托車,厭惡毒品、犯罪和繁文縟節。
菲律賓在尋找救世主,這個國家擁有逾七千個分布廣泛的群島和一億的總人口,卻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貧困中。這位市長粗野的主張,打破了階級與財富的藩籬,杜特蒂魯莽、傲慢的風格讓菲律賓人笑了,並開始對自己感到有信心。以他的話來說,他並沒有「不鳥」人民的想法,尤其涉及人權的部分。
在經過自由派多年效率低落的領導,以及對美國(前殖民統治者)數十年的尊敬之後,菲律賓終於出了一位直言不諱、以簡單對策解決國家問題的政治家。杜特蒂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不推意識型態:他嘴裡講的是貧民窟的語言,是個厚顏無恥的民粹專制主義者,在新興世界秩序的先鋒部隊中,遙遙領先唐納‧川普。
杜特蒂承諾,作為一個總統,他會像擔任納卯市(Davao city)市長時一樣,幹掉壞蛋並幫助社會。他陶醉於自己的化名:「骯髒哈利杜特蒂」(Duterte Harry),仿照克林特‧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在《緊急追捕令》(Dirty Harry)系列電影所飾演的人物,一位執行私法正義、總是先斬後奏的刑警,「骯髒哈利」‧卡拉漢(Harry
Callahan)。
杜特蒂告訴深受他吸引的選民說:「我是你的最後一張王牌,我向你保證,我會不擇手段都是為了達成任務……。所有吸毒的人,這些該死的人,我真的會殺了你們,我沒有耐心,也沒有中間立場,除非你先殺了我,不然我會殺了你,白痴!」
杜特蒂順利整頓了城市犯罪,在總統選戰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並迅速兌現其承諾。第一天,他發起一場拉丁美洲風格的「骯髒戰爭」,也同時帶來拉丁美洲人最黑暗的陰影:行刑隊。第一年任期結束後東南亞發生自波布開啓柬埔寨事件以來最慘重的平民喪命,短短十二個月內就犧牲一萬人的性命,其中大多數人非常貧窮,杜特蒂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在杜特蒂的恐怖統治下,行刑隊游走在貧民窟區,上任幾個月內,被這些私法警察所殺死的人數,是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獨裁者費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實施數十年戒嚴令期間死亡人數的三倍之多。
杜特蒂更著手復興馬可仕及其家族的聲譽。對許多人來說,這感覺就像在尚未癒合的國家傷口上再次撒鹽,但總統杜特蒂卻說:該是埋葬過去的時候了,他批准馬可仕的遺體下葬於國家英雄公墓、打算廢除目前仍試圖追討大部分馬可仕及其密友貪污一百億美元的機構,並支持馬可仕之子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擔任副總統的選舉爭議。
小馬可仕與他姊姊艾米‧馬可仕(Imee Marcos)——即家鄉北伊洛克斯省(Ilocos Norte)省長,開始陪同杜特蒂出訪外交行程,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二○一六年十月杜特蒂前往中國的國是訪問。一年後,一張面額十二菲律賓披索的新郵票印上了已故專制者的笑臉,令眾多菲律賓民眾感到驚訝。臉書流傳一則貼文寫道:「新馬可仕郵票不用黏,因為民眾都把口水吐在正面了。」
每天都有血腥屠殺的消息刊登在新聞頭版。二○一七年二月,杜特蒂下令拘押了最大力抨擊他的人,即前司法部長、現任參議員萊拉‧德利馬(Leila de Lima)。但事實上,指控德利馬的批評純屬「子虛烏有」,是受到人權組織具政治動機的煽動而發起的惡意騷擾活動。
杜特蒂極力打擊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首席大法官以及批評其毒品戰爭的世界領導人,包括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歐巴馬和教宗一樣,都被他封為「婊子養的」。
杜特蒂背棄了菲律賓最強大的盟友美國,轉向中國和俄羅斯。在全亞洲地區,一個原本嚴格遵守禮儀文化規範的國家內,杜特蒂的頑抗和放肆嚇得民眾目瞪口呆,然後端看一個個事件展現出難以理解與尷尬的魅力。
二○一七年五月,杜特蒂宣布在民答那峨島實施戒嚴,並放任軍隊對伊斯蘭教徒和共產主義者發動攻擊。杜特蒂的網路酸民大軍在臉書上淹沒了異議聲音,在上任首年的喧鬧結束之際,杜特蒂的人氣比當選總統時更高。杜特蒂享受這種通常只有極權主義政權才擁有的高支持率,且國會已經默許民答那峨島的戒嚴令實施至二○一八年底。
每當杜特蒂對其他世界領導人又有最新的不敬言論時,倫敦新聞編輯室總會不斷要求「更多杜特蒂」的新聞,雖然我很樂於報導這些聳動話題(畢竟杜特蒂確實是很好的素材),但看在許多菲律賓朋友與消息人士的眼裡,比起海外最初將杜特蒂描繪成有趣、高調的人形立牌,他更像是個極具威脅性的人物。
在菲律賓當地,那些瞭解杜特蒂任職納卯市長期間發生什麼事情的評論家們,情緒非常低迷;從一開始,他們就對杜特蒂擔任總統的前景感到不安,就像當川普宣布他打算競選總統時,也讓自由國度的美國打了一個冷顫,但菲律賓的情況更嚴重、更糟糕。
少部分關於杜特蒂的書寫,被埋沒在納卯當地報紙的新聞,揭露了美國外交電報、以及聯合國調查員與人權組織十年前的報導,這些內容形容他是個暴力威權主義者、納卯行刑隊的教父、堅信自己是絕對真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我在東南亞長大,並於馬可仕宣布戒嚴之後,首度到菲律賓進行短暫幾個月的採訪。我記得那時緊張的氛圍,還聽到學校師長、父母們與在馬尼拉、碧瑤市(菲律賓夏季首都)的菲律賓朋友、外國同事之間的緊張談話,因為他們正努力克服在軍事獨裁下的恐懼與擔憂。
沿著馬可仕高速公路前往碧瑤市的路上,建造了一尊一百英呎高、混凝土塑成的獨裁者半身像。後來這座雕像於一九八九年遭共產黨反叛份子炸毀,同一年馬可仕遭流放而身亡。一九八三年我還是學生時,對於艾奎諾二世(Benigno ‘Ninoy’
Aquino)遇刺身亡的消息感到驚恐,他是最大力反對戒嚴的人,被迫流亡三年後返回菲律賓,在馬尼拉國際機場降落不久遇害,現在馬尼拉國際機場以其名字命名。飛機內部一段精彩的電視畫面,艾奎諾二世告訴記者:「我不能因害怕遇刺而一動也不動,在角落虛度自己的生命。」幾分鐘後,他被護送下飛機時,遭槍殺身亡。
三十年過去,我不禁想知道,菲律賓人在杜特蒂領導之下,是否還會像當時那樣對謀殺事件感到震驚?我懷疑他們直到二○一七年八月,一名十七歲男孩桑托斯(Kian Loyd Delos Santos)死於菲律賓人厭惡的便衣警察手中,才開始群起反抗毒品運動——以及杜特蒂,這就像是個轉折點。
桑托斯遇害後的一項菲律賓公眾輿論調查顯示,總統的淨支持率首度下滑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意味他的政治蜜月期可能已經結束。儘管另一項民調與之相反——該民調指出杜特蒂的認同度與信任評級維持在百分之八十,正如馬可仕垮台是由艾奎諾二世遇刺所引起,杜特蒂垮台的那天,極有可能是因重新追查這位慘遭背後殺害的青少年案件而引爆。
桑托斯過世後一個月,影響力強大的天主教會表達了他們的立場,連續四十天於晚間八點敲響教堂鐘聲以抗議血腥殺戮。直到二○一八年一月底,菲律賓一家法院才指控三名警察殺害了桑托斯,而那時,杜特蒂毒品戰爭的掃蕩行動已經持續超過十八個月。
在本書付梓時,只有少數幾起因毒品戰爭引起的兇殺案件提交至法院,而且沒有一個被定罪。事實證明,司法體制無法或不願將兇手繩之以法,所以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首席檢察官於二○一八年二月宣布,將對杜特蒂上任以來,與毒品戰爭相關的殺戮事件展開調查,杜特蒂否認曾下令警察殺害毒品嫌疑人,杜特蒂的發言人也認為,調查只是「浪費法庭時間與資源」的舉動。
見證「毒品戰爭」的瘋狂殺戮
擔任記者期間,我駐紮於東南亞,生活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柬埔寨和泰國等各國。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的三個月內,我為第四頻道新聞台紀錄關於民答那峨島對抗伊斯蘭極端組織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與叛亂組織的戰爭,這是我第一次深刻體會到,菲律賓摩洛穆斯林(Filipino Moro
Muslims)經歷過西班牙與美國等殖民侵略者的壓迫、菲律賓天主教移民搶奪土地及數十年叛亂後的痛苦情緒。再過了十五年,菲律賓才選出杜特蒂,成為該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出身自民答那峨島的總統。杜特蒂看似帶來了新希望,但一切還只是開始……
杜特蒂上任前六週,我和他曾在納卯市有數次個人會面,當時距離民答那峨島實施戒嚴還有幾個月,毒品戰爭中的遇難人數也未達到二千人,但其瘋狂殺人行動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納卯市一場於午夜召開的媒體發表會上,參與者為總統隨行記者團和當地記者,我請他就放任國家行刑隊的指控做出回應,由於我是現場唯一的外國記者,所以提出這種問題也比較容易。
他憤怒地反駁,並誇耀說他擔任市長期間,就已下令英勇的警察們開槍殺人。杜特蒂誤以為我是美國人,所以他抨擊美國的虛偽,稱美國警察也在槍殺黑人,「有什麼差別」?我則強調,這些殺人事件並未得到美國總統的允許,但杜特蒂無視於此。這場媒體發表會在各家電視頻道上播放,我們之間的訪談影片在Youtube上面累積一千三百萬觀看次數。也讓我在社群網路平台上收到:「公審總統?外國記者該打!問一堆沒禮貌的蠢問題!」諸如此類的杜特蒂網軍威脅。
幾週後,我回到杜特蒂的故鄉納卯市,這一次,總統剛下飛機,結束與他心目中的英雄——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峰會上的會面。二○一六年十一月適逢杜特蒂出訪期間,他心目中另一個英雄馬可仕,則悄悄以軍禮下葬。杜特蒂花了一點時間稱讚這位已故的獨裁者,接著回到他最喜歡的主題——毒品戰爭,揚言威脅並為當時造成近六千人喪命的殺人行動辯護。
他聲稱菲律賓是「毒梟國家」(Narco-state)「就像拉丁美洲國家一樣」,警告那些操弄「毒品/政治」手段的人可能被殺。站在麥克風旁邊,我指出,他所提到的拉丁美洲毒品國家與行刑隊有關聯,並表示在他執政的頭五個月內,行刑隊在菲律賓所殺害的人,比馬可仕執政期間死亡的人還多。這樣的言論引起另一波反美謾罵,牽扯到美國入侵巴拿馬和伊拉克,也殺害兒童和成年人,「連狗和羊都不放過」,指責美國拿他在人權議題上作文章很虛偽,「你們毀了許多國家!」他說。
菲律賓總統府馬拉坎南宮(Malacañang Palace)針對此次媒體發表會所公告的官方紀錄中,並沒有記錄到他最後給我的評論,但這些內容卻成了隔天全國報紙和電視台的頭條新聞。當時總統問我是否還有其他問題,他的聯絡秘書(前電視台記者)抓著我衣角離開麥克風,杜特蒂:「連個問題都想不到?」嘴裡嘀咕著虛偽什麼的,然後低聲地說:「putang ina
mo」(你個婊子養的)雖然很小聲,麥克風還是收到了。菲律賓語「mo」(你)特別意有所指,如教宗方濟各和歐巴馬。我回到記者席座位上時,杜特蒂用他加祿語說:「看他像個懦夫一樣跑走。」
第二天晚上回到馬尼拉,我加入菲律賓自由攝影師路易斯(Luis Liwanag)的「夜行者」(the night shift)行列,身處杜特蒂毒品戰爭的最前線。這只是我第二次與夜行者的外出活動,但此時全菲律賓每日死亡人數已超過二十人。
晚上十點過後不久,我們在槍擊事件發生幾分鐘內趕到行刑隊殺人的現場,有人告訴我們,是兩名騎著機車的蒙面男子所為。一群青少年聚集在Dunkin’
Donuts的店門外,眼神凝重地看著一具躺在前方水溝裡的男子屍體,深紅色的血液從頭部後方滲出,與道路水窪內的雨水混雜一塊。警察趕到後,沿著附近欄杆拉起黃色封鎖線,這算他們的家常便飯,所以動作不疾不徐。街道上的車輛繼續移動,一切似乎很正常,除了那位死在水溝裡的人。一小群人在這裡圍觀,一輛吉普尼(Jeepney,譯註:一種菲律賓計程車)行經時,車上年輕女子拿起手機拍了張照片,似乎沒有人特別震驚,只是難過地呆楞在那。
在馬可仕執政的最後幾年,路易斯初次涉足攝影記者領域,他拍攝許多推翻獨裁者抗議活動的戲劇性照片,成了時代的象徵。一台萊卡相機從不離手,還有兩台Canon單眼相機掛在脖子上,攝影業界尊稱他「路易斯爵士」(Sir Luis),現在五十多歲的他回來了,開始記錄一個新獨裁者的興起,他跟我說:想更人性地面對恐懼。
「他們越來越大膽,一開始只會在黑暗的小巷,現在連繁忙的街道中心也肆無忌憚行動。」他如此說,在短暫休息時又多捕捉了幾個鏡頭,「民眾越來越習慣……,變得不太敏感,現在就像日常活動一樣。夜間殺戮活動橫行,人們像螻蟻一樣被殺,真的很可怕。」
命如螻蟻……
接下來幾個月,我深入研究杜特蒂的過去,以及他發動的一系列滅絕計畫,這句話不斷浮現腦海中,他似乎沉迷於殺戮行動,他或許不會把吸毒犯稱為蟑螂,但對吸毒犯也是人類這件事抱持懷疑,還聲稱很「樂意屠殺他們」。
「如果德國有希特勒,那麼菲律賓就有──」杜特蒂手指著自己說。
在我看來,菲律賓有比毒品更嚴重的問題,新的獨裁者準備誕生。
幾個月後,我花一小時與席胡戈(Miguel
Syjuco)談話,這位獲獎的菲律賓小說家與我探討對菲律賓新強人的憂慮。席胡戈正在進行另一部小說,也是揭露關於馬尼拉夜行者的暗殺行動。他為《紐約時報》撰寫多篇專欄文章後,遭到暴力威脅與人身攻擊。就在我們談話時,事件正迅速展開,毒品戰爭造成的死亡數量無情地增加。而杜特蒂宣布在南部實施「部分戒嚴」,並公開思考如何在菲律賓擴大軍事統治。
「歷史正在重演,」席胡戈說:「甚至過去的名字都回來了。之所以危險,不只是因為事件正發生,而是因為我們讓它發生。杜特蒂代表的是,當民主被允許扭曲、當民眾可以接受統治者拋棄民主制衡及任何約束他們法律,將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令我最害怕的是,不知道我們的民主制度最後會變成什麼樣。立法機關、法院、媒體、教會和反對派,他已經壓制任何起身反抗他的人,且非常有效地利用網路大軍和宣傳工具。」
席胡戈說,「民主不只是我們想要的多數決,民主也確保了那些即使是少數群眾也擁有代表權和享有平等權利,三十年來,整個世代的菲律賓人忘記了獨裁的教訓。」
在我們對話的這幾週內,杜特蒂在國會的夥伴開始彈劾選舉委員會主席、首席法官與獨立監督政府的監察專員。利用毒品戰爭的藉口,杜特蒂宣布對抗法治,要用槍枝來取代正義。每當我針對事件向菲律賓總統府尋求回應時,我的問題都被視為「惡意」。有人告訴我:「總統很『果斷』,他不喜歡迎合西方自由主義的觀點。」
杜特蒂/恐懼之國
我自己不喜歡某些西方外國記者「空降」進某些國家,然後就自以為睿智地分析當地民眾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本書幾乎完全是透過菲律賓人來敘述他們自己國家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我聽了批評杜特蒂的人士、總統家人、內閣成員以及其他死忠支持者的說法,也包含神職人員、公務員、報紙編輯及與我親密的同事。當然,我也花很長的時間聆聽杜特蒂的言論。我對這本書負有重大責任,他X的!這真是一種自殘、緩慢又痛苦的折磨。
我的觀點是,雖然菲律賓記者持續紀錄著殺戮行動與總統追求更大權力,但這個亞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其人民自由將日益萎縮。在杜特蒂日益獨裁的政權統治下,恐嚇脅迫氣氛壟罩著整個菲律賓,他的強硬執政風格還得到唐納‧川普的熱烈支持。據我所知,許多記者、人權捍衛者、律師、反對派活動份子和政治家都曾遭到威脅,甚至有些人已經死亡。許多被我採訪的人都要求匿名,因為他們害怕遭受不良後果。
對於那些不想招惹麻煩的菲律賓人而言,日子只能這樣過下去,他們當然意識到這些殺戮事件,但仍對杜特蒂哈利的滑稽舉動與反傳統性格感興趣。如果你是中產階級或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那麼最可能接近杜特蒂行刑隊的時候,是當你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一篇新聞,報導一些你從未去過的貧民窟發生了殺人事件,或是你的目光被一張五歲男童遭槍殺的照片所吸引,而殺他的兇手卻永遠逍遙法外。
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於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一書寫道:
和往常一樣,我們視若無睹地生活著。無視與無知不同,你必須努力無視它。
沒有什麼事情瞬間改變:在逐漸加溫的浴缸中,在你知道之前就會被滾燙的水煮熟。報紙上肯定有這些消息,水溝裡有一些屍體……
過去幾個月,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研究與撰寫這本書,這就是杜特蒂/恐懼之國的感受。然而,隨著水溫升高,菲律賓越來越多民眾開始出現不適、困擾的現象,也越來越難無視眼前所發生的一切。
曼谷,二○一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