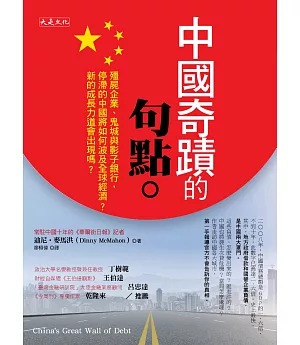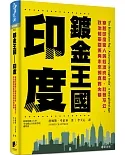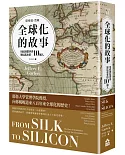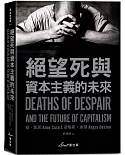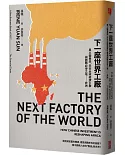前言
中國經濟能例外到什麼時候?
不過經濟刺激從未真正停歇過,負債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核心動力。若以絕對數值來看,中國的債務似乎是可以控制的。雖然難以準確計算,但到了2016年,中國的非金融債務總額是整個經濟體的2.6倍,和美國相去不遠(雖然有些估計又高出許多)。其實令人擔憂的並非債務總額,是債務累積的速度。2008年,中國的債務總額不過是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的1.6倍。根據以往的經驗,當一個國家相對於其經濟體,太快累積過多的債務,危機通常就會發生。
事實上,中國累積債務的速度,可能是現代史上最快的。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表示,自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體的負債增加了12兆美元(按:約新臺幣三百六十三兆元。),約等於該年美國整個銀行體系的規模。而中國的銀行體系規模,在過去九年間擴大了三倍,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都因此拉警報。
「對一個先進的經濟體來說,這個槓桿就已經太大了,更何況是新興經濟體。」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2016年末說道。他認為中國經濟成長日漸仰賴「快速的信貸擴張」,是全球金融穩定的第一大風險。
假如你在中國開車兜風,就會發現事情不對勁。許多城市都被無人居住的公寓大樓圍繞;奢華的政府大樓劃分許多辦公室,卻沒幾位官員在使用;中國工廠生產的鋼鐵占掉世界總產量的一半,遠超出該國的需求量;政府填海打算蓋工廠,卻從未真正蓋起來;國內各地工廠林立,卻都沒有發揮潛力。而風險就在於中國的負債浪費在這些,沒有回報的計畫上。
或許在21世紀──常有人稱之為「中國的世紀」的某一天,中國會一躍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宰制整個地區、甚至全球;而且多數人都認為這一天很快就會來。但在這件事成真之前,中國將面臨報應。
至於報應具體會如何出現,很難說。有可能是金融危機,或是長期經濟緊縮,就和日本在「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期間體驗的一樣。或者是成長率跌到2%左右,這對已開發經濟體來說算正常,但對中國這種開發中國家來說,這樣就是停滯不前,而且很難彌補。
雖然政府當局可能成功改革這個經濟體,但此時改革一定既痛苦又難以成功,導致經濟成長有段時間變慢,甚至永遠慢下來。但不管報應以何種形式出現,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奇蹟結束了。北京應對未來的方式,可能只是延緩中國的崛起,但也可能一蹶不振、永遠無法振作。
20年來再被看衰,但中國就是能例外
當然,中國的這項危機一再被人預告,卻從來沒成真過。2001年,專欄作家章家敦在其著作《中國即將崩潰》主張,中國經濟被脆弱的金融體系威脅,而共產黨會在十年內失去政權。2010年,以預測到安隆公司(Enron)垮臺而聞名的美國避險基金經理──詹姆斯.查諾斯(James
Chanos),將中國的經濟形容成「通往地獄的飛車」,房地產市場看起來像「杜拜的一千倍」(會這麼說,是因為前一年杜拜爆發了危機)。
2014年初,投資客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一篇短文指出,中國的成長模式已經「氣力放盡」。他預測:「中國的難題在接下來短短幾年內,會面臨危急關頭。」兩年後,索羅斯又說:「硬著陸看來是難以避免的。我不是預測到,而是已經看到了。」
但中國經濟不但仍屹立不搖,還維持極高的成長率。過去四十年來,它幾乎每年都能維持平均10%的成長,而且不曾低於6%。成長自2012二年後開始趨緩,看起來黃金時期結束了但就算是2016年,成長率也有6.7%,依舊高得嚇人。
對許多人來說,這種「無法失敗」的情況,證明了中國的例外主義;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管理,交給一群技術統治論的菁英負責,他們不受意識型態的紛擾、能下強硬的決策,追求成長、凌駕一切。
而美國人對中國例外主義深信不疑,正好反映出他們對自己國家的不安。2010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電視節目《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中說:「不如我們來當一天中國人?我想你們也知道,這樣就能授權給正確的解決方案!」
美國媒體常將中國描寫成美國想效仿的一切事物,卻又擔心短時間內學不來;簡言之,就是經濟健全、技術支配與妥善治理。比較樂觀的描寫是,2015年的電影──《絕地救援》(The Martian)中的中國形象;在本片當中,美國國家暨太空總署(NASA)要是沒有中國協助,就無法從火星救回麥特.戴蒙(Matt Damon)。
至於較為悲觀的描寫,則是2010年的某一支美國政治廣告,場景設在2030年北京的某間教室,一位中國教授解釋,美國之所以失去全球霸主的地位,是因為美國人既浪費又負債。「所以他們現在得幫我們工作啦!」教授說完,全班哄堂大笑。根據蓋洛普公司(Gallup)的年度民調,自2011年之後,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中國已經是世上最大經濟體,但其實中國經濟體的規模,只有美國經濟體的70%。
簡言之,中國例外主義被普遍接納為事實,正是中國如此強勢的主因。2014年,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發問,澳洲對中國的政策,主要受哪些因素影響?前澳洲首相東尼.艾伯特(Tony Abbott)的回答言簡意賅:「恐懼與貪婪。」
澳洲可能比其他國家,更能深切感受到中國的貪婪。我造訪帕拉布爾杜不久後,採礦潮就結束了,但現在澳洲人想要用一股「農業潮」來取代它,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於牛肉、海鮮、酒類、蜂蜜與日常用品的需求量都增加了。同時,造訪澳洲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多,使得教育事業與旅遊業分別成為澳洲第三大與第五大出口產業。
但艾伯特首相所說的貪婪,不是指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帶來多少機會,而是說它在十年後,有可能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假設美國每年要成長2%,那中國經濟體的規模,就必須在2016年至2030年間翻倍。成長幅度這麼大,也代表機會比成熟市場多。但若要享用中國崛起的果實,就得先付出極大的代價。
推薦序一
怎麼看中國大陸的未來?
「臺灣金融研訓院」大陸金融業務顧問/呂忠達
本書《中國奇蹟的句點》作者,在中國大陸經濟起跑的1990年代,開始學習中文,而他的人生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在中國度過,是這個國家經濟轉型的見證者,掌握了第一手的相關資料。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人口紅利」則被評價為過去這數十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作者在〈高齡中國,急需的成長力道〉提及,中國人口結構的老化速度,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有「未富先老」的現象,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有負面的影響。
作者指出,21世紀普遍被認定為「中國的世紀」;然而,人口成長因為1980年代的「一胎化」政策,現已趨緩,即使在2015年廢除了該項政策,但正如作者所描述的,其實傷害已經形成了。
再者,中國目前的就業率不如預期,儲蓄率因此升高、消費力減弱。此外,光是影子銀行「無中生有」的貸款數字,便已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0%。這位記者同時也點出一個問題:假使中國當局仍舊沒有著手處理其負債問題,將會對全球及臺灣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
有關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全球一般分成兩派:「中國機會論」與「中國崩潰論」。前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成長中的市場,所以要與它有密切的連結,才能促進自身的經驗成長;後者則認為中國有許多「結構性困境」,因此認定它的崛起或復興,只是一場泡沫。這種種對中國的激烈爭論,讓筆者想起波蘭已故元帥約瑟夫.畢蘇斯基(Jozef
Pilsudski)的一段論述:「蘇聯既不像許多人想像中的那樣強,同時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想像中的那樣弱。」事實上,如果把蘇聯換成中國,這段話也一樣適用,也就是說事實經常是介於兩者之間,很多事情往往是「比例問題」。
臺灣的經濟向來是對外的出口導向,目前最大的出口夥伴正是中國,約占了四成左右;而中國研究與兩岸關係,絕對是臺灣命運的終極考驗。很遺憾的是,臺灣落在統獨的相互對抗當中,不太能理性論證與冷靜思考「如何面對中國?」這項嚴肅的課題。
無論是在授課或寫作中,筆者長年向聽眾、讀者訴求:與其「親中」或「反中」,不如「全面知中」。至少作為一位「知中派」,務實的了解中國,找出因應對策與方案,可以讓臺灣走得更好!
推薦序二
債務長城的鬼影
《今周刊》專欄作家/乾隆來
萬里長城是中原文化的象徵,從春秋戰國時代一直到17世紀的明朝末年,超過兩千年的歷史,無數的帝王與軍事領袖,構築了人類最偉大的軍事建築。但是,萬里長城的軍事功能到底有多強,從來就是個問號,歷朝歷代的長城,可能都發揮過阻擋外族入侵的功能,但也都留下被輕易攻破、守軍不戰自潰、甚至主動開門迎敵的恥辱。
奇妙的是,京城裡的皇帝言必稱堯舜禹湯,堂前聚集的文武百官談的,也是作古千年的文王武帝,中國人就是相信長城,只要國力稍強,就耗費巨資、徵用民伕、反覆修築,兩千年來不斷輪迴,卻鮮少探究這道綿延數萬公里的城牆的實質意義。
到了飛彈按鈕可以決定戰爭勝負的21世紀,戰場已從兵士的刀劍互砍,轉移到經濟與金融戰場,中國人已經不需要再修築萬里長城來抵禦敵人了,但是大國之間的戰爭從未消失,鞏固中央集權領導的朝呼更為響亮。面對這樣的壓力,中南海的領導們又藉著強大的國力,瞬間築起了一道無形的萬里長城,這一回不是用泥巴與磚塊在崇山峻嶺間築城,而是用一張又一張的借條,瞬間堆出傲視全球的債務長城。
根據總部在華盛頓的國際金融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統計,過去十年,中國政府與民間債務總額占GDP的比例,從金融海嘯前的171%,暴增到2018年第一季的299%。高達36.5兆美元(新臺幣1,120兆元),相當於中華民國政府500年稅收的巨額債務,不只建了奧運的鳥巢、杭州的高鐵,以及監視全民的天網監視器,也養出了全球最大的影子銀行業,外加遍及神州大地的鬼城。21世紀的債務長城抵擋了經濟蕭條的攻擊,填飽了貪官汙吏的荷包,也滿足了人民樂觀的幻想,更鞏固了北京以及各地方政府的統治。
澳洲出身的迪尼‧麥馬洪(Dinny
McMahon),出生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1979年,9歲學中文、17歲踏入中國大陸,出社會後的工作主軸只有一個:中國觀察,他除了金髮碧眼之外,根本就是如假包換的改革開放青年代表。與汗牛充棟的中國經濟觀察者相比,麥馬洪穿上中國人的鞋子,站上萬里長城的烽火臺,從並肩作戰的夥伴身上,一幕一幕描述中國經濟發展的貪婪與恐懼的故事,完全接上了地氣(按:融入當地老百姓,反映出他們的訴求、願望)。
麥馬洪最後引用中國前任財政部長樓繼偉的評論說:「以債務驅動的大筆支出應是用來推動改革……但是這些支出卻拿去創造穩定的幻象,讓人們拒絕忍受改革的痛苦,當改革終於到來,痛苦也更烈,大家更不容易取得共識,且輕鬆的傾向極左或極右的民粹主義(按:有兩項特點,一是反菁英;二是反多元,主張反對人民訴求者是敵人)。」
作者要說的是,萬里長城築得再高,也必然會有缺口,40年的經濟奇蹟已經告一段落,正在向極左或極右傾斜的中國,即將對全世界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後果無人能料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