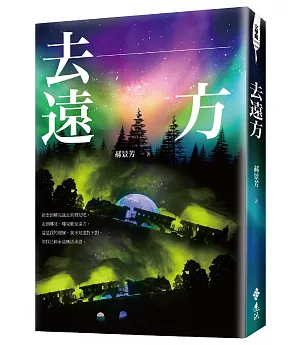自序
《去遠方》中大部分作品大約是十年前寫的,出自於我剛開始寫作的那段時間。今天回顧起來,有很多地方和我今天寫作的風格不太一樣,但我並不覺得它們幼稚,相反,我非常珍視最初的一些寫法,那是我今天很少運用,但是很喜歡的一些寫法。
具體是指什麼呢?
舉個例子。《九顏色》是書中的一個系列故事,其中包含九個獨立故事。有影視圈朋友將其買去改編網路劇。他們拿去很久之後,問我:「我們琢磨了很久這九個故事,它們獨立看起來我們都懂,但是我們不清楚它們串聯在一起的邏輯。」他們要我寫下這些故事的最初想法,於是我給他寫了這段話:
這九個故事都是關於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關於人的看法、印象、偏見、理性、情緒和信念,也關於真相和表像。很多時候,事物的表像讓人錯失真相,犯下錯誤,但也有些時候,對事物的信念雖然不是真相,但卻能給人積極的力量。真相與表像,哪個一定是好的,哪個一定是壞的?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我們自己眼光營造的世界裡。顏色就是觀看之謎。
這就是我那個時期寫作的主要特點。我的出發點都是某種模棱兩可的哲學爭點,越是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越是有多個側面的複雜問題,越可能成為我的寫作出發點。偏見很可能是錯的,但當我們都在嘲笑偏見的時候,它又有可能是對的。這樣的哲學的微妙讓我著迷。我喜歡探索人們都不重視的領域,或者在人們視而不見習以為常的事物中尋找。我迷戀意象、象徵、隱喻和模型,最終寫出來的故事,通常情節並不複雜,也沒有正確答案,但是都意味著我對某些事情的思索。那段時間,我寫了多種類型的故事,就是沒有傳統的情感劇。
後來的日子裡,我的寫作慢慢變沉、變實,不再像最初那段時間像浮雲一般飄在空中。我開始寫更多人情世故,寫更多悲歡離合。這樣的寫作獲得更多出版社和雜誌社的接受,也贏得獎項。但實際上我仍然想念最初寫作的風格,短小、精鍊、輕巧,浮動著無法說清的哲學疑問。
有關這個世界,我們能知道什麼?我們所有確定的,在某一刻都可能不再確定。世界的理論消解了,只有故事留下了。
《消失大陸的愛情》則是今年新寫作的小說。它的來源是有一次和友人的聊天:如果某天家園遇到危機,是否可以心無旁騖放棄家園,奔向遠方?正如在愛情裡,完美的AI替代品和原本的那個人,究竟有沒有不一樣?在衡量一些事的時候,用純粹理性客觀的標準衡量,似乎總有更優的答案。但是在生活裡,這真的是更好的答案嗎?我寫了一個氣候變化影響下的未來地球,主人公的選擇,是他個人的選擇,也凝聚著人類的選擇。
《去遠方》書名來自書裡其中一篇文章,也來自於我自己對生活的感受。我是一個常常心在遠方的人,無論在哪裡都會覺得疏離,而我也享受這種與人群疏離的感覺。心去遠方,在我看來是寫作的最大動力。
郝景芳 於北京
2018.09.05
前言:
《去遠方》是我早期寫作嘗試的完整總結。我寫的小說始終屬於無類型文學,這本集子中的作品更為明顯。書名為《去遠方》,是用了集子中的一個短篇的名字,也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篇。
我的小說一直有這個問題。對科幻讀者來說不夠科幻,對主流文學作者來說不夠文學。我曾將幻想小說投給過主流文學雜誌,但因類型不合適,收到過幾次退稿。編輯告訴我,雜誌並不發表科幻作品。另一方面,同樣的幾篇小說也曾被科幻雜誌退稿,理由是過於文學化、不太科幻。這是我在相當長時間裡面臨的尷尬。
如果我們將小說空間分為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那麼純文學或者主流文學關心現實空間,也表達現實空間,而科幻或者奇幻文學關心虛擬空間,也表達虛擬空間。前者如老舍先生的《茶館》,現實中的人物悉數登場,嬉笑怒罵反映現實世界的光怪陸離。後者如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或星球大戰的太空戰場,自有虛擬世界的邏輯和戰鬥目標。而與這兩種純粹的形式相對應的,是一種介於二者之間更模糊的文學形式:它關心現實空間,卻表達虛擬空間。
這種介於現實與虛擬之間的文學形式構築起某種虛擬形式,以現實中不存在的因素講述與現實息息相關的事。它所關心的並不是虛擬世界中的強弱勝敗,而是以某種不同於現實的形式探索現實的某種可能。
《西遊記》是這種形式的翹楚。它不是現實主義文學,現實中不會有一隻會變化的猴子和一隻貪戀美女的豬與人一同上路,也不會有妖魔占據每個山頭,但它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奇幻文學:它要講述的,不是魔法與種族的對抗譜系,它所關心的比那些更現實,也更複雜,它寫出的是現實世界的魔障,是一個人足不出戶而在心路上經歷的九九八十一難,寫下的猿是心猿,馬是意馬。四大名著中,《水滸傳》和《紅樓夢》都是以非現實的情節開場,無論是石碑下的黑風,還是補天的頑石與一棵草,都要將現實放在虛幻的大框架下。
虛幻現實可以讓現實以更純淨的方式凸顯出來。虛幻的意義在於抽象,將事物和事情的關係用抽象表現,從而使其特徵更純粹。誰能說得清頑石和一棵草對於《紅樓夢》的意義?沒有它們,賈府的恩怨依然可以上演,但若沒有它們,賈府的恩怨就只是世俗大宅的恩怨,整部書也就缺少了出世和入世這最為重要的超脫主題。若《離騷》不曾上天入地,只是一曲哀歌的話,那麼它也必然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精神求索。
講這些東西,我並不是想把自己的小說與古代神話和經典名著相提並論,而只是想探討類型文學對類型的局限。我的小說距離經典還很遠,我並不想用經典作品為自己的作品貼金。我只是覺得,給任何文學作品貼標籤、設定分類,從而人為設置柵欄,也許並不是一種好的方法。文學雜誌和出版作品上架的時候都有分類,擺在不同貨架,相互之間沒有交疊。這種情況使得文學作品化為一個一個小圈子,讀和寫都與其他圈子沒有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我難免會想,如果《西遊記》在今天發表,讀者範圍可能不會超過奇幻文學的小圈子,也不會有很多人意識到埋藏其中的複雜內容。
對我來說,文學首先是文學,其次才是某種類型的文學。我寫的作品不容易歸入類型,也不容易發表。我起初還在意,後來也就釋然了。很感謝那些即便如此,還能支持我寫作的人。從前以為這些短故事不會被人認可,直到編輯看到並給予認可,才讓我對這些無法歸入任何類型的簡短作品有了一點自信。這些支持對於一個無法找到歸屬感的作者來說至關重要。
郝景芳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