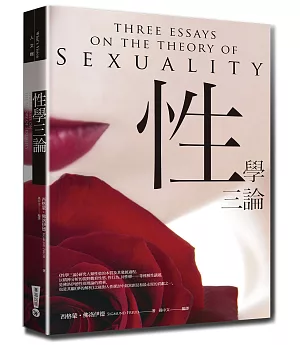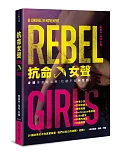推薦序1
科學與歷史交疊的重量
我記得我第一次閱讀《性學三論》是大二那年,在美國南加大修了一門美國性別史的通識課。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是這門課啟發了我對科學史的興趣。雖然 Lois Banner 教授沒把《性學三論》列入必讀書單,但課堂上的介紹令我大開眼界,使我反思對佛洛伊德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
當時 Lois 剛出版了一本關於人類學家 Ruth Benedict 和 Margret Mead 的傳記。二十世紀初,這兩位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剛萌芽的人類學系,顛覆社科對文化、種族、性別等議題的認知,是近代女性知識份子裡的傳奇人物,也襲手度過二十世紀裡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友誼,甚至愛情。雖然早期性科學缺乏女性專家的聲音,但像 Benedict 跟 Mead
這樣重要的女性公共知識份子,仍非常關注精神分析學及其他性學學派對於性別與性發展的理解。我大學接下來三年,除了私下細讀 Benedict 與 Mead 的著作,也沈迷於深刻引響他們的早期性學作品,包括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
1905年《性學三論》首度面世,之後的二十年,佛洛伊德經多次修改,把原先 80 頁的書稿擴張至 120
來頁。現今精神分析理論重要概念,如閹割情節和陽具崇拜,也是後來才加入,沒出現在原稿。書裡他大膽挑戰世俗的眼光,闡述人類「性對象」與「性目標」的區分、孩童的性精神發展(指出不只大人,就連小孩也有性衝動)、性變態是人類的本性與本質、淺在同性戀慾望是正常現象(「所有人其實都有選擇同性性對象的能力,在潛意識中也早就在這麼做」)、異性戀並非與身俱來的特徵(「一個男人會對女人產生性趣,絕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等。
透過這些論點,佛洛伊德把人類性慾呈現為一項生理機能,一種生命的動能,發展過程或許被阻礙、壓抑、培養、轉移、 昇華。雖然在當時性學圈裡,他最大的貢獻常被認為是他所創設的心理起因學說,而推翻之前對「性倒錯」的變異性學說 (degeneration) 與先天雙性學說 (bisexual disposition),但有如 Frank Sulloway
等學者指出,佛洛伊德的初衷還是以生物學的角度去探討人性,因為在他的認知裡,性慾是人類最原始的生理機能。
為什麼佛洛伊德要選寫《性學三論》?如剛才已提到,二十世紀初是性學蓬勃時期,眾多學者來自不同領域,包含法學、精神科學、神經病學、生物學、民族學、心理學、歷史學甚至文學,都加入戰場,豐富性學的學科建立,其中以 Magnus Hirschfeld 在柏林創設的性科學學院 (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1919-1933)為最鮮明且劃時代的例子。但佛洛伊德一生一直跟性學與其眾紛學門大師保留距離,因為對他而言,提升精神分析學的學術地位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因此,《性學三論》其實是透性學之名(英文原名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其實沒出現「性學」一詞),再次鞏固他一生最大的貢獻:細膩挖掘「淺意識」
(unconscious)的運作並把它設立為一個科學的研究對象。透過《性學三論》,佛洛伊德告訴我們各種性變態傾向均存在於精神病患的潛意識裡,精神病是性變態的一種負面展現。也因為他給了我們「淺意識」這個概念和思考途徑,間接挑戰宗教的知識論地位,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跟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十九、二十世紀科學革命裡佔有一席之地。
常常有人批評精神分析的文化束縛,說它隱約透露西方中心主義。這種批評有它的角力,但也有缺陷。值得注意的是,在東亞社會很少有人會如此質疑達爾文或愛因斯坦的科學論證(雖說從科學哲學的觀點來說,後兩者都有遺漏未解決的問題,且受往後門徒的調整)。但我認為,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佛洛伊德的作品及評估他們的重要性。近幾年美國學界出了一系列學術專書,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放進全球史的脈絡討論,勾韌出大眾文化如何挪用、顛覆並突破精神分析概念,在二戰以降的歷史時空裡突顯自我認同的觀念與政治張力(見
Political Freud [2015] 、 Cold War Freud [2016] 、 The Arabic Freud [2017] 等 )。因為在這一連串的歷史變局,我們無法將東亞社群的演變置身事外,對於鑑定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學在近代東亞社會文化史的參數,一樣來的急迫重要。
最近我在完成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專書《閹人之後:現代中國科學、醫療與變性史》,但我很疑惑什麼時候該「放手」,把終稿提交給出版社。我一位同事跟我說,什麼時候「放手」都沒有對錯,因為經過研究跟選寫這本書的過程,我們已成長為很不一樣的人。我覺得這樣的比喻,或許也能協助我們理解閱讀一本書的經驗。十五年前,我還是一位雙修生化與心理學的大二生,我以為佛洛伊德的想法像瘋子,我認為他對科學沒有重大貢獻,我沒聽過《性學三論》註腳裡引用的任何一位同期作者,我以為歷史是死的、在科學的世界裡只存在一種崇高的真相。如今,我對研究跨文化科學與醫療史有濃厚的興趣,我覺得佛洛伊德是位天才,我認為他的精神分析論跟進化論與相對論諭知同等級的科學革命角色,我熟悉大部份《性學三論》所引用的種種性學論述,我明白對歷史的解讀跟科學建立的真理一樣難成不朽的定局,
十五年後讀這本書的我,重新認識科學與歷史交疊的重量。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
姜學豪
推薦序2
女性主義與佛洛伊德的百年爭辯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1905年出版的《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在台灣再次被翻譯出最新譯本,為經典再譯的重要成果。《性學三論》對後人產生不少影響並引發許多爭辯,有其理論上必須好好理解的重要性。佛洛伊德在出版此書時,顛覆了他那時代的人認為兒童是「無性的」的想法,如書中所言:「大部分人認為,性衝動的出現始於青春期,幼兒並不會有性衝動的出現,這樣的觀點起因我們對性生活的基本規則缺乏了解所造成」。從台灣現今的性教育與性別教育的脈絡來看此觀點,不少反對性平教育論述藉由將兒童視為「去性的」、「無性的」,進一步排斥中、小學關於性與性別的教學,便是落入將兒童視為「無性的」與「去性的」假定中。因此今日的性教育如何以性平觀點落實性教育,並在未成年階段好好討論是重要的,而非將未成年與兒童放置在「無性的、去性的」想像當中。
其次,雖然佛洛伊德將同性戀、雙性戀稱為「性倒錯」(Inversion),但在此書中也提出心理的雌雄同體與生理的雌雄同體之間並沒有緊密的聯繫,此論點將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脫鉤,兩者並不必然直接等同。而書中也提出「精神分析學說始終極力反對將同性戀視作異類,將其與正常人群分離開來。透過性興奮的研究,我們發現所有人其實都有選擇同性性對象的能力,在潛意識也早就這麼做」,並提出「性衝動不以生殖為目的,自由不受拘束」,但文化中「將一切不為生殖服務的性衝動,都受到束縛」,可以看出佛洛伊德早已指出異性戀框架、生殖為目的的性無法框限人的慾望。劉毓秀針對這一點也指出佛洛伊德的貢獻:「佛洛伊德理論顯示,生物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三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連結,這對『男女天生有別』的頑固迷思以及強制異性戀機制(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不啻致命的一擊。」 。除了生物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三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連結之外,劉毓秀在討論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時,提到佛洛伊德時有不少論辯,但也提到佛洛伊德理論的幾點意義與貢獻,包含佛洛伊德所描述的實際情境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男尊女卑文化在心靈結構的形成與運作層面的狀況。
然而,佛洛伊德的理論引發的女性主義辯論也由來已久。不少論者從生物決定論、陽具崇拜(penis-envy)的理論切入討論。如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論》(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ysis)在探討女性身體與慾望時,將陰蒂比喻被「截掉頭部的陰莖」,小女孩擁有的陰蒂如同「較小型」的陰莖,此論點便是將男性視為參照主體來詮釋女性,女性被比喻為不完整的男性。對此,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在《此性非一》中批判佛洛伊德的力比多(Libido)論述是男性視野的。此外佛洛伊德在解釋女性身體與慾望時,將陰蒂視為屬於「男性特質」,陰道屬於「女性特質」的二元對立的發展模式,是將女性視為匱乏的、小男孩、萎縮退化、陽具崇拜的客體。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進而提出女人的性器官並非單一的性器官,而以「此性非一」的多元性器官來批判佛洛伊德陽具化的論述模式。
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家Alfred Adler、Karen Horney、Clara Thompson則提出性別身份、性別行為和性取向是社會價值的產物,而非生物決定論,批判佛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
)提出佛洛伊德將女性的不滿意與不滿足歸因於生理因素,而非社會經濟與文化地位的不平等。然而,持不同論述的則有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l)在《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提出佛洛伊德並非簡單的生物決定論,而是表明社會性存在是如何從生物性存在裡呈現出來。上述種種論辯,皆可以看到佛洛伊德所造成的影響與引發的辯論眾多,因此對佛洛伊德的性學理論,勢必有完善理解的需要。本文認為今日閱讀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最重要的讀者視角還是必須將權力、性別、與性之間的關係進行思考,在理解心理狀態的形成時,必須鑲嵌在社會結構因素當中,亦即在思考精神分析時,文化、法律、政治、經濟、社會等外在結構如何形塑心理、精神、性別、性與欲望等內在範疇,其中的聯繫便是最重要的關注所在。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李淑君
編譯序
初讀佛洛伊德《性學三論》是2013年,那年為了考研究所而將它列入書單,當時讀的還是唯一的正體中文版本。二十餘年前出版的書本,頁已發黃剝落,但內容字字仍是歷久彌新,即便我只是匆匆抄錄,卻仍舊震撼於佛洛伊德的見解,百年前的大膽論點,百年後仍然前衛。只不過,彼時的我萬萬猜不到現時的我,又能有幸與此書再度結緣。
《性學三論》最早的版本於1905年發表,但此後佛洛伊德卻不斷地修改其中的論述,截至1924年寫成的最後一版,共有四種版本。其中許多觀點都有相當的修改與調整,而這些調整後的差異,即是精神分析學派與佛洛伊德思想脈絡的軌跡。而後,《性學三論》也被翻譯為多種語言,本書的編譯便以最完確且流傳最廣的版本──James
Strachey於1949年所翻譯的英譯本為基礎,令其重新面世,讓正體中文的讀者能有更新的譯本可以閱讀。
如今放眼全球,性別平等議題、性少數權益的討論起落不休,於此時出版《性學三論》我想不啻有其非凡意義。期待此書能帶給人們更多不同的視角,在學術研究、醫學病理、社會法律,乃至時事議題的範疇,都能相互映照,成就更廣闊且溫柔的眼光。
2017年,夏,於台北
孫中文
原版序
世界上的戰火逐漸弭息,但全世界對精神分析研究的興趣越來越濃。我一方面欣慰,卻也憂心不是全部學說都讓大家接受與青睞。
精神分析學說中,「純粹心理學」方面的創造與發現,如潛意識、壓抑作用、致病的矛盾與衝突、疾病的益處、症狀形成的機制等,日漸得到人們的認可,甚至以往不接受的人們也開始逐漸重視。但與生物學相關的學說——即是這本書包含的要義「性學」——卻一再引起爭議,甚至部分曾埋首研究精神分析的人將之揚棄,轉而以其他路徑來定義「性因素」在正常和病態的精神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儘管情況如此,我依舊堅信同樣源自細緻而公允的觀察「性學」與「純粹心理學」一樣接近真相,無論是透過不斷論證回溯,或是一再的事實檢驗。不過世人有如此大相徑庭的反應,本身也不難解釋。首先,只有那些擁有足夠耐心和學識精湛的人,才能將分析深入到被觀察者早年的生活之中,從而證實我提出人類性生活本源的說法。但是,醫學治療往往要求迅速見效,這也就使得這種可能性大大降低。同時,只有那些擁有精神分析理論基礎的醫生才具備相關的素養,從而能不受自身喜惡和偏見的影響,做出專業的判斷。
有些人抵制精神分析學說最主要的理由,乃是因為本書強調「性」的重要,他們不同意人類一切行為意義都與性有關,並批判精神分析學說是一種「泛性主義」,指責它將一切都用「性」來解釋。但人出於維護自己的情感,在情感作用下常常混淆是非,選擇遺忘或者扭曲,於是便「震驚」於這樣的說法,從而抵制。其實很久以前,哲學家叔本華就曾指出:性衝動決定人們的行為和追求——他所說的性衝動難道就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的性衝動嗎?這番發人深省的警示怎可能被忘得一乾二淨呢?
至於性學概念的延伸,這是在分析孩童和所謂的性變態現象時所不可避免的。(如果人們早就學會觀察孩童,那我也就根本不必再去寫這些文章了。)最後,那些自以為「高高在上、對精神分析大肆批判」的人,我想都可以再試著沉澱與沉默一番,因為學說裡所擴展的性學觀念,和與哲人柏拉圖所說的──那種純潔無垢的「愛」,何其相似。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維也納,19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