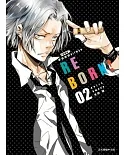代序
其實這篇序文,本是我的恩師鄭問先生答應要寫的,我把蕭主編很令人感動的來信附上,大家就很清楚為什麼我幫忙寫了:
鍾老師您好:
我們即將在八月初出版陳弘耀老師的首部長篇作品《大西遊》。會出版《大西遊》,主要是我在先前的工作中訪問過陳老師,結下相識的緣分,並曾得知《大西遊》多年前的幾次出版計畫都因無法符合坊間出版社的商業市場評估,而一再取消,算算距離連載完迄今,已三十年矣。前年陳老師過世,恐又更難了。適逢目色出版成立,其理念之一即是優先出版不受市場青睞的經典作品,因此我提議,決定將它出版出來。
由於陳弘耀老師已近二十年未正式在商業書市出版作品,新一代漫迷較不熟悉,因此初期發想時,即欲邀請一些過去陳弘耀老師的師友推薦,其中包含了曾在《歡樂漫畫》和《星期漫畫》雜誌並肩創作發表作品,且一直鼓勵和提攜他的鄭問老師,鄭老師接到邀請時也慨然應允了。只是未料就在預定交稿時間之前,傳來了令人悲傷的消息。
原先我已決定就此停住並繼續編輯作業,卻沒想到鄭師母竟仍惦念著這件事,在日前捎來短訊,寫道:「鄭問生前非常欣賞弘耀的為人和作品,是創作上的知己,未能及時幫弘耀完成序文就離開,一定是他的遺憾」,因此師母說,希望能請託您替鄭老師代筆完成。接獲訊息當下,不禁濕了眼眶,一是感念師母的心意;另一是感動兩位逝去老師的情誼,想到臺灣漫壇在短短不到兩年之內失去兩位老師,真的是太遺憾了。
非常謝謝老師的情義協助。
我想以上這封信,我能想到的就是情與義。
這也是我認識三十年的鄭問先生,從不虧欠人。所以我也只能厚著臉皮寫幾句。
陳弘耀老師,是那個台灣漫畫輝煌年代很重要的成員,但或許年輕的朋友不知道陳弘耀老師,很感謝有這個機緣,讓《大西遊》,重新問市。
人一輩子要看過多少漫畫,但陳弘耀老師的《大西遊》,間隔三十年,對他的分鏡節奏感,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好像昨天才讀過。
所以這本書我是極度推薦,也值得漫畫愛好者研究珍藏的。
臺北市漫畫工會理事長 鍾孟舜敬上
《大西遊》解說
說起陳弘耀,多半的直接聯想便是他確立聲名的《一刀傳》。一般人對《一刀傳》的定義,又普遍認為是部武俠漫畫,但之於對陳弘耀,他本人親口提及此部作品時,以為《一刀傳》其實是部具有「穿梭古今」元素的科幻漫畫。只是在《一刀傳》當中,古代版陳一刀的部份表現的太出色了,以至於讀者難以避免的,把感情都投注在《一刀傳》的俠情世界中。
一部作品問世後,作者的原意與讀者的解讀、認知有所不同,是很稀鬆平常的一件事,不過因為陳弘耀的《一刀傳》名氣太大,讓人容易忽略,他不只是個很會畫「武俠」漫畫的漫畫家,對於其他類型的漫畫,他也能掌握、駕馭得宜,這部份相信只要見識過他比較近期的《時間遊戲》
(短篇漫畫集),或是更早一些時候的《獸蒲團─偷禽寶鑑》(單幅幽默漫畫集),即會有清楚的認識。不過如果想要更深一層了解陳弘耀這位作者,只透過《一刀傳》與《時間遊戲》,以及《獸蒲團─偷禽寶鑑》這幾部作品,很明顯是有所不足的。因為這些作品都是陳弘耀進入熟成階段的果實,雖然美味可口,但都是太過於精密思量、雕琢之後的作品,少了陳弘耀早期創作的那種本能式的自由揮灑,與奔放不羈的爆炸能量,並且也不容易觀察他一路自我學習、修練過程中,汲取養份的來源,因此八○年代中葉開始在《歡樂漫畫》雜誌上刊載的《大西遊》,剛好可以提供我們進一步了解這位被稱為天才、奇才漫畫家的樣本。
不論今昔,許多的漫畫家都會告訴有志想創作漫畫的人,要創作漫畫不能只看漫畫,而是需要多面向的去吸收,接觸不同領域的訊息,好豐富個人的內在,厚實自己的創作能量。陳弘耀也是抱有此類見解的作者,他個人養份的吸收,也不光在漫畫當中,舉凡文學、音樂、純藝術..他都有相當程度的涉獵,不過影響他漫畫表現手法與內容、主題最多的,卻是電影與動畫。
先說電影這部份。陳弘耀在電影上得到的啟發,有兩個重要類型:一是科幻電影,另一個則是武俠電影。在科幻電影這方面,七○年代的《星際大戰》系列作,與八○年代的《魔鬼終結者》,都是他非常鍾愛的影片,這點如果有幸到過他早期工作室,或是看過他早期工作室的一些採訪照片,就不難發現一些痕跡。物質慾望相對比一般人低,也沒什麼收藏癖的陳弘耀,罕見地在工作室擺放著他親手組合用心塗裝的《星際大戰》,以及《魔鬼終結者》模型,而相關的畫冊、圖鑑也有沒缺席,從這邊便感覺得到他對兩作投入的氣氛,並且他也親口講述過這兩套作品的視覺處理,以及對未來的想像,是如何地開拓他的視野,提供創作內容上的參考。
《大西遊》故事中一些發生在天宮、外太空相關情節的場景,與反派角色的服裝造型,都有透出一些陳弘耀對《星際大戰》作出的回應與幽默,最末段「金角與銀角」與搭配他們的母親這三個角色,也很容易察覺出他對《魔鬼終結者》,那種超時代尖端的生化機器人的致敬與顛覆。
當然陳弘耀鍾意的科幻電影不只這兩套名作,已故名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遊》(2001:A Space Odyssey)一片,在外太空的視覺景觀上,展現的浩瀚寧靜,也帶給陳弘耀不少提點,其作用剛好與《星際大戰》戰鬥場面帶來的速度感與張力相互平衡,使得《大西遊》的視覺處理,在動靜之間有十分得宜的鬆緊度。
在科幻電影之後再來談談,對陳弘耀同樣具有深遠意義的武俠電影,七○年代至八○年代,武俠電影是相當重要的主流電影類型,而武俠電影又分作好些個派別,其中影響陳弘耀最多的要算是張徹導演的作品。
張氏一派的武俠電影,風格非常鮮明,他的影片總是強調熱血男兒間的情與義,其影片中的角色,常常為了朋友、兄弟的義氣相挺,而赴湯蹈火、義不容辭,除此還有另一個特色,則是少見一般武俠電影中,或多或少都要具備的,江湖兒女間的情情愛愛、風花雪月,並且女性角色不是無足輕重,不然便是被明顯邊緣化,女性角色之於張徹導演的電影不具關鍵意義,有時連花瓶功能都不存在,使得徹底陽剛的氣息,瀰漫在整個觀影過程裡。
在電影劇情發展這方面,張徹導演偏好以「復仇」為其故事的重心,為國為民、大義凜然那種華麗,卻很虛無飄渺的情節,不是他熱衷討論的議題,反而貼近真實的私人恩怨,讓他與觀眾容易互有共鳴。在現實中「快意恩仇」私刑報復是律法難容的,不過到了張徹的「江湖」則成了一種規矩與浪漫,而張徹也非常豪氣的將江湖恩怨盡情擠壓、釋放,讓暴力、血腥揮灑一地,因此銀幕角色受酷刑,在血泊中痛苦掙扎甚至身首異處等慘狀,都是輕易見著的。
回到《大西遊》上面,《大西遊》乍看是部具有喜劇基調的作品,藉著經典名著《西遊記》的架構來大作顛覆搞笑,此類改編方式並不罕見,但去西方取經要來渡化眾生這個大義,通常還是會保留沿用,然而陳弘耀在《大西遊》裡,可是完全捨去,取而代之的是江湖兄弟的恩怨情仇,主角獨尊孫悟空一人,唐三藏、豬八戒、沙悟淨等角色,都是為了要服務孫悟空因私人恩怨而起,接著愈滾愈大到失去控制的「復仇」行動。
前面說到《大西遊》具有喜劇的基調,但是劇中人男兒熱血的程度,可沒有因此而打折扣,反而是熱到破表。故事一開端,那位跟在悟空身邊的小老弟-小猴,是個連名字都沒有的配角(小個兒的猴仔就直接叫小猴),外型與個性都不搶眼,也不是什麼深藏不露的化外高人,可是遇到自己的大哥有難,唯一反應就是不顧一切的出手相助,這種肝膽相照、義不容辭的男性情誼,對應在悟空周圍其他的角色身上,也都如出一轍,個個為兄弟「生死」皆可置之度外,此番情懷與張徹的電影所表現出來的極為相近。再說《大西遊》中動作場面,其血腥、暴力的程度,好像因為表現風格的關係,似乎被卡通化變得比較不直接尖銳,可是看看故事裡,楊戩派出一班殺手去狙殺孫悟空那段戲的結果,孫悟空身體被機槍掃射成三段,只是陳弘耀很聰明的使用拉開的遠鏡頭,讓血腥的感覺被距離隔開,但畫面所呈現的意象,只要稍稍進入一點狀況,便可感受那種爆裂的強大衝擊。
這些陳弘耀因為受到張徹影響,而在《大西遊》中流露出來的特質,到了他的《一刀傳》還有更進一步的展現。好比主角陳一刀的生死弟兄柳長生,為了陳一刀被斷一臂,還給吊在懸崖邊,在甦醒後第一個惦念的,不是自己怎麼被吊掛在半空中或是少了一條胳臂,反而是大叫「大哥﹗」再則張徹的代表作有《獨臂刀》、《新獨臂刀》,對照一下兩者之間,不管是命名或是內容的安排,當中的微妙並不難體會。
當然《大西遊》故事以男性為主,屏除女性角色重要性的特質,在《一刀傳》中有略做修正,但到底女性角色在劇情中的份量還是偏單薄,張徹電影獨特的陽剛美學、男性情誼,還是在陳弘耀的作品中留下痕跡。
電影之後,來看看動畫之於陳弘耀創作,是怎麼樣的關聯﹖陳弘耀年輕時在動畫公司待過一段時日,也曾經為他的同學兼至交麥人杰先生跨刀,在台灣最重要的動畫電影《魔法阿媽》幕後協力演出,這些是他成年後與動畫的兩次重大交集,不過說實在的,這跟陳弘耀的漫畫創作沒啥深刻意義,重點在他童年時期,激勵他想要創作的是,一年難得一部,只在電影院才看得到的迪士尼動畫長片。那年代沒有如今的電腦科技協助,資訊也取得困難,然而即使如此,也無損陳弘耀的高昂興致,他以日本人「一期一會」的態度,全神貫注在電影院中,吸取他需要的養份,並將整部影片硬是記在腦海中,於腦中一再思量該作的魅力何在﹖吸引人的源由又是什麼﹖陳弘耀就是用這種方式訓練自我,讓日後他在漫畫動作表演上,有高水準的細膩與準度。
迪士尼動畫長片之外,華納公司的電視動畫片集,也給了陳弘耀許多刺激,看看哮天犬的造型,就可以感覺到有幾分華納卡通的味道。還有《大西遊》中許多幕的追逐、爆炸戲,也會讓人連想到《嗶嗶鳥與大土狼》(Wile E. Coyote and Road
Runner)。有意思的是迪士尼與華納,是兩種風格相去甚遠的動畫體系,更別提前面說到科幻電影、武俠電影..這些種種,讓人難以想像,它們總合在陳弘耀身上產生的化學變化,交織出《大西遊》或者是後續的《一刀傳》這般精彩的作品,真是太妙了!
文/張清龍(漫畫評論家)
專論
未完成的墨線:論陳弘耀
不知有多少讀者跟我一樣,每次打開《一刀傳》,總在全書最後一格懸盪,猜想故事接下來怎麼發展。好些年以後,再次看到陳弘耀的名字,是出現在翻譯小說封面、穿插在小說家袁哲生的作品《倪亞達》和《羅漢池》。陳一刀的待續情節仍擱置在時間的閣樓,漫畫家本人卻永遠離開了。
陳弘耀集結出版的作品不多,總計《魔輪》(1983)、《一刀傳》(1989)、《獸蒲團─偷禽寶鑑》(1996)、《時間遊戲》(2011)以及《千年世界盃》漫畫劇本(2013)等幾部,令人驚艷的《赤狐》(1992)、法國版《水滸傳》、《毛澤東》乃至原訂出書的《千年世界盃》漫畫版,皆未完成,而篇幅足夠出單行本的《大西遊》(1986─1987)在他生前也從未出版。作為生長在台灣的漫畫家,陳弘耀一生的創作都在回應、穿刺時代的圍困,也不免呈顯出在地的種種限制。他試著以漫畫劃破束縛,卻時時受到時代環境的框限,像個努力掙脫框格的漫畫人物,在平面世界永無止境的戰鬥著、挫敗著。
十六歲的陳弘耀畫出第一個完整的十六頁短篇〈末日〉,敘述殘存的地球人遭到敵軍追殺,正逃離太陽系,將軍凝望著無盡的黑暗,回憶起十八年前拯救他的機器人,靜靜等待即將吞噬掉他的終局降臨。〈末日〉最早發表在1981年,距離解嚴尚有六年,漫畫在彼時的社會觀感不佳,家庭和學校教育體制都認為那是端不上檯面的玩意。就讀復興美工的陳弘耀為了展出這篇科幻漫畫,先是在學校班展前一天師長檢查作品時假裝沒準備而被罰站操場一下午,隔天偷渡全篇作品參展,轟動校園。
如今重看這篇作品,陳弘耀展現的分鏡、畫工技巧已頗有水準,故事氛圍和核心概念的拿捏還有些青澀。稍後接續畫出三、四篇短篇練習作品,因故受託接下繪製《魔輪》三冊。此時他尚未掌握較長篇幅的結構,整體畫工略嫌粗糙,畫面的節奏和協調感也因為倉促而不及自己的習作。《魔輪》的故事編排受限於電影原作劇本,描述一個陰錯陽差加入越野單車隊的少年和外星人的奇遇,顯然仿襲當時好萊塢熱門電影《E.T.外星人》,漫畫家的發揮空間有限。但陳弘耀在工作過程中,除了鍛鍊製稿耐力和紀律,也逐漸思考怎麼呈現較長篇幅的作品,醞釀起自己發想的原創漫畫。
當他服完兵役後,隨即著手準備第一個連載作品《大西遊》。這部漫畫顯然脫胎自古典小說《西遊記》,而汲取同樣素材的日本漫畫家鳥山明早從1984年開始在《週刊少年JUMP》連載《七龍珠》。鳥山明的改編在現今看來實為王道漫畫經典,初期套用尋找七龍珠的英雄歷程加上成長故事模組,之後添加武打格鬥、外星人等元素,逐步擴大漫畫描繪的奇幻宇宙。但奇妙的是,陳弘耀在1986年連載《大西遊》的設定,就以科幻宇宙為場景,穿著牛仔褲的孫悟空駕著衝浪板似的筋斗雲,拿著如意棒大鬧名為「天宮」的人造星球。在陳弘耀的筆下,一切幾乎都顛覆了:天宮是暗黑陰森的所在,玉皇大帝像是反派頭子,觀音菩薩是龐克胖妹,楊戩是迷戀觀音的油滑傢伙,如來佛祖則是死神一般的邪派形象,唐三藏和沙悟淨是宇宙海賊,孫悟空頭上的金箍王冠暗藏著滅族大恨。凡此種種,我們可以想像作者本來可能開展出來的漫畫宇宙,以及其間難以預料的冒險故事。這部作品出現大量充滿勁道、速度感的密集效果線畫面、魄力滿點的跨頁圖,相當程度呼應著退伍後的作者正如孫悟空那般血氣剛猛地衝撞,企圖打開一番新局面。《大西遊》整體的基礎工程皆在現存的篇章完成,王道戰鬥與詼諧搞笑並行,流暢分鏡、動作場面和畫風,有幾分大友克洋的氣味,完全不遜於與他同輩的日本漫畫家。
可惜陳弘耀生在台灣,沒機會在一個持續存在的舞台逐步成長、累積經驗和人氣。他在受訪時提過,當初《大西遊》由於編輯突然要求連載腰斬結束,只得放棄。當時刊載的《歡樂漫畫半月刊》於1987年改為月刊,1988年停刊。沒有定期出刊、穩定發行的漫畫刊物一向是台灣漫畫困境的癥結。最常被提及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在1966年開始頒布〈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等審查法令,教育部要求地方加強管理取締連環圖畫,使得當時看似蓬勃的漫畫風潮遭受直接打擊,許多本土漫畫家退出舞臺,導致出版社大量翻印日本漫畫,有些出版社甚至找人描圖照抄、修改些許細節變造成本土作品,也時常另取篇名和作者名魚目混珠。例如陳弘耀就讀國中時,翻看手塚治虫《怪醫黑傑克》的盜版,作者打上別的名字,他還寫信到出版社請求那冒牌作者收他為徒。另有研究指出,其實早在審查制度出現前,台灣漫畫由於大量粗製濫造,品質低落不堪,加以家庭和學校不斷污名化漫畫,審查制度不過是給予最立即的打擊。一個原生漫畫生態的毀滅,除了制度催逼,也關係到社會集體心態的轉變。對照日、韓鄰國案例,漫畫同樣處在對抗著社會、教育體制給予的污名和枷鎖,並非總是一路暢通。台灣走向選擇以盜版日本漫畫作為滿足需求的辦法,一來是取得方便、成本低廉,二來是利潤遠高於培養本土漫畫作者和環境條件。直到1990年代初期,漫畫版權觀念、法規搭配下,出版社才漸漸放棄盜版作法,然而整個漫畫市場的供需和品味幾乎已是日本漫畫的天下。
1985年創刊的《歡樂漫畫》集結當時成群的漫畫天才競相推出作品,諸如鄭問、曾正忠、敖幼祥、阿推、麥人杰、陳弘耀、林政德、蕭言中、傑利小子等。他們的漫畫各有不同語法,也較為注意日本漫畫以外的養分來源,一起登場展現出台灣漫畫的生猛活力。迎接他們的卻是一個被日本漫畫吞噬殆盡的市場。年輕作者需要時間成長,同時要爭奪被日漫包圍的讀者。出版社試著花錢花心力造出本土漫畫產業環境,對抗不受版權規範的便宜翻印,雙方成本和獲利天差地別,自此台灣漫畫只能待在漫畫文化生產的下游,撈撈人家剩下的小魚小蝦。如此困境,使得漫畫在台灣很難出現典範,而沒有在市場和作品內容都取得成功的漫畫家,就不容易吸引願意長期投入的後繼者。儘管艱難,《歡樂漫畫》的短期存在,依然發掘出一批潛力新人,接續在爾後的《星期漫畫》上發光發熱,陳弘耀就在上頭推出代表作《一刀傳》連載。
陳弘耀大約沒想過,二十多年後的小說、影視作品會充斥著「穿越」題材。他最早在1983至84年間即準備過《一刀傳》的第一版,畫風與1989年正式推出《一刀傳》大異其趣。故事大綱是明朝末年版的陳一刀和1990年版的陳一刀交換時空背景,一個是大俠,一個是豎仔,一樣的外貌,兩樣的性格。陳弘耀以寫實風格處理穿越時空的離奇設定,分鏡、畫面的掌控能力比起《大西遊》時期更為成熟精緻,鋪陳雙線交錯的故事尤見功力。《一刀傳》的主要設定是雙主角,只不過作者將之轉換為同一人的前世今生版本(或可視為同一人的不同性格面向)。九○年的陳一刀是略懂武術皮毛的痞子,萬曆末年的陳一刀則是行俠仗義的武林高手,他們無端被拋擲到陌生的時代,試著以自己的方法存活下來。讀者一面為九○陳一刀深陷朝野惡勢力的圍勦而捏冷汗,一面為萬曆陳一刀困在現代文明社會而感到荒謬,兩邊皆是錯置,也因此拉出懸疑的張力,讓讀者好奇著後續情節走向。然而故事捲軸卻懸置在一個擁有美好氣象的開篇,作者並沒有將他們兩人放回到原本的時空,而是讓他們永遠關閉在不知後續的方格中。
《一刀傳》放到今天非但不過時,還有許多內涵值得挖掘。兩個陳一刀因閃電打雷,互相轉換至另一時空,代替彼此的身分過活,或許可看成「人如何了解自己」的隱喻。萬曆陳一刀穿梭至九○年台北,像是古裝演員走在資本社會的大街,其中一幕畫他走入(貌似)台北行天宮,瞥見婦人開著水龍頭洗水果,就跟著伸頭喝水。眼前是他從未想像過的世界,各種奇巧器具、穿著、行為都令他茫然無措,直到遇見一個擺算命攤的釘子戶老人願意試著理解他。九○陳一刀則拿著意外取得的手槍,去到險惡難測的萬曆末年,代替另個陳一刀承受被追捕、背叛的滋味,而他同樣困惑著古代世界的生存律法,該怎麼逃過接連襲來的劫難。隨著故事開展,陳弘耀似乎在暗示:人必須要深入歷史,才能理解現在,同時在冒險旅程中逐漸知道自己是誰。《一刀傳》蘊含的可能性和想像空間十分可觀,正當故事枝葉漸次衍伸之時,刊載的《星期漫畫》於1991年停刊。陳弘耀再次失去舞台,台灣也少了一部經典長篇漫畫。
陳弘耀後來在1992年畫《赤狐》初稿提案給出版社,可以看到畫工技術更勝《一刀傳》的華麗演出。可惜找不到出版社願意好好跟他磨出這篇《赤狐》,而他自己似乎也因為畫出十多頁細緻稿件而失去畫漫畫的動力,最後僅有尚未完稿的草圖和人物設定。就目前看到的內容,時代背景約莫在明代末年,故事只開了頭,主要角色剛剛登場,還看不出後續情節的梗概。之後,陳弘耀曾在1996年出版單格漫畫集《獸蒲團》,以輕鬆的筆觸風格,演繹各式諷刺笑鬧的瞬間定格。匆匆十年過去,他才在2006年推出《千年世界盃》原作小說,內文穿插人物設定和漫畫初稿,預告繪製中的漫畫版。《千年世界盃》以西元1026年中國宋朝在開封舉辦「世界盃足球賽」為故事主線,想像那可能實際發生卻沒有記載於史冊的蹴鞠大會。單憑小說文字敘述,即已顯露出陳弘耀擅於想像歷史的功力。像他這樣能從歷史的縫隙挖掘出虛構可能的漫畫家,實屬罕見。這必定需要做大量功課和研究,才能在充滿限制的時空框架中,找出發揮奇想的切入點,從而創生一個逼真的作品。可是又十年過去,這部《千年世界盃》漫畫始終未曾問世。
漫畫家黃熙文提及,年輕時因參加社團「漫畫之友」,認識了眾多漫畫同好,其中也包括剛退伍的陳弘耀。在黃熙文的描述中,「漫畫之友」最早從嘉義開始,後來拓展全台,他們定期聚會、交換作品輪閱批評,也將作品集合起來編印每月會訊。會員規定每月須繳交一定份量的作品、作品評論和研究,直到成員們各奔西東才解散。據說「漫畫之友」提倡推廣四頁漫畫,最早就是陳弘耀的點子,讓漫畫初學者容易入門,學習掌握起承轉合的說故事能力,之後再慢慢拉長篇幅。
陳弘耀在2011年自費出版《時間遊戲》,收錄大約在2000年前後創作的短篇漫畫,可說是親身實踐了演練範例。第一篇〈轉世〉以四頁篇幅,畫了個博學老人轉世到上古變成一隻暴龍的故事;第二篇〈對話〉也是四頁篇幅,假想地球可能曾逃過被消滅的命運。中間兩篇〈竹蜻蜓〉和〈冬眠〉則是飽滿的十六頁短篇,〈飛人〉及附錄的〈機械.人〉兩版本則是八頁短篇。這部集子算是陳弘耀的火力展示,證明他幾乎沒有不能掌握的題材和畫風,唯一的阻礙就是沒有時間─恰好是書名的反諷。這些故事共同顯現作者如何在一無聲的藝術媒材處理時間,詮釋轉世輪迴的時間向度,遙迢時間的暗面,時間的暫停或跳躍等。漫畫是文字與畫面相互激盪下的產物,短篇或許可以完全只用圖畫展現,長篇則嚴格考驗作者對結構的述說、鋪陳、安排,以及對時間的耐受度。
陳弘耀一生鍾情於漫畫,幾乎精通所有漫畫技巧(詳見他曾在2009年間部落格的「無責任漫畫教室」系列文章,篇篇都顯示他扎實的基本功和對漫畫媒材形式的深刻理解),卻沒能完成腦中的許多構想。我以為,他的掙扎奮鬥就是台灣漫畫困境的縮影。一部漫畫顯現的不只是作者本人的意志和技術,也關乎周邊出版、編輯、助手、工具、刊物、傳播管道、讀者反應,乃至社會整體的文化土壤厚度。因此一部漫畫不只是漫畫,其中匯集的是人與社會文化不斷互動的結果。在地的資源若不足以讓創作者擁有舞台穩定發展,只好向外尋求其他可能的出路。所以早年鄭問得到日本出道才能被稱為「亞洲至寶」,曾正忠差點要在日本漫畫雜誌畫連載,麥人杰要轉做動畫《快樂星貓》,而陳弘耀近年則準備與法國漫畫編劇合作。
近幾年由於《爆漫王》、《重版出來》等深入描繪日本漫畫產業的作品陸續改編成真人電影及日劇,人們多少對漫畫的製成、產出有些基礎認識,然而這些理解卻很難套用在台灣的漫畫生態。陳弘耀早年參與「漫畫之友」的故事讓我聯想到1950年代末期由鍾肇政、鍾理和、陳火泉、李榮春等作家參與的《文友通訊》。他們提出作品交換閱覽、批評,由鍾肇政彙整參與者的近況和意見,油印通訊,轉寄成員。一代一代的藝文創作者總在各種限制下面對嚴峻的現實考驗,嘗試突圍,糾集同志,讓作品、作者的身影積累起來,成為文化地層的一部分。
陳弘耀終究未能完成的作品之所以帶來那麼多遺憾,完全是因為他曾讓我們看見那可能達到的燦爛,宛如一道切開天空的銀河。
文/黃崇凱(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