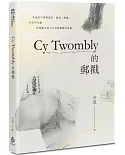自序
依時間順序而言,我的文學生涯是從詩歌創作開始的,更確切地說,詩歌是我邁入文學領域的基礎與起點,一個不可退轉的精神路標。一九八四年,我的新詩之路在嘉義的《掌握詩刊》上開展,在諸多寫詩同仁的砥礪下,我那激越的詩情之火焰更加被垂護地燃燒起來。在那以後,我盡情所願地抒情寫詩,寫出的詩作有的在報刊上發表,有的就這麼置放箱底與流動的時間共享安謐。當時,我的想法簡單無比,寫詩並非為功成名就,並非為贏得詩壇的桂冠,而是我深切感受到一首詩歌的完成後,那種用詞語很難表達的愉悅心境。抽象地說,那是詩神所賜予於我的召喚,要我終生守住這個奇蹟,只要我的指頭還能敲打,隨時就可寫下自己最深然的感動。然而,儘管有這樣的機緣,詩友亦鼓勵我出版詩集,但是我始終認為詩集自有其面世的時機,我應該尊重和順乎這規律的安排。
於是,因於經濟壓力的因素,我持續寫詩的同時,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注在翻譯工作上,日夜不曾懈怠,直到我譯出幾十餘部日本小說以後,我手邊那部厚如磚塊的《現代日漢大辭典》,竟然被我折騰得書背開裂內頁皺摺不堪了。或許這樣的付出獲得某種回報,我的生活情況因而相對穩定下來,便又執筆撰寫文學書評和創作小說,更勤奮地鍛煉自己的文筆。近年來,先後出版兩本小說集《菩薩有難》和《來信》,這些作品足以反映我熱愛小說的情感,以及我對於臺灣社會內部的急遽變化而造成底層人物命運多舛的關注。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在文學創作中似乎已取得某種程度的滿足,至少羨煞很多文學圈外人,但我依然無法忘情詩歌的靈魂,當它輕易盈滿我的內在生命時,我就如同獲得天神般的力量,不消多少功夫,即能完成對於詩神的承諾。雖然這是我個人的體驗,但我體會得尤為深刻,希望用文字寫就下來,使之與時間對抗,而非讓它僅僅駐留在思想的流沙河之中。
去年開始,詩神似乎特別善待我,在這微妙力量的促成下,我順利地寫出一○八首的詩作,也就是這次輯錄成的詩集《抒情的彼方》。我在這些詩作中,既有自我意義的完成,還演化出詩歌作為我思想情感的載體,如何使我所思的境界成為可能,或者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高度。若說將這無形的精神流動視為宗教般的秘契經驗的傳承亦無不可。我甚至很希望這樣看待。正如天底下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有其因由意義那樣,這本詩集的誕生同樣具有幸運的色彩。在編書過程中,我萬分感謝伊庭的鼎力協助,讓這本詩集的遠行多些祝福。因為我相信善緣促成的東西,最能承受時間風雨的考驗。詩歌在時間中試煉我,我在時間中歡喜接受,並在迎受的愉悅中得到復活。
邱振瑞 二○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