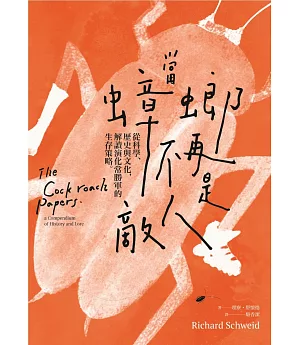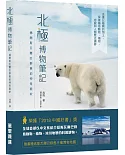作者序
我在1999年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常被人問道,為什麼要花時間寫這麼噁心的東西?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單純的想望,我想了解這種無所不在的昆蟲,以及牠們的演化史,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人類不會特別記起大部分平凡的日常生活,某天、某星期,甚至是某個月,可是多數人會永遠記得自己和蟑螂邂逅的那一刻。自詡「文明」的人類,由於對蟑螂發自內心的厭惡,因此只要看見蟑螂,多半都會深深烙印在腦海;也就是說,幾乎每個人都有精采、卻又毛骨悚然的蟑螂故事可以分享。
我對蟑螂感興趣還有一個原因:人類和蟑螂已並肩走過了漫漫長路。早在人類出現之前,蟑螂就已存在;我們跟蟑螂從未分開。就算有天人類從地球上消失,蟑螂也不太可能跟著一起滅絕,至少不會立刻滅絕。蟑螂比我們強韌,生理構造的設計也更適合生存。
最後一個原因是,蟑螂永遠不會退流行。書通常都有所謂的保鮮期,許多話題的壽命短暫,幾十年內就會大幅變換;讀者的口味也會改變,話題因此失去吸引力;還有一種情況是,新的發現讓既有想法和著作變得過時。但以上各種情況都不會發生在蟑螂身上。今日與蟑螂有關的事,很可能到了明天、明年或下一個千禧年都差不多,與最古老的人類遺骸相比,蟑螂存在地球的時間是人類的10倍;牠們在這350萬年之間,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在本書中關於蟑螂的描述方式不一定永遠不變,但是蟑螂低調的行為,而且幾乎什麼都能吃下肚,光憑這兩個了不起的生存策略,就讓牠們不太可能消失或大幅更動,至少不會那麼快;也許偶爾會出現微小的基因突變,但演化上的基本結構永遠都是一樣的。
不過在我寫書的這20年來,我的人生改變了、銀行存款變多,但是膝蓋越來越衰弱,我已不是當時的我了。那些曾造訪過、或被蟑螂肆虐的地方也不再相同;書裡出現的場景,現今已不同於下筆為文的那時。不過整體而言,現在的世界差別不大,某些地方迎接和平,另個地方卻爆發戰爭。
由於書中提及的一些情況已改變,特此說明:美國富樂公司(H. B. Fuller)已在拉丁美洲市場停售具成癮性的鞋用黏膠(對其成分甲苯上癮的街童,不難找到其他黏膠繼續大吸特吸);紐約市房屋管理局在公共住宅使用誘餌膠的比例大於殺蟑噴劑;2013年環保署更加嚴格規範殺蟲劑對人體的影響測試;優秀的蟑螂研究者路易斯‧羅瑟(Louis
Roth)於2003年辭世。遺憾的是,有些情況依舊:墨西哥華瑞茲城的女性死亡率仍居高不下;西撒哈拉尚未簽署永久和平協定;蟑螂排泄物引發的兒童氣喘比例持續上升。
關於蟑螂的研究從未停滯: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等機構,以遠端控制蟑螂行為的研究,幫助地震倖存者。一種稱為日本蜚蠊(Periplaneta
japonica)的強悍蟑螂,原本只出現在東亞,但牠們2013年搭便車抵達曼哈頓,現在正安頓在空中鐵道公園附近。此外,科學家也持續以蟑螂為實驗對象研究各種現象,舉凡一天中哪些時段最適宜學習(范德比大學)一直到DNA圖譜(洛克菲勒大學的全國蟑螂計畫,邀請公民科學家幫忙收集2004年到2012年的資料)。資深研究員馬克‧斯托克(Mark
Stoekle)審閱後者的初步結果,認為「這是了解蟑螂社會的窗口,且蟑螂社會與人類社會非常相似。」
相較之下人類跟蟑螂之間的變化就顯得微不足道了。隨著人類殺蟑武器的研究持續獲得資助,更高超的殺蟑方法也不斷問世。不過,蟑螂在突變後就會產生新的抗藥性,新的殺蟑方法往往在幾年內便失去效用。人類與蟑螂之間緊張的共存關係早已持續數萬年,從未因頻繁的小衝突而趨緩。
然而對一些地方來說,花錢研究蟑螂的大小事簡直不可思議,因為他們的錢僅能(甚至不足以)餬口維生,也因此不得不與蟑螂一起生活。已開發國家的民眾有足夠預算採買殺蟑武器,他們經常使用經濟實惠的殺蟲劑或是除蟲粉。不過,專業除蟲人士幾乎只用誘餌膠,雖然價格稍貴,但對人類較無害,效能也比較好。
儘管殺蟑方法日新月異,但是人類在這場戰役中並未佔上風。每當人類研發出更有效的殺蟑方法時,蟑螂通常也會以快速突變來對付新藥的毒性。例如本來有種葡萄糖可以引誘蟑螂吃下毒餌,但在佛羅里達州有個品系的德國蟑螂,五年內就對這種葡萄糖產生厭惡感。密西根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也在另一種蟑螂身上發現一個突變基因,能讓牠對除蟲菊精類(pyrethroids)的殺蟲劑產生「全方位抵抗力」。2013年10月的《經濟昆蟲學》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Entomology)就指出,許多從野外採集到的德國蟑螂都已具有多重抗藥性,包括氯化烴(chlorinated
hydrocarbons)、有機磷(organophosphates)、胺基甲酸鹽類(carbamates)、除蟲菊精類、苯吡唑類(phenylpyrazoles)與噁二嗪(oxadiazines),此研究的作者推斷:「殺蟲劑的抗藥性已成為害蟲防治業的一大難題。」
蟑螂能夠快速突變並對抗各類殺蟲劑,這已經很煩人了,偏偏人類用來殺蟑的武器,對自身造成的傷害甚至超越蟑螂。例如,最近有研究證實,如果讓第三孕期的孕婦接觸除蟲菊精類殺蟲劑的某些成分,可能會導致嬰兒出生後心理發展遲緩。其他類型的殺蟑劑也沒有比較安全:有機磷與N—胺基甲酸甲酯(N-methyl
carbamates)可能傷害兒童的神經系統。畢竟無論哪一種殺蟲劑,目的都是阻斷蟑螂的神經系統,使其維生器官失去功能。能對這種強悍生物造成傷害的東西,絕對是少碰為妙。
儘管現在有殺蟑噴劑、誘餌膠、水蒸式殺蟲劑與毒餌,但我們的滅蟑技術並未大幅超越前人。例如數千年前祈求庫努牡神幫忙對抗蟑螂的古埃及人,或是1624年被蟑螂圍困的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他在維吉尼亞殖民地寫下:「有一種印地安甲蟲,西班牙人稱之為caca-roche,牠們會爬進箱子裡啃食箱子,留下難聞的糞便。」
今日,人類被蟑螂夾攻的場景不輸當年,然而這僅是人蟲大戰的一部分,自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以來,戰役從未止歇。在20世紀銳減的床蝨(Cimex lectularius
L.),近20年來又在西方世界重振旗鼓,再度佔據人類的床墊,而且貧富不拘,從五星級飯店到遊民收容所,只要有人躺下的地方就有床蝨。這可能與兩個因素有關:旅行的人變多,以及牠們對殺蟲劑的抗藥性變強。這起反撲,彷彿是為了證明,人類一時的勝利只是過眼雲煙。
相較之下蟑螂顯得稍微親切,雖然蟑螂不反對啃咬人肉,但是牠們不會像床蝨那樣吸食人血。更討厭的是,床蝨等待食物的耐心勝於蟑螂,床蝨可以不吃不喝長達數月,等待人類自動獻上溫熱鮮血。一旦被床蝨叮咬,會癢得讓人抓狂,但是跟蚊子散播的致命疾病或是發燒相比,發癢似乎不值一提。從昆蟲對人類身心健康的威脅看來,人類大概會持續向昆蟲宣戰,直到其中一方從地球消失為止。幾乎不用懷疑的是,最後的贏家不會是人類。
儘管我們把蟑螂視為勁敵,卻能從牠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比如說,研究蟑螂構造大幅提昇了人類對自己的認識。實驗室裡,無數隻美洲蟑螂遭到肢解,只為讓研究人員藉此更加了解人類的生理功能與神經系統。蟑螂的構造雖然簡單,卻擁有超高效率,在在啟發了科學家。蟑螂跟人類看似天差地遠,但卻能帶來許多可應用於人類的發現。貝爾塔‧沙瑞(Berta
Scharrer)是神經內分泌學的創立者之一,亦曾獲諾貝爾獎提名,她就是用蟑螂做實驗。她曾寫下:「這種動物生性節約,生命力旺盛,在實驗室裡奮力求生,對空間的要求很低。」
蟑螂對人類的啟發不僅限於神經學與生物學,不只是我們將其肢解、尋索生命構造時的發現,蟑螂也教我們保持謙卑,牠們不斷點醒我們,人類無力抵抗微小生物。雖然我們有能力「濫用」智慧,想出「越來越可怕」的方式廝殺,但人類的力量絕對有限,畢竟一隻蟑螂就能嚇倒我們、一隻床蝨就能折磨我們、一隻蚊子就能殺死我們。
蟑螂時時提醒我們,在平凡生活的邊陲角落,存在著另一個世界,那個陰暗空間的規則與人類世界大相逕庭。蟑螂以動物本能、靈敏反射及狹小空間建構的現實,與截然不同的人類生活相互交織:水槽下、冰箱後、水管內,甚至是在踢腳板與牆壁的夾層。潛伏的蟑螂也代表每個人藏在外表之下,不願呈現的卑劣思想與感受。我們都知道,如果否定它們的存在、壓抑這些黑暗的欲望,下場可能會很悲慘……同理,視而不見也無法消滅蟑螂。
正因如此,我們應該多多關心這群長伴身旁的伙伴,仔細觀察蟑螂能讓我們看見一個令人著迷的世界;這個世界看似貼近,卻又如此遙遠。希望這本書能繼續發揮類似百科全書的功能,並落實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標:為讀者呈現驚奇又美妙的蟑螂世界。
理察‧舒懷德
巴塞隆納,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