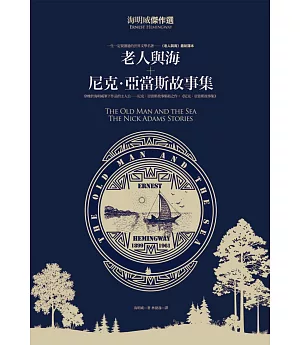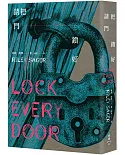導讀
激流中的孤島──海明威的悲劇英雄文學
將時代的乖離和生活的痛處,理解為終究徒勞無功、一無所得的克服與超越,將人類冒死以換取自由尊嚴的生命歷程凝結在小說情節中,向人類展示一種「知之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生態度;將生存的虛無性、個人的悲劇性和時代的荒謬性,體現在一系列風格獨特的作品中,是恩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留給世人最珍貴的文學遺產。在來不及洋溢青春的唯美就過早承受死亡的陰影,這塑造了海明威的創作背景;不斷的求生卻逃離不了死亡的威嚇,是海明威前後一貫的作品主題;一幅荒野獵客、人中硬漢的外形卻內藏悲憫蒼涼的內心世界,是海明威留在世人記憶中的作家形象。在海明威逝世近半個世紀後重讀他的作品,其對人生意義探索,對生命哲理的和體悟,應驗了「歷久彌新」這句格言。
海明威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橡園鎮(Oak Park, Illinois),一個位於芝加哥不遠的社區。母親教授鋼琴和發音課程,父親克倫恩.海明威(Clarence
Hemingway)是一位醫生,他在海明威二十八歲時舉槍自殺,父親不明的死因給年輕時的海明威留下深刻的創痛。橡園高中畢業之後,在堪薩斯市擔任「星報」(Star)記者。一戰期間,前往歐洲戰場,在義大利前線擔任紅十字救護車司機,在一次位於皮耶佛河邊(Piave
River)的砲彈襲擊中腿部受到重傷,光是從腿上取出的彈片就高達兩百三十七塊。海明威在米蘭的醫院中治療了二十個月後返回美國,但從此得了嚴重的失眠和恐懼症。一九二一年在美國知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介紹之下,與哈德莉.李察德森(Hadley Richardson)結婚並遷居巴黎(1921-1926)。在此期間擔任「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記者,在知名作家龐德(Ezra Pound)、史坦恩(GertrudeStein)等人鼓勵之下,開始嘗試散文寫作。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裡》(In Our Time ),從此走上作家之路。
一九三七年海明威前往西班牙,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海明威以記者身份支持政府軍一邊,許多以鬥牛為主題的短篇小說在此期間應運而出。二戰期間,海明威積極參戰,是一位英勇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員。二戰後,海明威住在古巴的哈瓦那,專心寫作,並根據西班牙內戰經驗,寫出了二十世紀經典名著《戰地鐘聲》(Foe Whom the Bell Tolls )一書,一九五四年以《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Sea )一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聲望達到顛峰。獲獎之後,海明威前往東非,途中發生飛機墜機事件,海明威再次身受重傷。卡斯楚取得古巴政權以後,海明威離開古巴返回美國的愛達華州,但酗酒和嚴重的皮膚病使海明威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病痛日益加重。一九六一年,海明威在自己家中以那把心愛的獵槍自殺身亡。
早熟的憂傷 生命的迷惘
一戰經驗,是海明威創作的緣起。人性的暴虐在殺戮戰場上狂亂的渲洩,無數青春生命在煙硝砲火中悄然消逝,戰爭傷患在病榻中痛苦的呻吟和嚎叫,聲聲撕裂了愛國軍人天真的幻想,一封又一封沾染血跡的家書記錄著無望的鄉愁,這一切,這一個悲慘時代的死亡世界,將年輕的海明威塑造成一個憤世嫉俗與哀傷主義的作家。
《我們的時代裡》(一九二五年)雖是一部篇幅單薄的短篇小說,但已預示了海明威後期作品的「原型主題」。故事以尼克.亞當斯(Nick
Adams)的「成長史」為軸線,從少年到青年,從參加戰爭到戰後返鄉,以及最後獨自回到孩童時代生長的地方,通過對痛苦、暴力、死亡最直接、最震撼的體驗,由一個脆弱、靦腆的小男孩到成熟、世故的男人。作品始終散發一種早熟的憂傷、血淚交織的領悟、如影相隨的困惑,反映出那個時代人們的迷惘與失落。實際上,尼克.亞當斯就是海明威的「化身」或「身影」,他不斷重現在後來的作品中,扮演海明威生活自傳的第三敘事者身份。在「印地安人營地」(Indian
Camp)一篇中,尼克見到醫生父親在沒有使用麻醉藥的情況下,用一把大折刀為一位印地安婦女進行剖腹生產,他親眼目睹了父親用九英尺長的細線縫合傷口的野蠻場面,印地安婦女的丈夫因不堪忍受手術給妻子帶來的痛苦,用剃刀割斷自己的喉管,將自己裹在毛毯裡。年幼的小尼克體認到,人生是一場生死相搏的戰場,歡樂與痛苦交雜、希望與失落交錯、愛情與野蠻相隨,既無法閃躲也無法逃避。末尾,尼克問他的父親:「死會很難嗎?」父親回答:「不,我認為很容易。」。這句意味深長的簡短對話,預示了父子都將以自殺告終。海明威的創作主題和人物命運,一開始就是以「生死一線」的嚴酷選擇為起點。實際上,尼克的父親,一位喜歡打獵、釣魚並與印第安人建立友好關係的紳士,正是海明威一九二八年自殺的父親縮影,尼克則是一九六一年海明威自殺事件的預兆。
二心:從復原到超越
《在我們的時代裡》以兩篇「大二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作為結尾,這是短篇小說集中最重要的篇章。歷經戰爭創傷的尼克從歐洲戰場歸來,回到密西根州錫尼(Seney)鎮,獨自一人重遊兒時故居。這時候的尼克已經不是「印地安人營地」時期那個天真無邪、懵懂無知的小男生,而是一個歷經滄桑、身心俱疲的成熟男人。然而尼克的返鄉,不只是一趟回家之路,而是一場「心療之旅」,一個戰爭傷患藉由重新投向自然的懷抱,藉由對自然生物「擬人式」的關愛,而獲得精神境界的清洗和沉澱。
「大二心河」雖然只是一個釣魚的故事,卻預示了海明威後來作品的原型主題,那就是不斷通過對自然的挑戰來證明自然的強壯和人類的渺小。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大海、森林、雪山、草原、小河,都是人的精神形式的擬像物,是人的精神變化的隱喻指標,從中折射出個人不同的人生階段和不同的精神層次。而悲劇則是指人的「有限性」(human
limits)。海明威對自然的生命力量有著深刻的描述和體會,因為內含在自然中那種通過不斷自我調適和包容痛苦以獲致永恆性的那種力量,正是人類永遠無法達到的境界。自然從不墮落,永不邪惡,所以自然不會失敗,永不屈服。
《老人與海》:人類精神的寓言書
一九五二年根據真人實事、寫於古巴哈瓦那的中篇小說《老人與海》,是海明威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文風簡潔、字字珠璣。小說還被拍攝成電影,由安東尼.昆(Anthony
Quinn)主演。小說不僅徹底駁倒了《過河入林》出版後一群認為海明威才華已經乾枯殆盡的評論家,而且獲得了一九五二年普立茲文學獎和一九五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對比於先前的《非洲的青山》,歷經滄桑的海明威更趨於成熟和睿智,他從一個「狩獵人」成熟到一個「人類家」。從文學史來說,《老人與海》已經不只是一部關於「老漁夫打魚」的故事,而是一種象徵、典故和紀念,它不僅是一部人人必讀的勵志文本,作為一種崇高的人類精神形式的展露與表達,《老人與海》已經和海明威的個人聲望一起深植人心,永垂青史。
儘管海明威並不同意人們把《老人與海》看成是一部象徵主義小說,但這部小說也不僅僅是一部「討海日誌」,而是一部關於人類精神形式的寓言敘事,而這一精神形式的主題正是悲劇英雄主義,它表現在老人堅信「人不是為失敗而生的」、「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給打敗」
的信念之上。漁夫「聖地牙哥」不是一個普通的打魚人,而是一個「人類鬥士」。「老人枯瘦憔悴,後頸上滿是深深的皺紋。臉頰上的褐斑是不會致命的皮膚病變,那是熱帶海洋上陽光反射造成的。」。但老人很勇敢、很堅強。對老人來說,這三天的出海,是他一生最後的戰鬥,他要向男孩證明自己依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知道自己天生就是個漁夫,他決心要「航向遙遠的地方」,「待在黑暗的深水裡」,他要在一個孤獨無人的海域上,單獨面對他的對手,證明自己、考驗自己。在等待馬林魚浮出水面準備與之奮力搏鬥時,他為他「抽筋的左手」感到懊惱,因為這將使他的搏魚失利,他把抽筋看成是「對自己身體的背叛行為」,用西班牙語「calambre」來說,是丟臉的事,這意味著老人痛恨懦弱、厭惡逃避和投降。聖地亞哥是一個人類英雄的典型,是耶穌受難者的化身,但英雄與暴夫的差異就在於,暴夫的目的是在征服他人,英雄是為了戰勝自己。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所長
宋國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