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活於浮世,乃有物哀
一
話說二○一二年底,我忽爾覺得閒得發悶,於是再到媒體上班;有一份報章容許方太初撰寫時尚與文化的專欄,名為《浮世物哀》,她所寫的正是衣飾與文化的「越界之思」—從衣飾到日常之「物」,從文化、抗爭、電影、音樂、繪畫到詩,我每回簽核大版,都會驚覺她的文字每有一些稍縱即逝的日常微光,如今成書了,重讀之時猶約略有點雖在堪驚。
《浮世物哀》每每在有意無意之間開顯不同地域的文化交錯,當中有衣飾的「根」(roots),遍佈文化交流的「徑」(routes),而兩者交互辯證的,如今想來,豈不就是文化想像的「越界之思」嗎?
「根」,說來大概恰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所論的「地下莖」(Rhizome),在大地之下,廣伸著無定向的「徑」,交匯而成永不止息的城市文化游擊戰—也許不必深究「徑」(或「莖」)是甚麼,讀者諒可想像,《浮世物哀》所書寫的正是開放而縱橫散瀉的地下空間,所指涉的文化系譜亦非「純種」,倒是混雜著廣義的文化變體—有所啟蒙,交融、啟發,由是蔓莖處處延伸,無有終極。
時尚萬變,然則始終不離其宗,信是人與衣、與物無數瞬間的凝視(gaze),時而緩慢,有若「會登凌絕頂」而「一覽眾山小」;時而急驟,有若「亂石穿空,驚濤拍岸」而驟然「捲起千堆雪」;時尚之為「物」,總是與時俱變,或如方太初所說的「衣之皺褶與迷宮之城」:一切衣飾之「皺褶非平滑,所以不是一,而是眾多細細的褶痕,細細的漩渦,收納著陰影,也收納著你所不知道的奧秘」;是以世間萬物,皆為皺褶,「如蝴蝶折疊成毛蟲,毛蟲伸展為蝴蝶。種子舒展其褶則長出了樹,我們的大腦打褶,所以收藏回憶與思想」。
我其實不大懂得時尚,心想,那該是衣飾的想像吧,因而想起,法國理論家所鍾愛的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剛好有此說法:「想像就是轉譯內在源源不絕的低吟聲,讓創意聽到它的回音。」時尚美學的散播亦作如是觀,於文化與想像的交匯之處,每有想像力的傳輸轉譯,隱隱然構建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論說的「辯證影像」(dialectical
image),展現出多重交錯的意義:「過去與現在恰如閃電般交匯而成星陣」,「辯證影像」也者,則是「由疏離之物與正在到來但也正在消失的意義所組成的星陣」,在所有意義失去界限的瞬間,總是對觀看者的想像力多所考驗。
時尚乃是不同風格、物料與文化的拼貼組合,所有影像俱可在一瞬間掙脫歷史之覊絆與限制,故此亦必然為緊貼時代的產物,從而探究如何掙脫城市消費的覊絆與限制,重新構建身體與慾望的想像力;方太初每從微物說起,比如有感於在電影《胭脂扣》片尾,「如花對縮在角落、早已老去頹敗的十二少說:『這個胭脂盒我掛了五十三年,現在還給你,我不再等了』」,盒中有一個小吊墜,揭開,內有小鏡,「還有如璀璨年華般的胭脂」,當中所收藏的,「是浮光掠影裡的舊時夢,也是繁複龐大、體系複雜的歷史裡,承載個人小史的遺物……」
《浮世物哀》老是嘗試穿越不同的邊界而恍然有悟(或乾脆執迷不悟),比如從藤田嗣治的故事,說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巴黎畫派」(Ecole de Paris),再說到貓與狐的心象;又比如從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說到本雅明,從時裝設計師亞歷山大‧麥昆,說到瑞士畫家保羅克利(Paul
Klee),繼而再說到鏡子的隱喻:「麥昆擅於把兩種相反的特質揉合在一起,這樣在一體中互有矛盾的最佳例子就是鏡子」;波德萊爾將玻璃匠叫上樓,質問他為何「沒有讓人把人生看成是美好的那種玻璃」?
二
時尚萬變,或如張小虹所言,總是關乎穿衣者的「幸福與沉淪,相識與離散,因輾轉,或繾綣,衣服堆裡日月長」;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嘗言「凡是女人皆為戀衣狂」,如此說來,一切的「壓抑」(repression)、「否認」(disavowal)乃至「無視」(scotomization),都無法擺脫迷戀之物;是以張小虹有此說法:「衣性戀者的精神分裂,也分裂在深情與嘲諷的距離擺盪。理論與耽溺、批判與濫情,往往是一體之兩面、矯枉而過正」,因此時尚大師所言說的大都會,大概都有越界的意思吧,他們「談跳蚤市場舊衣慈善店,談復古懷舊千禧未來風,都是這些年來流目顧盼的深情所託,想從衣飾窺看大千世界……」
「時尚」之「時」,許是希臘文化所說的「史」,就像本雅明所言:「時尚確定了商品希望被人崇拜的方式……同時擴大了它對日用品的左右能力,就像把時尚的統治延伸到宇宙一樣」,超乎日常需求(need)而源於欲望(desire);或一如蘇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所言:「時尚規定了儀式,通過它使商品被崇拜……時尚以活潑的儀式慶祝新奇,而不是循環,在當中人們不需要記憶……時尚是藥劑,在公眾的範圍內彌補了遺忘過去的巨大影響。」
蘇珊‧巴克―莫斯也提及本雅明的觀點:「時尚不僅是現代時間的尺度,它展示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聯繫,這是由商品生產方式的改變而帶來的新法則,在時尚中商品的幻覺效應和外表緊密聯繫。」是的,本雅明嘗言,過去的時代存在著很多不曾兌現而等待相認的期盼,故此時裝遺留了諸多秘密標示,乃有好一些堪可解破歷史的線索,乃有將之解開以尋找烏托邦的可能。
三
時尚萬變而千面,猶如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小徑分岔的花園》(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所言,時間乃是一座迷宮,「因你每作一個決定,時間就分岔開去,你前方的命運也就不同了,如像迷宮般有了各種可能」;由是方太初寫道:「那麼城市呢?此城如此小,但無論人心、街道皆如迷宮,兜兜轉轉,那就不妨想,我們不是坐困愁城,而是開放了無數可能性,那些皺褶一直延展,讓我們思索,讓我們兜轉,讓我們成了那隻手,在人生之衣上捏起皺褶」。
博爾赫斯所述說的迷宮許是彌賽亞(Messiah)一樣的歷史—某些時刻的某些事情必須被救贖,被圓滿或不圓滿地完成,或被審判,或如走入或走出不同的迷宮,皆因彌賽亞歷史一如迷宮,所有歷史時刻俱可能有不同的彌賽亞降臨或已然降臨,如同人生之衣延展著各種皺褶。
此所以方太初也有此說法:「時尚總是承諾著未來的鏡像(你穿上時裝就會變成怎樣、你穿故你在),西西里乃「叛逆南方小島」:「當地或許曾遭受多種入侵、多種拉扯,但無妨當中世代而活的人,至今依然保有自己的身份與個性,也許這就是這個叛逆的南方小島最為可貴的精神」,再讀下去,也許就可以解破時尚如何顛覆王室形象,如何諧謔宗教權力吧。
在《浮世物哀》,時尚不僅僅是「衣道」,更是「物道」,當中老是牽纏著藝境的想像:諸如電影、音樂、舞蹈、繪畫、抗爭與詩;在方太初看來,萬物總是與人相近,猶如衣之別針或鈕扣,互為穿透或通融,比如她曾引述波蘭詩人賀伯特(Zbigniew Herbert)一首叫〈鈕扣〉的詩:「只有鈕扣從不屈服/目擊罪行而克服死亡」,是故鈕扣從不屈服,一切抗爭亦從不屈服。
方太初筆下的舊衣暗藏「垢之明暗」,故亦旁及日本的幽玄美學、陰翳禮讚,乃至攝影師奧諾黛拉(Yuki Onodera)《舊衣畫像》(Portrait of Second-handClothes)的光影體驗,那就恰若蘇軾所言的「萬人如海一身藏」,當中說到波蘭青年攝影師維爾尼克(Natalia
Wiernik)的系列作品,說到「就是關乎人如何淹沒於大背景之間」,最終則說到「舊衣堆成一座山,用一架紅色的吊臂車,將舊衣吊起又拋下,當舊衣落在山堆上,它就只是當中無名的一件,如千千萬萬其他舊衣一樣。但當它在空中舒開之時,它的獨特性、它曾經的故事,才忽爾展開」。
她有時從一張空椅子說到「物道」,比如援引梁秉鈞的〈靜物〉:「本來有人坐在椅上/本來有人坐在桌旁/本來有人給一盆花澆水/本來有人從書本中抬起頭來」,然後,「人去樓空,椅子、桌子、花盆、書本全都靜默」,〈靜物〉於是追問悖理的世界:「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
在〈瘋癲與時尚〉一文,方太初寫得特別有意思:「瘋癲是一個統一的詞語,在這詞語下大多人的面孔都被歸類為一種(一如在「正常」這標籤下,我們都失去自己的臉孔)……」許是她早已意識到時尚乃齊美爾所論的「精神生活」,當中亦不免滲透了城市的憂鬱與焦慮,因而每每浮現出意想以外的震驚,或失神。
四
這就明白了,難怪《浮世物哀》這本書的啟首,援引了齊美爾在《時尚的哲學》的一段話為引子,當中或可透析時尚與「精神生活」的某些洞見:「時尚的問題不是存在的問題,而在於它同時是存在與非存在;它總是處於過去與將來的分水嶺上,結果,至少在它最高潮的時候,相比於其他的現象,它帶給我們更強烈的現在感。」
齊美爾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_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說得好,大都會街道縱橫,高速而多面向,將大都會與鄉鎮的精神生活區分:「為了適應變化以及各種現象的比照,理智並不需要任何衝擊和內部劇變,它只是利用這些劇變使得更保守的心理狀態可以適應都市生活的節奏」,城市人的生活正是無數變種的綜合體,因而「發展出一種器官來保護自己不受危險的潮流」,乃至棲居其間之人免於被毀滅性的外部環境所威脅,幸存者也許就只能以「頭腦代替心靈來作出反應」。
方太初書寫時尚與文化,以另類觀點論說呂碧城、蕭紅、張愛玲等民國女子,也旁及她們的「衣道」與「物道」,乃至「精神生活」,她也許不會忘記,張愛玲在〈更衣記〉曾這樣說:「古中國的時裝設計家似乎並不知道,一個女人到底不是大觀園,大多的堆砌使興趣不能集中,我們的時裝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
民國女子的時代早就遠去了,幸或不幸,方太初存活於現今的「浮世」,認識「物道」,於是乃有「物哀」(Mono no aware)—「物哀」也者,那就是對「物」(mono)有所感而有所哀(aware),從而對「侘寂」(Wabi
Sabi)之真相,多所體會而多所闡發:殘缺、無常、不圓滿,乃有此說法:「由是將『物哀』與侘寂美學放在時裝上,穿衣者是主體,衣與物是客體。穿衣者以衣飾體現生死哀戚,如同物哀」。
方太初又說到電影《東尼瀧谷》,「與日和民族的『短暫美』一脈相承」,時間流逝,無有盡期,「體現在時裝上,是另一種物哀觀」;她嘗試穿越穿衣者的「衣道」與「物道」,穿越一切的生死哀戚,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她與浮世萬象無數瞬間的「凝視」—時時刻刻與人、與物、與詩、與藝境多所「凝視」,互有所感而互有所悟,乃有《浮世物哀》這本書。
葉輝




















![現代美術[季刊]NO:200期[110/03]](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8%2F92%2F0010889265.jpg&width=125&height=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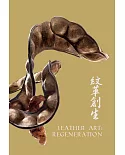
![現代美術[季刊]NO:201期[110/06]](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9%2F73%2F0010897333.jpg&width=125&height=155)

![2021桃源國際藝術獎[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90%2F14%2F0010901421.jpg&width=125&height=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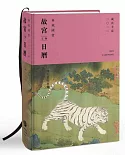





![工藝製造現場 第一話:鍛・練[線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90%2F14%2F0010901427.jpg&width=125&height=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