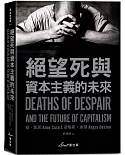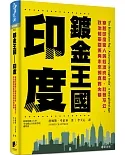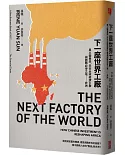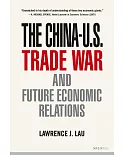推薦序
不可諱言地,全球化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問題。多數問題被視為是全球化所產生的副作用。然而,根據本書的作者,許多問題不是來自全球化本身,而是其他不良政治體制藉由全球化的機會圖謀利益所造成,這些政治體制覬覦全球化所造成的繁榮,運用不正當的手段壓榨勞工,形成血汗工廠。全球化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良的政治體制才是。如果沒有全球化,它們也會以不同的方式與面攫取不正當的利益,全球化反而讓其惡行曝露並賜與改正的機會。事實上,全球化的深化反而可以解決這些弊端。例如勞動標準的趨同是全球化的結果之一,它會迫使血汗工廠改善勞動環境。所以,當我們在批判全球化時,必須明顯的區分那些是全球化導致的現象,那些現象反而是因為阻礙全球化所造成。
除了本書所提出的血汗工廠外,有些國家因為政治極度腐敗與社會動盪,因而被排除在全球化的過程之外,它們甚至連建立血汗工廠的機會也沒有。這些國家多屬非洲國家,在其他參與全球化國家享受經濟繁榮時,它們的經濟停滯造成與其他國家的貧富差距加大,此亦被認為是全球化的負面效果之一。但與血汗工廠一樣,造成國與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各國的政治與社會體制。但這並不是說,全球化就完全沒有缺點,它明顯的使參與全球化國家國內貧富差距擴大,這必須依賴各國的社會福利政策來改正。
本書作者提出獨特的見解,以生動的案例告訴讀者,全球化背負了不該背負的罪名,她不但找出真正的嫌疑犯,為全球化洗脫罪名,還提供血汗工廠問題的解方。由於全球化洪流太過巨大複雜,一般均習慣不加思辨的將與全球化相關的現象歸因於全球化。尤其對具有反全球化意識形態的人士,將全球化視為所有罪惡的源頭,卻不知道全球化是造成人類進步繁榮的最主要動力。全球化強化不同地域的人民間的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交流,讓一些隱藏的黑暗無所遁形。儘管它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效果,但都不值為了修正這些效果而阻礙全球化的進行。
趙文衡/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寫在前面
受抗議學生驅使,一名商學教授環遊世界
一九九九年二月寒風凜冽的一天,我看著一群約百餘名的學生,聚集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校區中心的哥德式建築──海利大會堂(Healy
Hall)前階梯上。他們慷慨激昂、鼓譟不休,校警在人群外圍來回巡守,以防萬一。這群學生確信自己品行端正,懷著一致的使命感;在面對錯綜複雜的迷惑時,能清楚判視黑白、分辨善惡。大企業、全球化、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惡棍,無情地摧毀世界各地勞工的尊嚴與生計。不久之後,五萬多名有志一同的激進者湧向西雅圖的WTO年會;到二○○二年IMF世界銀行會議召開之際,抗議群眾激增至十萬人。而壞蛋們在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和義大利熱那亞(Genoa)的集會,也受到反全球化行動主義人士百般阻撓。二○○三年在墨西哥康昆(Cancun)的WTO年會,又有新面孔加入──一個新開發中國家組織的代表;世界貿易會議也因嚴重貧富差距問題不歡而散。反全球化行動人士分別來自:大學校園、工會、宗教組織、歇業紡織廠、人權團體,以及非洲的棉花田。這些人全部集合在一起,堪稱是全球化的「後座力」。
起初,這股後座力使現存體制大吃一驚。就連左傾的《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似乎都對西雅圖那場「大屠殺」百思不解。「那究竟有何意義?」隔天他們在社論版上這樣問。從IMF大廈的高層辦公室俯瞰,樓下的烏合之眾是群本意良善,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蓄意阻撓者,堵住通往繁榮的唯一路徑。以傳統經濟智慧觀之,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明明就是窮人及被壓迫者的救星而非殺手,這股後座力怎麼就是搞不清楚狀況?截至二○○四年為止,世界貿易會議已將近五年沒有實質的進展。
不過幾乎在同一時間,這群搞不清楚狀況的經濟文盲,叫囂的音量竟然變小了。「唷!」商業體制似乎在說:「真高興那結束了。」但仔細查看便知,事情沒有真的落幕;相反地,反攻已經開始。儘管一些最瘋狂的口號(如「資本主義是死神」)已經消失,後座力非但沒有消退,反倒變成主流。過去只會出現在海報上或歌曲裡的議題,現在公然在國會殿堂、全球貿易談判會場,甚至是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會中討論起來:自由貿易對互惠貿易、國外代工、勞動和環境標準、貿易協定,還有範圍更廣的:富國對上窮國,富裕美洲人對上貧窮美洲人。雖然貿易議題在美國的歷史上鮮少獲得大眾青睞,今天卻儼然成為政治、經濟與道德論述的焦點。
回到一九九九年的喬治城,我看到一位年輕女孩抓起麥克風。「你身上的T恤是誰做的?」她問群眾:「是成天跟縫紉機銬在一起,沒得吃、沒得喝的越南孩子?還是每小時工資一角八,每天只能上兩次洗手間的印度少女?你知道她的房間擠了十二個人,沒有自己的床,只有稀得像水一樣的粥可以吃嗎?你知道她每星期被迫工作九十個小時,而且還沒有加班費嗎?別說是加入工會,你知道她連大聲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嗎?你知道她不只窮,還活在髒亂疾病之中,而這全都是為了替耐吉(Nike)賺錢嗎?」
這些事我一無所悉,不禁對拿麥克風的年輕女孩感到好奇:她怎麼知道的?
於是,接下來的七個年頭,我踏遍世界尋找答案。我不只找到我身上的T恤是誰做的,也跟著它的製造過程穿越千里、跨過三個大陸。這本書講的就是創造棉質T恤的人物、政治和市場的故事,一個全球化的故事。
或許有人會問,對於現今全球貿易的辯論,單單一件商品的「傳記」能有什麼幫助?就一般情況而言,說商業及經濟研究方面的故事已不合時宜。我們從故事中學不到什麼教訓,爭議仍然存在,因為故事只給我們「軼事」類的資料。以廣為現代人接受的方法論智慧來看,在某時某地確實發生的事情──故事或軼事──可能深具娛樂性,卻不具知識意義:故事無法讓我們系統化地闡述理論、測試理論,或進行歸納。如此一來,今天的研究人員擁有更多資料、速度更快的電腦和更好的統計方法,然而個人觀察的心得卻愈來愈少。
當然在其他領域,故事扮演的角色就比較受人尊敬。理查‧羅德斯(Richard Rhodes)在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作品《原子彈的製造》(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一書中抽絲剝繭,一層一層地探討原子彈發明的過程,以此闡明一群高智商人士在工作上的智力發展。蘿芮兒‧尤瑞奇(Laurel Ulrich)在《一個中年婦人的故事》(A
Midwife’s Tale)中,用一位看似平凡無奇女人的日記,建構二百年前緬因州(Maine)森林裡的生活,突顯一地的經濟、社會結構和物質生活模式,是無法套用在別處的。歷史學家羅伯特‧達塞爾(Robert Dalzell)則在《企業精英》(Enterprising Elites)一書中敘述美國第一批工業家的故事,看他們在十九世界新英格蘭(New
England)建立的世界,進而呈現工業化的過程。所以,故事,不管說的是一個人也好,一件事也罷,都不僅呈現一個生命或過程,更彰顯了孕育這個生命或過程的廣大世界。這也正是我這篇T恤故事的目標。
「這個世界還需要講全球化的書嗎?」這是賈格迪許‧巴格瓦帝(Jagdish
Bhagwati)新書的導言標題。(註1)嗯,這世界當然不需要再多一本以抽象概念批評全球化貿易或為其辯護的書,因為雙方面的論據均已闡述得夠強而有力了。(註2)我寫這本書不是要捍衛哪個立場,只是要說個故事。儘管T恤的故事會浮現若干經濟和政治議題,但那不是我的出發點。換句話說,我說T恤的故事不是要傳達什麼道德教訓,而是要找出「故事的」道德教訓,看故事會帶領我們走向何方。
當然故事中也灌注我個人的偏見,迄今這些偏見仍在我心。身為受過正統訓練的金融與國際經濟學者,我和我的同事都有那種多少令人倒胃口的傾向,相信如果每個人都了解我們所了解的──如果他們「懂」的話──就不會吵得這麼凶了。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發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倡導自由貿易已逾二百年,我們卻還在設法務必要讓學生、國人和共事者「懂」,因為我們相信,只要這些人了解,每個人都會認同我們的觀念。當我碰巧在喬治城遇到抗議事件、聽到這段對T恤的謾罵,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這個年輕女孩雖然本意良善、陳辭愷切,卻沒抓到重點。她需要一本書──或許就是這一本──來為她說明一切。但跟著T恤環遊世界後,我的偏見已不再那麼偏頗了。
長久以來,貿易和全球化的辯論都呈現兩極化:善對抗全球市場之惡。經濟學家普遍主張,國際市場競爭會捲起富裕之浪,(至少在最後)可頂起所有船隻;批評人士則擔心市場力量的無情效應,特別是對勞工的衝擊。他們尤其擔心服飾方面的自由貿易,很可能只會導致工資和工作條件呈螺旋型下跌,最後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書中描寫:終將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然而,以我這件T恤的一生看來,全球化倡議者和批評者都太看得起市場了。雖然故事的確受到競爭激烈的經濟市場影響,但T恤一生中發生的關鍵事件,和競爭市場的關係其實沒那麼密切──政治、歷史和刻意避開市場的策略才是重點。就算是對高度競爭市場讚不絕口的人,也不願親身體驗市場的強大威力,因此我的T恤一生各階段的「贏家」,擅長的更不是在市場裡競爭,而是避開市場。這些旨在逃避的策略對窮苦百姓的殺傷力,比市場競爭本身還強。簡言之,出乎意料地,我的T恤故事呈現的重點不是市場,而是一張由歷史和政治編織成、將市場困於其中的羅網。在揭開T恤一生的過程中──特別是與目前爭論不休議題有關的部分──我始終不得不去探討歷史背景和政治因素。
許多經歷過貧困的國家(如台灣和日本)都因全球化而富足安康,許多仍算貧窮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也不若以前那樣悽慘。然而,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大部分在非洲)並未霑得全球化的雨露。此外,在某些快速成長的國度(如中國)裡,也有許多百姓被遠遠拋在後頭。我的T恤故事正是說明:全球化在某些環境固然有可能提升財富,在其他地方卻成為「贏不了」的陷阱;似乎是政局不安定,或是政治、市場運作不良,注定了經濟失敗的命運。
我的T恤故事也呈現出,全球化辯論的反方(不管有意無意)也是改善人類生活條件不可或缺的一方。在現今爭論的濫觴時期,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提出著名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市場力量一方面是需求所致,另一方面又是社會保護貿易制度的產物。(註3)博蘭尼認為正反兩方恐無和解之一日。後來幾位作家──文筆最佳的應屬彼得‧杜赫提(Peter
Dougherty)──卻反過來主張「經濟學家只是廣大文明計畫的一分子」,市場的生存尚需仰賴各種形式的後座力。(註4)我的T恤故事即沿著杜赫提的說法發展:單是市場或後座力其一,都不足以為種棉花或縫製T恤的窮人捎來希望;雙方不自覺下的共謀,才能開創出前景。懷疑自由貿易者需要大企業,大企業也需要有人質疑,而最重要的是:亞洲被剝削的勞工和非洲的棉農,更需要這正反兩造同時存在。
我動筆寫這本書時,完全沒料到T恤的故事竟會和當代幾件最重要的經濟大事扯上關係:掌握紡織品貿易四十年之久的政權──從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的選舉政見起算──在本書完成之際終於斷氣,留給一個屬於失敗者的美麗新世界、少數大贏家,和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約莫同時,全球最貧窮的國家聯手發動一個大衛對抗巨人式的驚人行動,以全球貿易會議為人質,要脅美國提供農業補助,特別是對棉花,我T恤主要(或者該說唯一)原料的補助。九一一事件後沒幾天,在政府雷達螢幕下,T恤銷售和軍事援助這兩個不相干的議題,竟在布希(Bush)政府和巴基斯坦(Pakistan)一場詭異的協商中被綁在一起,顯示美國紡織業仍握有出人意表的權力。而中國,我T恤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也躍上中央舞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中國這個奇特的資本主義警察國家(police
state)像氣球一樣迅速膨脹,用低成本的進口商品淹沒美國,迫使美國每家公司不分大小都得擬定「中國策略」,對付「中國價格」或處理「中國威脅」,同時民主黨員和共和黨員無不努力解釋他們在「中國議題」方面的立場。
最後,從我第一次在喬治城大學碰到抗議事件開始,學生們以和平方式占領了學校校長室,拒絕讓步,直到校方及校服供應商答應處理喬治城T恤及其他服飾商品背後,那據傳的「血汗工廠」情況。全國數十所大學陸續有類似抗議事件上演;過去五年間,學生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士已徹底改變競賽規則,改變了全球一些大企業做生意的方式。多虧有這些後座力,今天的T恤故事才能改頭換面,比短短幾年前的故事更好。在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以為會寫出一個故事來幫助學生用我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了解市場在改善窮人生活方面的成效。我的確寫出這麼一個故事(但願如此),但那不能說明一切。在此,我必須對這些學生說,(現在)我了解你們為什麼會走這條路了。
現在我也更加了解這篇T恤傳記中的人物:尼爾森、露絲、蓋瑞、遠志、艾德、古蘭、蘇勤、穆罕默德、永芳、奧吉和派屈克。他們都是很棒的人,每個都很棒,能遇見他們是我三生有幸。希望每一個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有興趣的人,都能遇見他們。這本書瞠乎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