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溯古泛今觀戲,玩味翻嚼字裡
劉基(伯溫)的著名篇章〈賣柑者言〉,全文如下: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
這是《賣橘子的》劇名的由來。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相聲瓦舍】首演於新北市藝文中心。
當「文創」這個名詞被強調之後,定義愈發模糊了。本來,文化的精神,確實是多元、敦厚、寬鬆、融合,然而聰明的生意人,總能牽拖出對自己事業有利的解釋,迎合大眾口味,似乎成了「文創」的思維正確。
傳統相聲講究「短」、「小」、「精」、「悍」,尤其包袱(裡面裝著「哏」)的外皮,講究「一戳即破」。迎合清末那樣的時代,民智未開,教育不普及,生活皆由瑣屑事件拼貼,不涉及眼界、品味、思想,吟個詩詞、對個對聯、歪批戲曲小說,已算是「文哏」。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問世,為我等「失敗者的下一代」找一個情感的歸流,當時(二○○九年)就發願要寫一個劇場作品,以為呼應。不料,龍女士入閣,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文化部長。當年,龍女士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時,我也多次應邀,服務公部門的專業諮詢,龍局長看我坐在會議室角落,特別呼喚:「阿綱,過來坐我旁邊。」我扭捏一陣,她又說:「幹嘛?不喜歡當官的呀?」
是的,我被她一眼看穿,「不喜歡當官的」。因此,我不願意在她擔任部長的時期,披露已完成部分篇幅的作品。終於,她辭官卸任,回歸為村子裡的龍姊姊,我的戲可以上演了。
一齣相聲劇,素材來自《古文觀止》、《搜神記》、《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時空,在溯古泛今的大江南北穿梭。不迎合大眾,不符合「時尚正確度」。我猜,初步只能引發國文老師、歷史、地理、博物愛好者的共鳴。
三個人物,並不具有特定性格特質,叫某甲、張三亦可,但我愛講究,於是在三部啟蒙書中各取一典,做為角色名,也都和「吃」有關:
《百家姓》──慕連茹習,宦艾「魚容」。首演由我出任。
《千字文》──果珍李柰,菜重「芥薑」。宋少卿首演。
《三字經》──稻粱菽,麥黍稷,此「六穀」,人所食。黃士偉首演。
兩首插曲《打鞦韆》和《四時漁家樂》,都是小時候在音樂課上學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四時漁家樂》,作詞者韋瀚章、作曲者黃自,他們合作的另外一首名曲,就是《國旗歌》。兩首插曲都請張靖英重新編曲,我寫的新詞〈說書〉,也請靖英作曲,成為本劇的主題曲。
包袱的「皮」厚嗎?就看對誰而言了。我倒認為,志於文化深耕的同好,終生學習者,對古文、對傳統小說內容、作者下過工夫的中學生,必然覺得這齣戲的哏,皮很薄。
另一方面,在創作劇本的同時,做了一些自主練習,針對簡體字進行諷刺,寫成一些零散的極短篇,部分篇章已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收錄在這本書裡,製造一些間隔的閱讀樂趣。其中有兩篇,林一先畫成了雋永的連環漫畫,請來書中,增添光彩。
所以,這部著作不宜以簡體字印刷發行,會怪怪的。
推薦序
《賣橘子的》──笑聲裊裊,心波粼粼
從一個學西方戲劇的人眼中,來看阿綱的相聲新作,實在是個奇異的旅程。
我對相聲的記憶,仍停留在魏龍豪、吳兆南的時代,在他們定義的相聲中,《賣橘子的》恐怕有些面目模糊了:它沒有連續不斷的包袱,去讓人笑到喘不過氣。但期待上的落差沒有困窘太久,我的文學神經就在閱讀中開始隱隱騷動:魚容才說了自己的童年,就轉上他父親當流亡學生的經歷;沒停太久,故事就到了紫湖的由來;戰亂的歷史還沒來得及沉重,龍王的童話就把想像帶去真假難分的久遠……敘事自由,幾乎隨心所欲;沒有一件事逼著我們認真,卻又感到沒有一件事允許輕忽。這是遊戲的口吻,卻有史詩的開闊。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形容西方小說的歷史有上下半場:上半場,自由,不對單一主題認真;下半場,結構嚴謹地為主題服務。這個看法應用在近代西方戲劇的演變亦然:上半場,演員與詩人共舞(代名詞是莎士比亞);下半場,結構,甚至是公式,為目的與主題服務(新古典主義以後所有亞里斯多德戲劇典範的變形)。在下半場的喜劇,包袱或笑點是結構服務的目的,是被精確設計的效果,傻子、愚行、誤會、巧合、冤枉、雙關語、雜耍特技……全是設計的手段,目的在搏君一笑,偶爾,也順便偷渡一點道德或批判的訊息。在這種戲劇中,編劇是騙子,看戲的成了被操縱的傻子。
上半場的戲劇中,敘事本身成了魔幻的旅程,敘事的鬆散,其實是引君入座的頭等艙,觀眾更為自由,他的想像力更被尊重,成了上路的引擎。《仲夏夜之夢》忽而宮廷,忽而森林,情侶不識工匠,仙界又擾亂人間……而我們卻連誰是主角都說不準。還不快活?「請讓你的想像力運作(On your imaginary forces work)」,《亨利五世》一開場,莎士比亞如是說。
《賣橘子的》不單是把我帶離了傳統相聲,而是把我這個浸淫在現代戲劇(發軔於對新古典主義的反叛)與莎士比亞的人,帶回了熟悉又愉悅的世界。這愉悅,不來自單單坐在那兒等著被逗樂,而是在記憶中不斷複習不停送上的場景、畫面、時代,甚至知識:《西遊》、《水滸》、《三國》,我的童年文學;長江與亞馬遜河的長度,我的中學地理;脊索動物門,哺乳綱,鯨目,我被當掉的生物。《賣橘子的》讓知識成了甜蜜的負荷。
只有在那些謹慎又零星的批判裡,我感到自己又回到文學與戲劇的下半場:阿綱想為相聲做很多,或許多了點兒,這些段子負載了太多期待,太多心情,但顯得黑白分明,我自在的樂趣一下不敢放肆,成了立正聽訓的孩子。
但他的訓話很短,很快地,我又追著《賣橘子的》上路旅行。《賣橘子的》的笑聲不張揚,卻很瀟灑,像是山谷人家的一縷炊煙,裊裊飄去,但揭露的一方天地更是廣闊,視野更是自由,在它豐富的敘事中,我被撩撥不已,心波粼粼。
(本文作者何一梵,英國威爾斯大學戲劇博士,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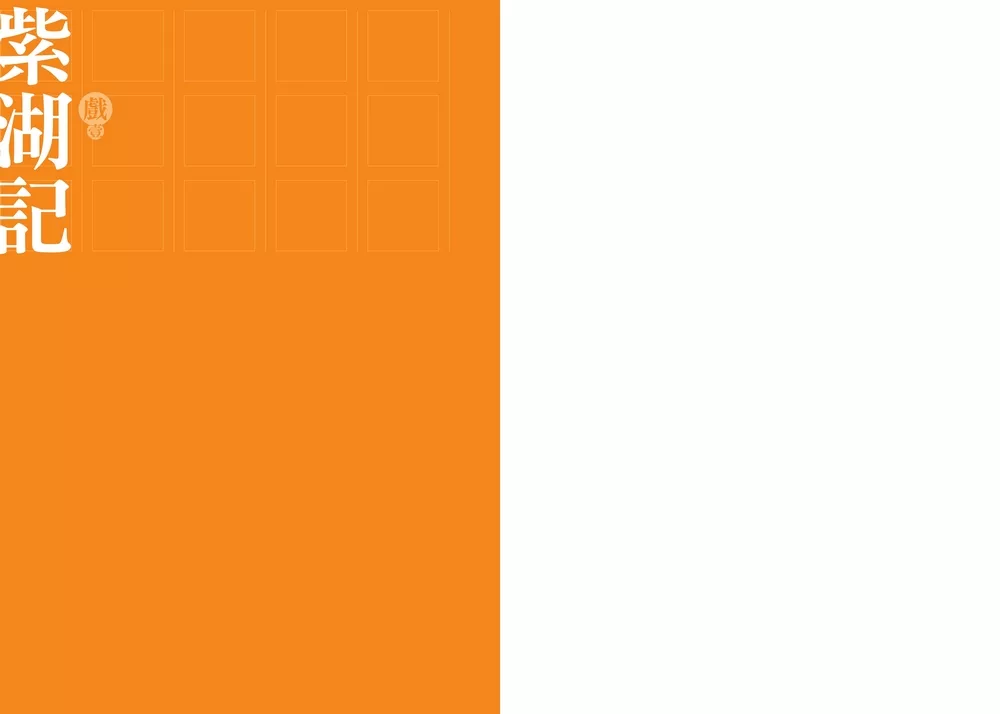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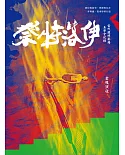
![韓國華 : 林吳素霞南管戲傳本[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6%2F28%2F0010862886.jpg&width=125&height=155)




![講戲與做戲 廖瓊枝經典折子戲 劇本與表演詮釋[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90%2F85%2F0010908512.jpg&width=125&height=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