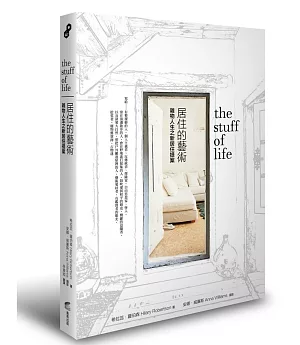自序
我很早就開始對室內空間的布置擺設產生興趣了。四歲時,我就讀於一所鄉村學校,我們學校的戶外遊樂場包括了一大片老樹林旁的粗草地。有一些女老師會在附近走動巡邏,在她們的監督下,我們是可以在草地上自由活動的。我們最常玩的想像遊戲就是扮家家酒。找幾個朋友組成一個「家庭」之後,我會開始打造我們的營地;用細樹枝做成的圍牆隔出幾個房間,搭建我們露天的家。我們有葉子鋪成的床,橡樹果實是廚房裡的茶杯,用葉子做窗簾,雛菊花環做裝飾,還有樹皮當地毯。當我拿起冬青樹枝做成的掃把打掃「家」裡地板、或者幫我想像中的孩子擺放他們青苔床上的樹葉枕頭時,時間彷彿停止流動了。
童年時期的扮家家酒經驗並沒有讓我在成年後特別熱衷於家務,但我對於打造別具美感的居家環境卻萌生無比的熱情,先是我少女時期的房間、接著是我狹小的大學宿舍裡那面空心磚牆;我還從一把里特費爾德(Rietveld) 樣式的椅子(那是我的教父親手為我製作的十八歲禮物)得到靈感,以荷蘭風格派(De Stijl)
的三原色為一張空白帆布上色。或許對我來說,在這個混亂又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能夠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私密的愛達荷(private Idaho)」 並且擁有主導權──不論這個空間多麼簡陋、多麼狹小,手頭上的預算多麼拮据──就是一種療癒。只要我可以拿些枝葉做出自己喜愛的擺設、從《Casa
Vogue,》雜誌裡撕些漂亮圖片下來、在牆上貼滿從博物館買回來的明信片、或者學學安迪‧高茲沃斯(Andy Goldsworthy)怎麼堆疊鵝卵石,我就會覺得自己像是在家裡那樣自在。我也收集了許多自己喜愛的視覺參考資料,這個資料庫總是可以帶給我滋養與靈感。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對於「風格設計師」在做什麼可說是一無所知,但當我了解「風格設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之後,我知道我非要努力成為其中的一員不可。搜尋、收集、布置、再重新布置;我生來就是要做風格設計的。長大之後,我開始有機會打造一些室內空間,其中有許多(即便不是大多數)個案的預算非常有限。我是「限制」的愛好者;「無限」的可能性會是相當恐怖的一件事,而且室內設計預算無上限並不保證結果必然是美好的。
我的兒子才十天大的時候,我們搬進一間我們花了好幾個月打掉重練的房子。對於帶著小寶寶的新手父母來說這間房子並不是很實用:它是一間漂亮、但面寬狹窄的維多利亞式三層樓房,比較適合有青少年的家庭,方便孩子們把自己關在頂樓、或是藏身在外頭露台花園的小亭子裡。初為人母的我,完全是憑寶寶還沒出生前的時尚家居概念而做了室內裝修的決策:上了白漆的光亮地板(要花很多力氣維護,而且又滑又硬)、白色布沙發(不切實際)、絲綢窗簾(黏答答小手的最愛)。我一直想要擁有一間鋪滿地毯的小房子,但就在我們終於搞定最後的一些細節時,我先生在紐約找到了新工作。我們就這樣離開了。
我愛旅行,也喜愛到達一處新天地的感覺,於是我選擇效法先人們搭乘瑪麗皇后號(Queen Mary) 的精神,帶著三歲的孩子前往紐約。我帶了六大箱的行李,大多數的珍藏(與我們大部分的傢俱)不是被留在倉庫裡,就是送給朋友了。如果說我對於放下那些從倫敦黑斯廷(Hastings)或其它任何二手商店、市集、後車廂舊貨市集(car boot
sales)、古董店經年累月收集來的珍藏完全不以為意,那是騙人的。我試著說服我自己,生活裡少了這些東西也挺不錯的;至少算得上乾淨俐落。或許我還能把自己改造成一個極簡主義者?這下全世界都笑話我了──「你?門兒都沒有!」
我在紐約市重新出發,思索著開始一個不一樣的人生。也許我不再想當一個室內風格設計師了?我決定,把自己當成「異鄉英國女性」(Englishwoman Abroad)的化身
,我應該來試試新的角色。我們跟一個打算在上紐約州展開鄉村生活的家庭分租了一間很實用的公寓。要嘗試別人的生活方式,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有解放的感覺,然而這種感覺不久就會被「茫然」所取代。我們原本打算在那間公寓住上一年,但這家人的「鄉村生活」實驗顯然並不是太成功,於是很快地,我們得再搬到另外一間公寓,第二間公寓卻讓我們覺得怎麼住都不自在。好不容易,等到第二間公寓的屋主總算把他所有的傢俱運往他舊金山的新家,我們立刻動身前往麻薩諸塞州的布利姆菲爾德跳蚤市場(Brimfield
Flea Market),這是一趟重拾我與「物件」之間關係的旅程。我又入手新的老古董了。萬歲!
這是必然的結果。對我來說,打造一個居家環境實際上就是在擺設我經年累月收集來的這些物件;每個物件都有它的故事,足以喚醒你對某些地方、某些人、以及探索興味的記憶。這也是向世界展現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的方式:這是展示自我的博物館;是一窺你個人特質的線索。我想,所有的物件──即便它再怎麼不起眼──只要慎重其事加以安排布置,都能綻放它的美麗。而「美」(不論「美」對你而言的定義如何),正是靈魂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