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黃昏武士的寓言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
「爾所見者為利害關係之世,予所立足者乃道理是非之世;爾所見者為現象界,予所見者乃實相界。」──夏目漱石、『断片』(明治三十八年)
《少爺》可謂一篇源於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所謂「生命衝動」(elan
vital)的創作。夏目漱石以他自幼熟悉的江戶方言與落語口吻,在一個禮拜到十天之間一氣呵成,寫完一百四十九張稿紙,其間極少修改,彷彿生命力以沛然莫之能禦之勢從筆下流洩而出,自然地渲染出一幅莽撞、率真、富正義感而元氣淋漓的江戶兒(江戸っ子)畫像,在充斥著日本近代文學的「苦惱的近代知識人」典範──包括漱石自己日後創造的三四郎和「高等遊民」長井代助──之外,另外塑造了一個完全對立而獨立的原型。有趣的是,這樣一個完全非典型的人物卻捕捉了明治維新以來在嚴厲的國家規訓和急速現代化下變得過度壓抑、畏縮的日本人的心,讓這個莽撞的,帶有古風的江戶兒至今仍是憂鬱的日本民族最喜愛的文學人物之一。
故事很簡單。一個在東京出生長大,生性莽撞率直而富於正義感的青年(「少爺」)因莽撞的決定而到四國的松山就職,擔任舊制五年中學的數學教員,可是一到了那裡,他莽撞率直的個性就和學校當權派(校長「狸貓」和教導「紅襯衫」)的偽善陰險直接衝突,讓他吃了不少苦頭。最終,充滿正義感的主人翁為了替被紅襯衫陷害調職的英語教師古賀打抱不平,和學校裡另一位正直的外來者,也就是東北出身的數學科主任堀田(「豪豬」)一起修理了紅襯衫和他的跟班兼共犯的美術老師(「馬屁精」)一頓,不過兩人也因此而被迫離職。「少爺」於是回到東京轉任輕軌電車的技師,和忠心的年邁女僕阿清一起過日子。
這其實是一個簡單「賞善罰惡」的故事,在江戶落語中常見,但它確實是一個好看的故事。事實上,如果讀日文原文,熟悉江戶腔,甚至懂得一點落語的話,你還會覺得這個故事好聽極了。一邊讀一邊想像「少爺」用那有趣的江戶腔連珠砲般地咒罵那些偽善的鄉巴佬,你真的會感覺彷彿在淺草聽寄席落語般的過癮-而且好笑。或許,一般讀者──特別是在現實世界中受盡壓抑之苦的日本上班族──讀到這個層次就夠了。「少爺」這樣的人物在現代日本社會的現實當中幾乎不可能存在,然而透過閱讀他在書中對體制誠實,甚至口沒遮攔地咒罵,小市民的委屈獲得了抒解,也為明日的奮鬥與忍耐帶來了一點力氣。這種情緒淨化(catharsis)的功能,有點像居酒屋帶給日本一般市民的慰藉作用:讓壓抑的情緒暫時解放,讓隔離人與人的高牆瓦解,讓情感短暫自由交流,於是在帶著微醺傾心交談的瞬間,小市民從國家與資本的規訓逃離,獲得了短暫的自由。
然而文本閱讀有無盡的可能性。做為日本的「國民作家」,寫遍了日本人面對現代文明的惶惑不安,因而受到日本國民長久愛戴,至今盛名不衰的漱石的這部非典型作品,更是不會逃過文學評論家多疑之眼的嚴密檢視。拜這些深度閱讀者的努力之賜,我們於是知道了更多理解《少爺》的方式。
比方說,我們可以從作家漱石個人生命哲學的角度為這本書定位。這又有幾種不同的看法。立教大學教授石崎等主張,漱石小說中一直存在兩種生命理想──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與隱遁的「逸民」,而他的生命發展軌跡則是由前者向後者過渡的過程,例如初期作品《少爺》與同期作品《野分》《二百十日》屬於「士大夫」精神的「社會正義」系列,但從《三四郎》、《それから》以後內省性格愈來愈強烈,逐漸過渡到「逸民」精神。評論家宮井一郎則主張漱石的內在世界存在一個追求人格與自由的「人格社會」與追求現實利益的「利益社會」的對立,終生不易。這個對立最早出現於《我是貓》裡面的苦沙彌與金田家的衝突,然後到了《少爺》,漱石對自由的強烈渴望,以及對利益社會的強烈厭惡,於是以一種被現實社會尺度視為「瘋狂」的方式表現在主人翁對教育體制的衝撞之上。
又比方說,我們也可以對本書進行一種文化的,乃至文明論的解讀。這就是著名的保守主義評論家江藤淳的立場。江藤銳利地指出《少爺》裡面這個「江戶兒」的個性反映了漱石本人在成長期受到的江戶武士與町人(商人)階層文化與感性的薰陶,而他刻意採取落語故事的方式描繪一個性格平面的主人翁,而不用現代小說的寫實手法捕捉人性的多層次與矛盾,目的就在彰顯「少爺」這類人物是非寫實的,是在現實中不存在的一種理想型。不只如此,「少爺」這個融合了武士與江戶町人氣質的主人翁之所以不存在於現實,還有另一層歷史的,以及文明的意義:武士與町人氣質代表一種已經消逝的文化,一如藤澤周平的《黃昏清兵衛》,因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就一頭栽進了無法回頭的西化與現代化浪潮,而代表所謂「現代性」的功利主義價值觀也完全取代了江戶時代的武士與町人文化。也因此,代表武士精神的「少爺」和「豪豬」雖然痛快地修理了代表現代文明的惡人「紅襯衫」,還是被迫離職,因此終究還是「敗者」。最終,現代文明戰勝了江戶文化。這個解讀,清楚地反映了江藤淳個人的文化保守主義。
甚至我們還可以做大歷史的,以及政治的解讀。東京外語大學教授柴田勝二的《漱石の中の〈帝国〉》(二OO六)另出機杼,把漱石「國民作家」的稱號,從「屬於全體國民的作家」這個原始意義擴大為「國民主義/民族主義的作家」。在他的解讀之中,《少爺》描寫的不再是一個逝去的江戶武士與町人文化,以及對現代文明的抵抗,而是致力於現代化的明治日本與西洋帝國主義的對抗。主人翁「少爺」的武士氣質,不再是江戶或明治維新敗者諸藩的武士氣質,而是維新中的勝者,也就是薩摩與長州武士的氣質,而最具象徵的代表人物則是西鄉隆盛。於是,「少爺」與「紅襯衫」(喜歡讀俄國作家高爾基)的對抗,變成了薩、長武士所創造的明治日本與俄羅斯對抗──也就是日俄戰爭的隱喻。最終,「少爺」雖懲罰了「紅襯衫」,卻被迫離開松山中學校,則是日俄戰爭後三國干涉還遼的暗喻,也是明治末期日本民間對戰爭「雖勝猶敗」而爆發之民族主義情緒的根源,以及漱石寫作本書的背景。柴田的驚人解讀,明顯地反映了當代後殖民研究的影響。
然而不管怎麼讀,或許我們最終還是必須回返人的處境(human
condition)。所謂「經典」的意義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種超越歷史與文化脈絡的,從普遍人性角度加以閱讀的可能性。「少爺」是武士與町人後裔,說的一口江戶腔,他或許是漱石的化身,或許是一種抵抗西洋文明的本土文化認同的象徵,也或許可以是明治日本與列強周旋的隱喻,但他的莽撞卻率真的個性,他快意恩仇,仗義助人的遊俠行徑,以及他和體制與主流價值直接對抗的笨拙與勇氣,卻體現了一種跨越文化、國界,乃至時代的,關於人的自由與正義的共同理想。人活在社會之中,受社會的制約與規訓,雖生而自由卻不得自由,並且不得不在種種規範之下存活,於是法國哲學家盧梭會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社會規範總是體現主流價值觀與其偏見,法律只能實現局部正義,受污辱與損害的弱者如何解放,如何獲得正義?不完美的人只能創造出不完美的社會,不完美的法律,不完美的政治,於是受苦的人們只能在夢中,在故事與傳說,在戲曲之中,想像、傳頌某種任性的,自由的,勇敢的,溫暖的,親切的,可以為我們實現正義的形象與身影,像我們的「少爺」。武士做為一種階級早已消失,然而武士做為一種尊貴的公共獻身精神(noblesse
oblige)依然可能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很放心地,用一種跨文化、跨歷史,乃至無歷史的的方式-用一種讀寓言的方式,來讀《少爺》吧。
(2015.5.13南港四分溪畔)
參考資料:
1.《日本現代文學大系 17: 夏目漱石集(一)》(東京: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三年)
2. 江藤淳 《夏目漱石》(東京:角川書店,昭和四十三年)
3. 柴田勝二,《漱石の中の〈帝国〉:「国民作家」と近代日本》(東京:翰林書房,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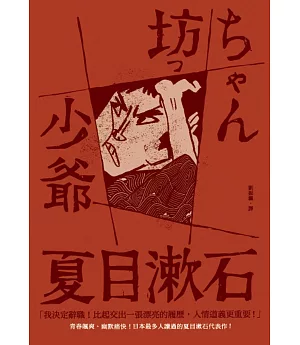















![向田理髮店[二版]](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91%2F72%2F0010917251.jpg&width=125&height=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