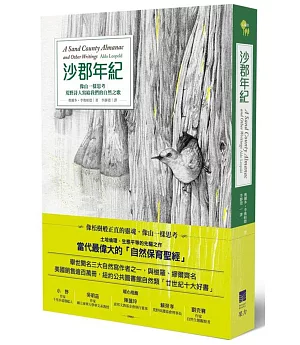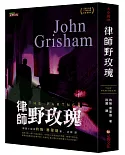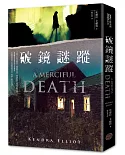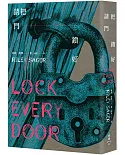【導讀序】
野性蘊藏著世界的救贖
文|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一九九八年左右,我進入了生命裡第一個生態團體──「生態關懷者協會」。這個協會與其它強調自然知識,或環境抗爭的團體不同,我加入它的第一個參與活動,就是《沙郡年紀》的讀書會。當時我並不知道李奧帕德在生態論述上的地位,但第一次翻閱此書的我,被李奧帕德冷調的描寫能力,出人意表的隱喻句,以及說理時像用圓規畫同心圓似的層層遞衍的論述手法深深吸引。
在我至今的寫作生涯裡,如果要毫不矯情地說最常回頭翻閱的書,那麼包藏了一個自足宇宙的《波赫士全集》與相較之下在「厚度」上不成比例的《沙郡年紀》,該是最多的兩部作品。當我陷入思考自然的兩難議題,以至於思緒停頓之時,往往幾行的閱讀就能讓我重拾熱情。
**********
《沙郡年紀》的成書過程十分漫長,一開始是一九四一年亞飛諾普(Alfred A. Knopf)出版社編輯哈洛德‧史特勞斯(Harold Strauss)的邀稿。在歷經數年的寫作調整後,數家出版社卻始終拒絕出版這本書,他們希望李奧帕德能修正被收羅到這本文集裡的作品和觀點(當時書名一度稱為《沼澤輓歌》Marshland Elegy—And Other
Essays,以及《像山一樣思考及其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And Other
Essays)。有的編輯建議觀點應予統一,有的建議應將偶爾出現的學者口吻或道德性教誨加以調整。李奧波數次調整,至少在一九四八年前往搶救鄰居一場火災,而在途中心臟病猝逝前,他不斷嘗試將長久以來的觀察、疑惑與思考,用一種可親、乾淨,又具有想像力的語言表達出來。而就在死亡突然降臨的前幾天,他才剛得知《沙》終於被編輯接受,準備出版。
現在多數版本的《沙郡年紀》,都和李奧帕德另一部作品《環河》(Round
Rivers)併在一起,這便是編輯產生的化學效應。經過編輯以後的《沙》由自然觀察漸次進入科學闡述,最後提升到哲學層次,它不再只是一本談論「無法失去野地生活的人的愉悅與兩難困境的書」,也不只是「自然所教導的快樂與悲傷的片段」,它被喻為是「保育界的聖經」、「自然寫作的經典」、「世紀之書」,而耶魯大學英文系教授塔馬其(John
Tallmadge)指該書,「以極優美的散文呈現,文字簡潔,含義卻極為深刻,就像所有最好的詩歌一樣,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又正如一件精雕細琢的藝術品,在外表上卻看不到一點刻痕。」更是對此書在文學上的成就,下了恰如其分的註腳。
**********
李奧帕德早年曾任職林務官,一九三三年他所寫的《可供狩獵的野生動物經營管理》(Game
Management),在當時被視為從事野生動物經營管理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將自然生物(如狩獵與林業)與生態環境(如礦業)視為資源,到現在都還是自然資源保育論者的重要觀點,他們推動的保育價值奠基在自然是人類豐富的資源,應該「明智地」加以利用。這也是李李奧帕德早年秉持的看法。但隨著他在生態學的研究與野地觀察的經驗累積,李奧帕德提出了幾點革命性的看法。
其一是「社群」的概念(The Community Concept)。李奧帕德認為必須將人視為土地國的一份子,透過整全的研究,試著去「保存生物社群的完整、穩定和美」,才是人類與自然的相處之道。李奧帕德定義下的「土地」包括了土壤、水、植物和動物,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流動性關係,直言之,就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這生態系每一種生物與生境都屬於社群關係,共同組成「土地金字塔」(The Land
Pyramid)。
其次,李奧帕德指出完全以經濟目的作為自然資源保護的觀點,有一個基本弱點,那就是許多生物(比方說野花和燕雀群)在人類的眼光裡頭看起來並沒有經濟價值,如此一來,他們會被輕易地犧牲。李奧帕德認為,人類有責任讓土地適應文明所改變的新環境,必須思考如何以較和緩的手段來完成期望中的改變。這種態度,應該根源於生態良知(Ecological Conscience)與土地美學(Land
Aesthetics)。
**********
土地美學是李奧帕德論述裡另一個別具特色的觀點,它最大的特質即是在面對非「人工製品的美學」(Artifact
Aesthetics)時,人類扮演的是感知者與鑑賞者的角色,人類的靈魂在這裡完整地成長。荒野(Wildness)的存在提供了我們到野地去創造感知的根源,換言之,保存荒野便是保存了「被感知對象」的存在。李奧帕德在書中描寫「狼眼中的綠火」,訴說「閃電打入懸崖」,「冒煙的石頭碎片呼嘯著掠過耳邊」,「閃電擊裂一棵松樹後……一片閃閃發光的白色木片,長度約有十五呎,它深深地戳入我腳旁的泥土裡,然後立在那兒哼叫著,就像一把音叉」,這類令人為之震懾的「野性之美」;也描寫了葶藶這般路旁植物的「微物之美」。野地的多樣性與人類感知的多樣性恰成正比,而且它與人工美學有極大的不同:自然界有時帶給人辛苦、痛苦與傷害(比方登山、溯溪,或被野獸及蚊蟲侵擾),卻也會構成獨特的個人與群體經驗。從這觀點來看,每一種生物與地景的消逝,都是美學上的損失。李奧帕德說接觸自然不是「按住板機向上帝索取肉」,也不是「在樺樹皮上寫下拙劣詩句」,更不是開著車「累積哩程數」。他認為,這種方式都是將休閒建立在「戰利品」的觀念上。而具有美學內涵的接觸,有賴於「感知能力」,因為人類置身於自己所欣賞的對象之中。感知能力的特徵是:不會消耗任何資源,也不會稀釋任何資源的價值,具有豐富感知經驗的人,相對較會去深沉思考人和自然的倫理關係。
因此,李奧帕德認為健康的生態系本身就具有美學價值,「自然美學的聲音就是保護政策或土地管理的重要聲音」。
**********
幾年後,我協助「生態關懷者協會」的陳慈美老師接待研究李奧帕德的專家──北德州大學的柯倍德教授(J. Baird Callicott),他又為我理解的李奧帕德,帶進了更深一層的體悟。隨著時代的變遷,土地倫理已不再是「聖經」,它面對新的解構生態學(The New Deconstructive
ecology)、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的挑戰,前者從更多的生物研究資料,提出一個無組織、多元而彼此不協調的組織典範(a plurality of mutually inconsistent organizing paradigm),來詮釋多變、難以預測的生態系。後者則以基因學、演化學的概念,質疑了以倫理為核心思維的李奧帕德式生態學。
更有一些學者,批判李奧帕德是「生態法西斯主義」(Ecofascism),比方說哲學家艾肯(William Aiken)和法萊(Frederick Fene)就曾經指出,如果從土地倫理的立場出發,作為人類文化的準則時,必把個人淹沒在集體、種族、部落或國家的榮耀之下。
李奧帕德的後繼者對這些批判與新挑戰,並未一味捍衛,柯倍德就認為他的觀念若要在今日仍具有生態學上的可信度,就必需被修正,或是強化。我想這是今日重讀《沙郡年紀》的深刻意義之一:一本書的內容與讀者,應該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成長,書中不夠清晰、過往熠熠生輝的概念得以被重新思考、反省,這樣的書才堪稱經典,這樣的讀者才是經典的讀者。
**********
當然,重讀這本書,依然讓我著迷的仍在於李奧帕德當時如何建構超越時代的思維,更特別的是,這樣的思維是透過如斯的詩意語言表現出來。
當他提到每種生物都有內在價值或原生價值(intrinsic value or inherent
value)時,他不用艱澀的哲學詞句,而是說「自從冰河時期起,每年春天,沼澤便在鶴的喧嚷聲中醒來。構成沼澤的泥炭層,位於一個古老湖泊的凹處;鶴群彷彿正站在屬於牠們自己的歷史中,那浸濕了的幾頁之上。」當他想說人類得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利,因為物物相關時,他會說:「我以為狼的減少意味著鹿會增多,因此狼的消失便意味著獵人的天堂,但是,在看了那綠色的火燄熄滅後,我明白狼和山都不會同意這個想法。」
而當他想講述生物身上具有不可取代的美學價值時,他會說:「物質的『魂魄』(Numenon),它和『現象』(Phenomenon)正好成一對比──後者是可計算、可預測的,即使那是最遠一顆星的搖動和轉動。北方森林的魂魄是松雞,山核桃樹叢的魂魄是冠藍鴉,沼澤地的魂魄是灰噪鴉,而長滿刺柏的山麓丘陵的魂魄則是藍頭松鴉。鳥類學書籍並沒有記錄這些事實。」
這也是我向所有讀者,而不只是對關心生態,對自然科學、環境倫理有興趣的讀者推薦這本書的重要理由。
**********
第一個提出白蟻群體是一個有機體的科學家馬萊(Eugène N.
Marais)曾這樣描述大自然的「無道德性」──「自然界從來沒有流下憐憫的淚水,就算最美麗、最善良的生物受到傷害,自然界也不會出手保護。」但他也認為,身為靈長類的我們最特別的就是,擁有觀察事物因果關係後,產生新記憶與行為模式的能力,在所有的動物裡頭,人類在這點走得最遠。即使自然界並無道德性,但人類文化裡的倫理、美學思維,仍然在人類演化史上,重新界定了人類的魂魄。李奧帕德曾將梭羅的名句「野性蘊藏著世界的保存」(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更動了一個字,成為「野性蘊藏著世界的救贖」(In wildness is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或許,這是人類做為一種生物,又想超越生物本質的嚴苛考驗。
柯倍德曾在整理美國歷史上跟保育有關的決定後,發現許多案例「受到美的激勵多過責任上的期許。」(more…motivated by beauty than by duty)他當然認為這還不夠,因為在李奧帕德的哲學裡,土地美學、倫理責任,以及科學研究,也是一種社群關係。
純粹以自然科學的角度來思考做為一種生物的人類,我們生活在馬萊所說的冷酷無情、從未流下憐憫淚水的自然界。但人類多麼想從這樣的自然界裡重新定義自我的形象(就像我們多麼看重自己在所愛的人眼中的形象),這從來就是一種倫理上、美學上的救贖。
【初版作者序】
有些人離開了野生生物也可以生活,有些人卻做不到。這裡的隨筆就表達了後者所感受到的欣悅與所面臨的窘境。
在文明進程開始擯棄自然環境以前,野生生物在人們眼中,就像晨風和落日一樣理所當然。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是否值得犧牲自然的、野生的、自由的萬物?只有和我一樣的少數人會認為,看到大雁給我們帶來的快樂要比看電視所得到的快樂更生動自然,尋找一朵白頭翁花的美妙情趣與言論自由一樣,都是不可剝奪的權利。
我承認,在機械化生產為我們帶來豐盛的早餐之前,在科學為我們揭示野生動植物從何而來、如何生存之前,自然環境裡的這些東西幾乎沒有多少人文價值。因此,全部矛盾就歸結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這些少數派看到了進化過程中的遞減定律,反對我們的人卻沒有看到。
人們必須根據事物的狀況調整對策。這些篇章就體現出了我的對策。它們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敘述的是,我和家人在遠離現代生活的簡陋木屋中過周末時,觀察到了什麼景象,產生了什麼感受。威斯康辛州的這個沙地農場,先是被日趨龐大與進步的社會耗盡資源,之後又遭到了拋棄。我們則試圖用鏟子和斧頭,在這座農場上重建我們在其他地方失去的東西。正是在這裡,我們進行尋找,並仍能找到上帝所賜予的美糧和無窮樂趣。
這些木屋隨筆按照月份先後排列為「沙郡年紀」。
第二部「隨筆」(編按:本書編排為第二部「地景之書」,另增錄第三部「鄉野沉思」),其中細述了我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它們讓我明白,我的同行者並非步調一致。這一逐步加深的認識過程有時是痛苦的。四十年來,我在美國大陸各個地方親身經歷的這些插曲,對於各種可被共同歸結為「自然資源保護」的議題,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證。
第三部「結語」(編按:本書編排為第四部),其中提出了一些邏輯性更強的觀點,科學合理地解釋了我們這些少數派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只有對我們非常有認同感的讀者,才會費神思索這裡提出的具有哲學意味的問題。可以說,這些隨筆告訴了我的同行者,應該怎樣做才能恢復我們應有的步調。
自然資源保護並未取得應有的進展,因為它與亞伯拉罕式(註)的土地觀念毫不相容。人們認為土地是屬於自己的商品,因此濫用土地。只有把土地視為我們所隸屬的群落,我們才有可能帶著愛與尊重來使用土地。只有通過這種途徑,土地才能在機械化時代的衝擊中倖存下來;也只有通過這種途徑,在以科學為主導的情況下,我們才仍有可能收獲土地奉獻給人類文化的美學價值。
土地是一個社群,這是生態學的基本觀念;而土地應該得到愛與尊重,這一觀念則是倫理學的延展。土地能為人們帶來文化上的收獲是早已被廣為接受的事實,但近來卻常常被人遺忘。
這裡的文章,試圖融合以上三種觀念。
當然,關於土地與人的看法,會受到個人經歷和偏見的混淆與扭曲。然而,不論如何,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日趨龐大與進步的社會,如今就像患上了疑難雜症,由於時刻擔心經濟狀況是否良好,竟至失去了維持自身健康運作的能力。整個世界都如此貪婪地要求得到更多的浴缸,結果卻失去了製造這些浴缸所需的穩定性,甚至失去了關掉水龍頭的必要能力。在這種時候,最自然、最有益的行動就是,適度地放下那些已過於泛濫的物質享受。
要達到這種觀念上的轉變,我們必須重新看待自然的、野生的、自由的萬物,並對那些非自然的、被馴化的、失去自由的事物重新加以評估。
——奧爾多•李奧帕德 一九四八年三月四日於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
【增訂本序】
一九四八年,奧爾多•李奧帕德去世時,《沙郡年紀》還只是草稿。這些手稿由李奧帕德之子盧納進行編輯,於一九四九年成書出版。之後,李奧帕德生前從未發表的另一批隨筆和日記也由盧納加以整理,並在一九五三年以《環河》(Round Rivers)為標題出版。
這裡的新版本包括《沙郡年紀》的全部內容以及《環河》中的隨筆。文章的排列順序在此有所變更,其中的兩篇隨筆被合併在一起,旨在避免重復,並更好地呈現李奧帕德的主要觀點。重新編排之後,本書初版序言中所介紹的各個部分發生了下述變化:第二部已被重新命名,第三部調整為第四部,新的第三部主要選自《環河》。我們還修改了文本中一些有可能誤導讀者的過時引證。
很多人都曾閱讀並引用過這些文章,然而,公眾在強烈追捧「自然之美」的價值時,卻遺忘了這些文章的主旨。比如在路邊種些花草進行美化,這絕非李奧帕德所理解並宣揚的人與土地之和諧。美國一方面在立法中聲稱要保護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卻計劃著在兩處極具自然價值的地方修築水壩。在科羅拉多大峽谷修水電站的提案早已呈交國會,這樣的工程最終會毀掉生機盎然的河流,大水將會淹沒這一獨特自然遺產的大部分地區。
若干年來,籌建中的項目還包括在阿拉斯加開發水電,所選位置將使太平洋沿岸的遷徙水禽因為蓄水而失去主要的繁殖地。許多個年代裡,野鴨、大雁和其他鳥類每年都要飛過華盛頓、奧勒岡和加利福尼亞,但是水壩的修建,會在瞬間消滅這些鳥類的絕大部分。當年李奧帕德寫下〈大雁的音樂〉時,這一切還都無法想像,而現在這種景況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我們身上。遺憾的是,提議、擁護並實行這一計劃的美國人,會以經濟利益之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儘管經濟學不應成為決定性的因素,何況人們本可以尋找並採用其他可行的發電方法。
李奧帕德的孫輩這一代人,有的是大學校園裡的叛逆青年,有的從事社會工作或參加遊行,有的正在異域的土地上戰鬥。當年,奧爾多‧李奧帕德對於「野生的、自由的萬物」作出了睿智的理解與雄辯,隨著他的孫輩這一代人,觀點變得更為成熟,而保護「野生的、自由的萬物」也到了關鍵時期。
在吸引這些年輕人關注的所有事務中,大自然所面臨的困境已然是最後的呼喚。人類對土地的冷漠態度,正在給野生的、自由的生靈帶來毀滅。要遏止對自然的破壞,最好的辦法或許就是,把弘揚土地倫理的緊迫任務托付給年輕一代。
——卡羅琳‧克拉格斯頓‧李奧帕德&盧納‧李奧帕德 一九六六年六月於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