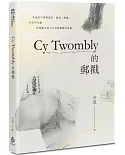我僅有一雙眼睛/陪島嶼色盲
加薩屠殺、復興空難、高雄氣爆、捷運殺人、警察闖進飯店監禁平民、洪仲丘命案迄今無解……這是個天災人禍不絕的時代。當多數天災也係人禍造成,而人禍的根由仍然十分可疑時,詩人不甘坐困愁城,只能期待翻牆,或以詩翻牆,越過這有形無形的權力囚牢,到達自由的海岸。愁城中的詩人,甚至哀悼也顯得無力,必須代之以嘲諷、甚至咒罵。詩人溫柔,而無法婉約,婉約簡直有對不起這個時代之嫌。
本期衛生紙,隱匿、沈眠、蔡仁偉不約而同對哀悼詩提出質疑。與其說是質疑詩人的真誠(誰有這把尺?)不如說是自問,詩人除了哭泣,能有何為?一些精彩示範:石芳瑜〈中國,麻煩你獨立一點好嗎?〉與阿鈍〈挖坑吧,以色列〉直接對現存兩大跋扈政權叫陣,陳子雅〈有人問我鬼島的緣故〉和盧郁佳〈餿水油〉則對島上自相摧殘與自相催眠的民眾毫不留情地嘲諷,讀來不可不能不痛醒。
在全球暖化被聯合國提到最緊急議程之際,人與自然的關係,也亟待重新反省。張耳〈「自然」詩現在應該怎麼樣寫?〉把這筆帳從陶淵明頭上算起,台東的詩人瞇則不僅從生物(小黑狗與小蟑螂)、更從無生物(雨和雪)為對象,辨識階級、種族差別心的緣起。詩人溫柔,這溫柔也可以是撼動心底的改革力量。
鴻鴻刊出新編的《女武神》劇本,重寫華格納經典成為反核以及反映青年革命的當代台灣史詩。甫出版的新詩集孫得欽即獲得兩篇觀點迥異的點評,可見獨特的聲音是不會被書海淹沒的。李雲顥透過阿米的兩本新作,探問「詩人罹患的是非寫作不可的病?抑或者,症狀是透過寫作才被開顯出意義來?」答案請自行尋索。不過我們深知,面對有病的時代,詩人非寫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