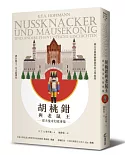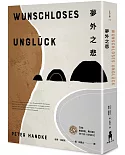向卡夫卡致敬(摘錄)
卡夫卡,《城堡》這本值得矚目的傑出小說及其同樣出色之姊妹作《審判》的作者,於一八八三年生於布拉格,出身自一個說德語的波希米亞猶太家庭,於一九二四年死於肺結核,享年僅四十一歲。他的最後一張肖像,攝於他死前不久,看起來更像個二十五歲的男子,而不像是四十一歲。照片上是一張害羞、敏感、深思的臉,黑色的鬈髮低低地長至額頭,一雙大大的黑眼睛,既帶著作夢般的眼神又炯炯懾人,直而下垂的鼻子,雙頰帶著疾病的陰影,嘴唇的線條異常細緻,一個嘴角漾著似有若無的笑意。這個表情既天真又睿智,讓人想起筆名為諾瓦利斯(Novalis)的哈爾登貝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德國浪漫主義時期詩人),天使般的神祕主義作家,尋找「藍花」的人。諾瓦利斯也是死於肺結核。
可是,雖然他的凝視讓我們把他想成來自東歐的諾瓦利斯,我卻不想稱卡夫卡為浪漫主義作家、神馳於神祕經驗的作家或神祕主義作家。就浪漫主義作家來說,他太過明確,太過寫實,太過依戀生活以及生活中固有的單純效用。他的幽默感──一種複雜的幽默感,為他所特有──對一個神馳於神祕經驗的作家來說太過明顯。至於神祕主義:他在和史泰納(Rudolf
Steiner,1861-1925,奧地利哲學家)的一番對話中的確曾說過,他自己的作品讓他了解了史泰納所描述的某種「先知狀態」。而他把自己的作品比喻成「一種新的祕密教義,一種猶太教的神祕哲學」。但他的作品沒有先驗哲學那種熱烈沉重的氣氛;感官沒有過渡至超感官,沒有「逸樂的地獄」,沒有「以墳墓為新婚之床」,也沒有真正的神祕主義者所慣用的其餘詞彙。這些他都不感興趣;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伊索德》、諾瓦利斯的《夜之頌》或是他對死去之未婚妻蘇菲的愛都不會吸引卡夫卡。他是個作夢的人,他的文章在構想和形式上往往如夢一般,就跟夢境一樣帶有壓迫感、不合邏輯、而且荒謬,是真實生活的奇怪影子。但他的作品充滿了經過縝密思考的道德觀,一種嘲諷、挖苦、經過絕望地縝密思考的道德觀,追求正義、善良、以及上帝的旨意,用盡全副力量在努力。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風格中:一種本著良心的、坦率得奇特、客觀、清晰、而且恰當的風格,其精確、幾近官方的保守主義讓人想起史提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奧地利作家)。是的,他是個作夢的人;但他在夢中所渴望的並非一朵綻放在神祕之境的「藍花」,他渴望的是「平凡的福分」。
這個詞出自本文作者年輕時的一篇故事《托尼歐.克羅格》(Tonio
Kröger)。從馬克斯.布羅德那兒,他是卡夫卡的朋友、同胞和最佳評論者,我得知卡夫卡很喜歡這篇故事。卡夫卡處於一個不同的世界,但身為東歐的猶太人,他對於歐洲市民階層的藝術和感受有非常精確的概念。或許可以說,促使一本像《城堡》這樣的書誕生的「遠大抱負」,在宗教的領域內相當於托尼歐.克羅格身為藝術家的孤立,他對人類單純感受的渴望,他對於市民階層所感到的良心不安,以及他所愛的金髮、善良與平凡。也許稱卡夫卡為虔誠的幽默作家,會是對他的最佳描述。
這個組合聽起來有冒犯之意,而組成這個詞的兩個部分都需要加以解釋。布羅德說,福婁拜晚年的一則軼事一直深深打動著卡夫卡。福婁拜這個知名的唯美主義者,他在強烈的禁慾中犧牲了所有的生活,獻給他虛無主義的偶像──文學,有一次跟他的外甥女柯曼維爾夫人去拜訪她熟識的一個家庭,一對強健快樂的夫婦,被一群可愛的小孩所圍繞。在回家的路上,《聖安東尼的誘惑》(Tentations de Saint
Antoine)的作者陷入沉思。和他外甥女沿著塞納河步行時,他一再重提他剛剛瞥見的那種自然、健康、愉快、正直的生活。他一再重複地說:「他們活在真實之中!」這位大師的信念是為了藝術而否定生活,從他嘴裡說出的這句話完全捨棄了他本身的立場──這句話是卡夫卡喜歡引用的。
托瑪斯.曼
導讀
召喚自我測量的文學城堡
卡夫卡的《城堡》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一則現代神話,描繪了二十世紀特有的典型經驗──官僚主義。很多人即使沒有讀過《城堡》,也知道這是在講K被召喚到城堡當土地測量員,卻無法進入城堡的故事。
但文學之所為文學,並不在於服務故事而已。《城堡》的內在結構,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得多、有趣的多了。我們先從一個問題出發,那就是K到底是誰?當我們這樣問的時候,有一個顯而易見又敷衍的答案──K就是卡夫卡。顯然這樣的答案可以並不能真正滿足讀者,反而更像是城堡會給K的回答。我們必須回到小說本身,看看這些文字本身,到底提供了什麼關於K的訊息。
當我們試著接近K的時候,一幅可怕的景象在我們面前展開,因為我們越想接近K,我們就離他越遠,各種嗡嗡聲開始出現,沒有一種詮釋是能讓人滿意的,只有混亂的訊息。此時,讀者就越像土地測量員本身,被召喚來測量小說的意義,卻發現沒有進入這個名為K的城堡道路。
卡夫卡幾乎沒有提供關於K的具體生平,只有兩次略為提到了他過去。一次是在第二章,講到K的家鄉「那兒的廣場上也有一座教堂,部分被老墓園所圍繞,而墓園又被一道高牆所圍繞……在一個曾經失敗的過好幾次的地方,他嘴裡啣著一面小旗子,一試就爬上了圍牆……當時那種勝利的感覺似乎將在漫長的一生中給他支撐…」這段敘述非常值得玩味,暗示了K與死亡的關係,彷彿他像個幽靈來到村莊,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死了。由於讀者無法確定K的真正存在樣貌,這種陰森虛無,反映在《城堡》中,是出現各種無法分辨的房屋(「那間旅店在外表上跟K所住的那一間十分相似」),人物(例如阿爾圖與耶瑞米亞這兩個助手),甚至是名字(索爾蒂尼與索爾提尼這兩位官員)。
另一次是在十三章,提到「K剛好有一些醫學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有治療病人的經驗,有些事醫生辦不到,他卻做到了。由於他的治療效果,大家一向稱呼他為『苦草藥』。」這裡則讓我們有一種感覺,K是有神秘力量的,好像這是他身為幽靈所附帶的能力。雖然K沒有在村莊裡發揮這種醫療力量,卻在與女性的交往上,展現了出奇的神祕力量,總能在一瞬間將對方誘入一種情色狀態。例如碰到芙麗妲時,K幾乎是毫無理由就在瞬間擄獲了她(「這正是我最秘密的意圖,您應該離開克拉姆,成為我的情人」),兩人隨即在吧檯底下進行魚水之歡。這種略帶笨拙反浪漫的情色,是除了設法進入城堡,小說的另一個重要主軸。
這兩次提及K的過往時,都是由作者(卡夫卡)所敘述,至於K本人在與其他角色對話時,從未提及自己的生平,令人感覺他與城堡一樣神秘。更有趣的一點,是除了作者與讀者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叫K,他也從沒有如此向他人介紹過自己。
只有四個角色在與K對話時,曾用K這個名字稱呼他(其他人物都叫K為『土地測量員』)。此現象頗不尋常,稱呼他為K的四個人──芙麗妲、歐爾佳、阿瑪麗亞與蓓比──-清一色都是女性,而且都是K所喜歡或有曖昧關係的女人。卡夫卡似乎在藉此表達,唯有愛能召喚出主體,把「土地測量員」變成「K」,愛所帶來的不是盲目,而是新的認識能力。
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德勒茲(G. Deleuze)與瓜塔利(F. Guattari)在1975年出版的《卡夫卡:邁向一種少數文學》(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是當代卡夫卡研究中最具突破性的經典。他們不從一般的詮釋角度出發,針對故事內容,直接解讀作品的意義。而是用各種比較、拆解的分析方式,讓我們看到卡夫卡作品實際上是一種生產意義的文學機器,並描述這些概念機器的運作機制。
以《城堡》來說,德勒茲與加塔利發現小說由兩種空間模式所構成,一種是仰角的,也就是向上延伸的,如高度、鐘樓或等級制度;另一種是水平延伸,如走廊、不斷移動的辦公室或分不清楚方向的道路等。我們可以發現,有一種特殊的運動透過這兩種模式展開。當K越想以第一種模式向城堡接近時,小說就安排他進行水平運動,從旅館、酒店、學校移動到歐爾佳家等。整部小說在現實空間中,是由K的水平運動所構成。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K雖然拼命想接近城堡,但在水平運動的過程中,K所碰到的角色等級,卻離城堡越來越遠,產生一種向下延伸的運動。例如K本來想見主任克拉姆,到後面就變成是他的僕役或秘書,甚至是秘書的助理;與他有曖昧關係的女性,也從原是克拉姆情人的芙麗妲,最後變成替代芙麗妲酒吧工作的蓓比――小說越後面,K周遭的人物與城堡的關係就越來越遠。
村上春樹於2006年獲得卡夫卡文學獎,他於布拉格頒獎典體上致辭時提到:「卡夫卡的作品是如此偉大,它具有某種普世價值。我會很直接將他理解為他是歐洲文化的核心。但在同一時間,我們也分享著他的作品。我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他的作品《城堡》,當時我不並覺得『這本書是歐洲文化的核心』,我只是覺得『這是我的書,這本書是寫給我的。』」
《城堡》的特殊之處,在目標於終極上的不可接近。K越是無法接近城堡,他越與更多人物產生關係,讀者對他與村莊的世界,就有更多的認識。《城堡》的內容不於在城堡本身,而是K的世界。城堡像是康德所謂的物自體,或是拉康的大他者,你不能接近它,但它卻成了可被認識世界的構成條件,即使它有可能是空的。K拼命想往城堡這個目標前進,不斷嘗試向上面連絡──小說的內容即是由這個過程中的挫折與奮鬥所組成。城堡本身並不重要,K在村莊的一切才是小說的重點。
如果你跟村上春樹一樣,當你在讀《城堡》時,能感覺到這是本寫給你的書,那就你就成了被召喚的K,準備進入這座文學城堡。如同前面我提到,閱讀這部小說,會產生一種特殊的運動,當你越想近它的時候,你就越往後退,退到你自己的生命裡。只有被召喚的人,才能成為K,而成為K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你必須愛卡夫卡。這種愛沒有理由,彷彿卡夫卡在命令讀者說:「這正是我最秘密的意圖,您應該離開現實,成為我的情人」。
《城堡》同時也是一部猶太密教的卡巴拉聖典,它可以產生各種解讀,開啟神秘的訊息與認識能力。正因為這份神秘,一個個文學愛好者,像村上春樹一樣,被召喚到小說面前,開始他們無限期的自我測量過程。
耿一偉(目前為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曾選編與譯註卡夫卡的《給菲莉絲的情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