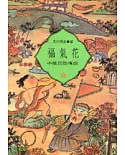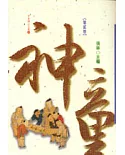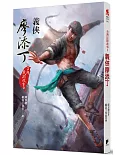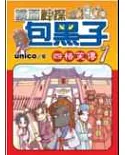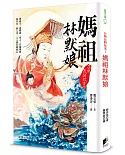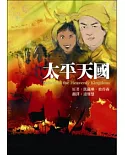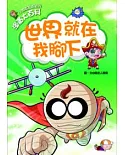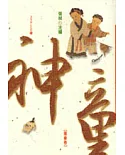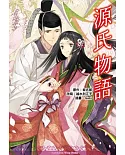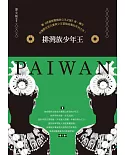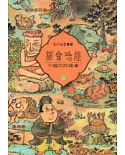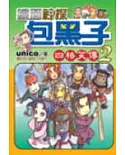推薦序
打開臺灣史的錦囊
一只四百年前留下的錦囊,牽動著幾代人的命運,同時亦帶出臺南府城歷史風華。國姓爺的錦囊封藏著祕密,錦囊一開,猶如拉開臺灣歷史的序幕,邀你一同盡覽時光長河中的榮盛興衰。
作者巧妙地利用傳說中鄭成功獲賜的一只錦囊,串聯出臺灣遠古左鎮人生活、荷據、清領、日治、戰後等時期文化風貌,透過本書的描述,臺南十七世紀大航海時期的繁榮風光躍然紙上。在風中,彷彿聽見臺江內海港口大船停泊時,人們的吆喝聲;在字裡行間,則看見七頭鯨魚守護的海上,漢人、平埔族人、荷蘭人彼此交換貨品的身影。
本書內容以林姓望族作為故事線,臺南歷史、地理及文化場景為小說時空舞臺,史實與虛構的情節交錯,描述不同時代的臺南文化風貌,同時兼具小說的趣味性與歷史的真實性。在書寫手法上,則以電影分鏡手法描述不同故事,故事看似獨立,卻在結局完整連結,每則故事都是一顆珍珠,藉由國姓爺的錦囊彼此串聯,讀者閱讀完本書之後,可初步了解臺灣歷史輪廓。此為本書可貴之處──讓年輕一代更願意閱讀歷史故事,進而探尋臺灣多元文化並呈下的種種樣貌。
臺灣人口組成來自四面八方外來移民,歷經中、日、荷蘭等不同政權,呈現豐富獨特的文化特色,本書從不同角度呈現臺灣殖民文化下的豐富樣貌,而又在結局回溯至史前時代,隱含臺灣主體性議題,讓讀者們在結束閱讀、闔上書本之際,開始思考臺灣人的身分認同,餘韻無窮且低迴不已。臺灣主體認同需要更多人對於臺灣史的關心,然而歷史資料過於艱澀時往往拒讀者於千里之外。歷史的書寫需要趣味性吸引讀者的興趣,傳說則是歷史書寫時最佳調味料。本書打破歷史書寫的藩籬,藉由傳說、故事,讓歷史故事更貼近生活。
文/臺南市文化局局長 葉澤山
作者的意圖十分明確,身為臺南子弟,他欲將府城輝煌的歷史說與讀者聽。這是近乎教科書的重責大任,讓小說來承擔,很危險,一不小心就可能寫成歷史小 百科。但作者是練家子,他透過林氏家族和一只錦囊的因緣,出入四百年的歷史時空,情節綿密,節奏暢快,彷如建了一座家族劇場,林氏祖先一一上臺,表演各自
的時代戲碼,流光婉轉,毫無冷場,好看!尤其蔡馨和林美智兩位女性風騷一時,引人遐思,在歷史舞臺上臺南女性可不曾缺席。
我不免想, 臺南遍地都是故事,如果鄭和下西洋在此汲過水的大井頭都成了「民權路上的一塊井溝蓋」,想必保安宮賣杏仁茶、左鎮街上的阿吉桑,或任何一名臺南人,大概人 人家裡都有個錦囊,都有一段歷史,林家一族只是其中切片,故事源源不絕,臺南啊,真是意味深長的一座老城。
──《中國時報》開卷版前主編/文字工作者 李金蓮
《錦囊》既是生動的歷史小說,也是精彩的人文地誌。作者運用在地素材,藉由一只國姓爺的錦囊,從長久的歷史時光,串起世代的記憶,在古今時空的交錯之 中,開展一段又一段虛實相映的感人故事,也重構了臺灣的過去與未來。種種青春面貌與年少情懷,纏繞著異國、異族、異文化的身分糾葛與迷離,單純的情與愛竟
也透顯著化不開的幽怨哀傷,這是青年男女的故事,也是臺灣族群認同的隱喻。《錦囊》也是屬於臺南的文學寫作,臺江內海、一鯤鯓、安平、林百貨、東門城、開 山路、延平郡王祠、馬公廟、臺南神學院等,歷歷在目。捧讀這本奇書,彷彿經歷了一趟神妙的走讀臺南閱讀之旅。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吳玫瑛
這真是一本令人驚嘆的歷史小說!故事時間的長河,從遙遠一萬年前的一名左鎮人全神戒備地躲在風的翅膀下,打開感官,嗅聞著風帶來獵物的氣息開始展開…… 而以一只傳說中國姓爺的錦囊作為故事勾,穿梭古今地串起荷據、清領、日治、戰後來到臺南的現代時空,其間如過盡千帆的家族榮盛興衰與庶民的悲歡離合,令人
捲卷沉思;卻又以一塊神祕消失的遠古人左臉骨的化石回到故事的源頭,「分離的已經復合,每滴血又回到了血管,生命的故事又重頭來過」,作者如是低語。
打開第一頁,「風是他最好的朋友……」即欲罷不能地一口氣讀下去,如詩一般綿密且精鍊的文字、以史實與虛構交錯的情節、歷歷在目的寫實場景、溫暖良善的人 物刻畫……這個看似以國姓爺的府城開拓史為背景的故事,原來說的是我們每個臺灣人的心靈原鄉。「風是所有人的朋友」,作者於是以此句為故事作結。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黃雅淳
如果你讀過美國知名作家路易斯‧薩奇爾的大獎小說《洞》,千萬別錯過這一部兼具魔幻寫實與神祕氛圍的巨著。作者以如詩的文字摻揉歷史與想像,書寫臺灣 四百年來穿越皇權、戰爭、開墾、殖民時期的歷史片段。當你追蹤一只御賜錦囊的輾轉,透過幾個小人物的命運流變與家族興衰,彷若走進一部史詩般的電影:或是
眺望戰雲密布的臺江浪濤;或是跟隨平埔勇士,追捕隱匿叢林的獵物;或是來到舟楫紛忙的運河邊,聽商行的人聲鼎沸和苦力們的對喚吆喝,交織成古安平的繁華如 夢。一只錦囊背後的錯綜因果、層層謎團終將被你揭開,當你掩卷之時,也將如歌的行板,走過四百年的府城;走過一段再真實不過的臺灣。
──兒童文學作家 廖炳焜
臺南,擁有臺灣獨一無二的史前時代文化瑰寶,距今九十至四十五萬年前的「早坂犀牛」以及二至三萬年前臺灣最早的智人「左鎮人」,都曾在這片土地活躍;漫 漫時光流轉數十萬年,從史前進入歷史時代,臺南成為臺灣近三百年首都所在地,荷據、清領、日治時期多元文化交融匯集於此,綻放璀璨光芒。呂政達先生透過一
只國姓爺的錦囊,帶領讀者穿越時空,從史前時代跨越至現代,隨著錦囊所串連的故事,讀者彷彿進行一場以臺南為背景的歷史壯遊,既寫實又虛幻,既有歷史的真 實感,又兼具傳奇的魅力性;歷史與傳奇,看似衝突,卻在本書中完美融合。
呂政達先生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宏觀層面以歷史為舞台, 跨越史前文化至現代,微觀處則描述臺灣庶民生活,常民文化躍然紙上。他以在臺南的少年時光為靈感來源,書寫出一部貫穿古今的重量級小說,濃縮歷史的精彩片 段,更賦予豐富情節,文字活靈活現,內容則蕩氣迴腸。這本書不僅讓讀者對臺灣歷史演進有更多的理解,更能啟發現代台灣人,認真的面對自己生命的起源。
近年來,越來越多作家以臺灣歷史為藍本創作小說,而此類小說也受到廣大讀者青睞,足見過去被置於中國史脈絡中、不受重視的臺灣史,逐漸恢復其主體性。身為 讀者,我從這本以臺南為原點出發的小說裡,看到了臺灣人身分的認同,也希望這類關於臺灣歷史的書寫,讓更多人珍愛這片土地,並引導下一代建構起以臺灣為核 心的史觀和認同。
──臺南市長 賴清德
願望是憧憬,是期盼的美好,讓人如置身其中,喜悅流露。
願望是目標,是行事的動力,讓人如近在咫尺,喜悅可得。
願景,看似遙遠,卻可藉由築夢踏實而實踐。
長期經營親子客廳讀書會,我認為成員彼此間拋出問題,進而回答、追問,可增進情誼。
親子共讀,布題也很重要,因而我相當重視親子對話的質與量。學習,首需知如何學習。如何學習,老師是關鍵。 家長也是關鍵。
學習,是與世界的相遇與對話;是與他人的相遇與對話;也是與自己的相遇與對話。從既知的世界出發,探索未知世界的旅程;是一種超越既有的經驗與能力,形成新的經驗與能力的挑戰。關鍵之一是師長對於問題的設計與掌握的時機,對孩子的理解與學科概念的精準串聯與構築鷹架。
閱讀呂政達《錦囊》如探囊取物,欲罷不能,您也可以試試看,親子教養可以很浪漫!
──教育部閱讀推手/天下雜誌閱讀典範教師/臺南市新化國小教師 楊春禧
爸爸和媽媽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因為自小到大,我的休閒假期是在閱讀歷史、府城遊蹤中度過。全家人曾經參與臺南米其林三星之旅,透過府城歷史散步,讓 我緬懷古人,發思古之幽情,凡事儘量往好處想,就可擁有正能量。閱讀呂政達《錦囊》,我覺得它是家族、臺南的歷史,更是整個臺灣歷史的縮影。特色如下: 一、取材精當;二、內容豐富;三、故事生動有趣。
我很喜歡它。透過文學的薰陶,讓我獲得歷史、文化的精髓,因而增長見識和智慧。推薦您閱讀!
──國立臺南一中 王政淯
我曾經投稿數十篇作品,刊登在國語日報上,其中一篇是〈風光明媚大臺南〉。府城其人其事,豐富這座古都,我愛府城。把自己歸零,用朝聖和海綿的心態學習,不斷地問問題、想問題,這是我閱讀與寫作優異的祕訣。閱讀呂政達《錦囊》,我喜歡作家穿梭古今的精采手法。
這部長篇小說讓我跟家人共讀,透過問問題增進互動,因而更加熱愛府城。這本書能讓你沉迷其中,欲罷不能!
──臺南市立後甲國中 王政傑
關於國姓爺鄭成功在臺灣的故事,其實,我們聽了很多,真正深入理解卻極少。一般人「近廟欺神」,總覺得歷史場景都在周遭,以為隨時都能取得資料毋須深 究,然真要解讀這段歷史,才發現史料龐雜竟非想像中的易懂易得。身為臺南子弟的呂政達先生,運用小說迷人弔詭懸疑手法,不僅巧妙將鄭成功作為關鍵人物時
期,臺南府城風華盡顯無遺,還順帶鋪陳出臺灣四百年歷史軌跡脈絡,猶如戲中戲的寫作手法,挑戰作者多元整合能力,也大大滿足讀者各方需求。臺灣歷史層次脈 絡分明、小說劇情節奏明快絕無冷場、早期地理環境考證查實……
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臺灣歷史小說。
──「非讀BOOK臺南愛讀冊」電視節目主持人/國立南大附小教師 溫美玉
風如段故事,狂野吹頌著,卻淡淡地成一抹回憶,令人細細回味……
風在訴說一個故事,關於聲音、戰爭、石頭、錦囊的故事。這故事有種靈性,反覆繚繞思緒,迴響空洞的耳邊。國姓爺所賜予的錦囊,巧妙地牽起一條線,串連了 許多人的生命,儘管來自不同時空,但他們卻心靈相通。作者以科幻的口吻,緩緩道來久遠的過去;以說書人的語氣,輕輕訴說此刻的現在。我們流著一種血,一種
來自祖先身上,那沸騰的熱血;我們聽著一個故事,一個來自長輩口中,代代相傳的故事……
這故事如風,輕柔吹拂過,卻深深刻畫於腦海中,令人欲罷不能……
──天主教聖功女中 陳佳音
一只錦囊的故事,在文化古都臺南,譜成了一首和諧的交響曲,這首曲子加上演奏家精心編排,演奏起來別有風味,成為一首動人心弦的樂章。
如果跟著這只錦囊,我可一步一步地踏上這首交響曲的音符。跟隨它所背負的眾多故事,我能想像自己成為其中的人物,甚至那只故事靈魂角色的錦囊,這樣,我就能跟著歷史,飛躍蟲洞……
讀了這本書,我彷彿真的身歷其境,透過作者細膩的描繪,那些景色就活生生地顯露在我面前,讓我可以真正地觸碰到歷史,使我對這從小生活到大的臺南,又多 了點朋友的情誼,說不定我下次再看到那些早就看慣了卻又陌生的古蹟,心裡也會升起一股說是敬畏,卻又多了點真誠的熟悉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 趙昱婷
作者序
小說書寫的生命探源
我的生命有一半住在臺南,青年後才移居臺北。審視我的寫作取材和範圍,基本上是從臺北的都會生活與經驗的碰撞出發,近年來也開始從青少年時期的回憶尋找寫作靈感和題材,這個過程,並未經過策畫或設計,但許多作家也出現過類似的生命回顧歷程。
從遠大一點的文學視野來看,呼應文學探源和尋根的風潮,不過,閱讀已故作家李潼的《少年噶瑪蘭》卻讓我確信,這趟臺南的文學寫作,不一定是要如實地從個人的經驗開始和完成、出發和抵達,如果只是依照此書寫慣態,我勢必又會去寫我所熟悉的散文和雜文路線。
其實,題材在我少年生活體驗裡俯拾即得,那就是臺南人生活裡到處見得到、呼吸得到的國姓爺鄭成功的文化氛圍。當然,我不準備寫一本以鄭成功為主角的小說,而是以國姓爺的開拓史為出發點,圍繞著臺南歷史時空的小說,融入我所理解、尋找、探索以及想像所及,並嘗試將四百年來的某些歷史片段當作書寫的焦點,完成一本屬於我的、臺南人的,甚或是臺灣人的小說。
這部小說,將環繞在國姓爺獲賜的一只錦囊,藉由四百年來這只錦囊的下落,串聯出臺灣穿越皇權、戰爭、開墾、殖民地時期的種種記事,在歷史的記憶身影裡,書寫臺灣人形塑身分認同的種種面向。
後 記
沒有戰爭的海岸
請為我敘說海洋的訊息,夏日圍繞的海洋。竹筏馬達劃過潮水,灰色的帆布篷在風裡翻動著,傳送來濃濃的氣息,我們的船駛過龐大的蚵架旁,永遠的靜默蔓延在水底裡。遠遠地,翻過對面沙洲的木麻黃林,才是海峽,那當地的導遊透過擴音機說,這是一片永遠風平浪靜的海面,蘊藏豐富的漁產,候鳥相約飛來過冬,颱風總在海口處轉彎。我默默觀看眼前的海景,就是這裡了。
竹筏停靠在沙洲上,安排遊客觀賞招潮蟹的洞穴,沙岸邊,有漁家搭起帳幕賣炸蚵仔。下船,我獨自走進木麻黃林,眺望平靜的海面,心內沒來由地傳來一陣悸動,就是這裡了,我放下負在肩上的包裹。早晨的霧仍然沒有散去,再遠,還能看見些什麼?我彷彿看見昔日的海戰場,戰艦從甲板射出繩索勾住敵船,燃燒的帆,溫度節節升高,將旗仍在火海裡飄揚,砲彈射進海面,激起龐大的水柱,數百艘戰艦的將兵一起吶喊,回音飄盪,繼續迴旋在歷史裡。在多年後寧靜的夏日海岸,我窩起手向遠方的海看過去,卻只見鷗鳥的盤旋。
那場海戰,將改變島嶼的歷史,但將軍並不知道,他永遠不可能知道了,船艦才剛靠岸,他就發下號令,率領兵士去追趕敵軍。據說曾有部下勸他紮營休息,將軍卻執意追趕,他必定曾匆匆穿過這片木麻黃林、海岸,看見我身處的這片風景,海風同樣從我們身旁掠過,他們繼續趕路,當年,會有靜默的蚵架,鹽田和虱目魚塭嗎?
八百名兵士追進平原深處,當年,這裡有高大的蔓草叢,漫無邊際,一走進去即迷失方向,只有荒疏的日頭指引。他們說不定見過驚慌走避的鹿群,幽靈在寂寞的草原間行走,驚動候鳥從他們腳邊飛起。黃昏,他們紮營,造飯,將軍卸下浸透汗水的戎裝,設想敵軍的行蹤。然而,就在那夜色即將掩來的時刻裡,將軍顯然並沒有設想到,歷史將為他設置的命運。
將軍,我細聲念著他的名字,如海岸邊的祈禱,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我們的血管裡都流著他的血。時日如舊,仍有灰鷺停留在露出海面的木柱上,文風不動如同雕像;仍有黑面琵鷺群圍成圓圈,合力追捕水裡的魚隻;烏魚在陽光裡扭動尾鰭,閃亮鱗片。海岸彎成擁抱的姿勢,留住這一灣水,在內陸和外海間,如同海洋的記事簿,那場戰爭的記憶,也必然書寫在某段海面的紋痕上,隨著潮汐翻騰,在從不瞑目的沉船間,長滿青苔的盔甲,魚兵蝦將的巡邏取代了死去的誓願,他們還來不及登上期待的海岸。
我們家族的記憶,則一直保藏在舊厝的廳堂。小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即對供奉祖先牌位邊的書卷感到好奇,卻都要等到滿十八歲,才許開盒觀書。我始終記得自己的十八歲,天色尚明,廳堂裡長明燭佇立供桌兩側,祖父燃香祝拜,請下用紅綢緞布包好的木盒,「感謝將軍的庇蔭,家族裡又有個十八歲的男丁了。」我心知祖父嘴裡喃喃念著的男丁就是我,低下頭,翻看盒裡的將符、璽印和手書,經過幾個世代的翻閱,那方宣紙已顯泛黃陳舊,稍稍褪色的墨水寫著「一死豈憑丹心知,忠勇付與子孫訓。」四百年前寫字的人心內充滿悲壯,恍如準備要在死神面前繳械了。四百年後,輪到我來看這幅字時,我看著祖父虔誠的臉孔,內心底滿是惶惑:祖父,你還要派我去打那場戰爭嗎?
那場戰爭的結局是悲麗的滅絕,敵軍趁暗夜悄悄包圍過來,襲擊,火槍從草叢間伸出,在明滅的彈火間,只有幾名兵士突圍而出,讓後人得以了解那晚的事件。後來的史家一直想知道,為什麼那天將軍執意要追趕敵軍,然後遭受死亡的命運呢?黑夜裡響起的槍聲如高牆包圍,將軍臨死的心緒在想些什麼?歷史在喧嚷裡爭辯多年,在巨大的時代變遷與轉動裡,筆尖沾著墨水,卻沒有將這段最後的追趕寫定,他們一直想知道,失去主將的這場戰爭,應該算是勝利,還是失敗?
在長久的歷史時光裡,我們終究都失敗了。我彷彿看見將軍仍伏在桌案上,拿著毛筆寫字。天色尚明,氣氛凝重,從他緊握的手勢裡寫出來的楷書,也像接受發號施令,在宣紙上站好自己分派的位置。他的神情鐵肅,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慢慢地寫,好像想把他來不及用完的壽命、他分配到的時間,都耗盡在這場書寫裡。隔天,他就要離開家人,帶領艦隊遠航了,那時,他是不是已預見自己的死亡?
我們這些還沒有輪到出場的子孫,在許多年代後屏息觀看他的書法,長明燭嘆息垂淚,黃昏的家訓,一去不回的青春歲月,全都在攤開書卷的剎那間湧向眼前。那次的出航從此決定家族的命運,像連根拔起的盆栽,植栽在一座熱帶的島嶼上,回歸線向南,北極星當空,然後發芽、結枝、連葉,孩子們跑過廳堂,高聲喧鬧,總覺得他仍坐在神主牌位裡,眼神炯炯向這邊的方向觀看,陌生而又熟悉。
小學五年級,我第一次在歷史課本裡看見他的名字,心裡滿是驚詫,咦,這個人從我們家的神案走了下來,轉身,就走進歷史課本了。那場海戰仍未結束,雖然結局勝負已知,卻每在有人翻開歷史課本時,繼續漫天的烽火,海上全是燃燒的船艦,屍體漂浮,魚群紛紛閃避,鷗鳥躲藏在礁岩間,而將軍的船艦仍將一再地靠岸,全身戎裝,刀箭齊整,發下號令,開始他最後的追趕。
那天下課回到家,放下書包,我急忙拿著課本到祖父面前:「阿公,你看,這個人的名字,也出現在我們的課本裡呢。」祖父靜默地望我一眼,笑笑,好像是他早就知道的祕密。然而,我們有沒有遺傳到他的勇敢、他面對滅絕時的鎮靜自若、他的執著?我們能不能像他一樣,在死神來臨時解械,放下手裡的弓箭,卻仍執意抬起臉孔,露出傲然笑容?
我的祖父一生都在農事裡度過,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夏季微風襲來時,他躺在廳堂後側的榕樹下乘涼,有一天午後,祖母來叫他進去吃飯,他卻沒有再起來過,就這樣解械了。長一輩的都說,日治時代祖父做過里長,曾經解救過鄉人的性命。故事有許多版本,常聽到的是日本警察上門來抓那名鄉人,祖父用日語騙他們說,門裡面有蛇,嚇得日本警察不敢進去,這也該算得上是勇敢吧。直到去世前,祖父從沒有提起過這段往事,然則,祖父,你還要派我去打那場戰爭嗎?
再下一代,我的父親放棄農田,轉到小學裡教書,相親結婚,生下我們,我從不記得他有可稱為勇敢的事蹟。然後到了我這一代,我常覺得自己的個性像足父親,喜歡獨處,一個人去旅行,在陌生的遠方得到心靈的釋放,正如眼前靜默的海岸,木麻黃在風裡翻動,萬古的浪潮向前推進海沙,沉浸,迅速退去,一如往常沒有多餘的爭辯。潮退,招潮蟹才從小小的洞穴現身,爭先恐後的向四方散去,那是牠們的自然本能,那場海戰發生在這裡時,牠們還沒有出生,沒有占到觀看歷史的位置。眼睛如果望向海岸線,再遠,踮起腳尖來看,我還能看見些什麼?記憶的開端和結束,像鯨魚從海面驚鴻一瞥?
那導遊遠遠從木麻黃林走來,召喚我,該是返回去的時候了。他們世世代代都住在這裡,守衛海岸、蚵架和黑面琵鷺,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故事了,像綿綿伸展的海岸線,他認得這裡的每一株植物,叫得出每個鄉人的名。我們往回走幾步路,停下來交談,我說,請再等等,我還有件事要做。我提到那場海戰,提起將軍的名字和他必然的結局。導遊疑惑地側過臉來,咦,你怎麼這麼熟悉?是讀歷史的,還是有家族關係……我慌張地低下頭來,總以為只要坦白承認,對方就會拿歷史裡將軍的形象和眼前這副肉身做比較,想起讀國中時,歷史老師在課堂上提起將軍的名字,全班同學的眼神全投在我身上,試圖從我的神情、身影裡尋找將軍的模樣,但就算有,也已是稀釋過的血液,如蒸發掉鹽分的海水,被馴服的獸類,我同樣緊張地低下頭來。
這是祕密,噢,我一點也沒有遺傳到他的勇敢,常常,生命裡的一些小失敗,已足夠將我擊潰,抱著頭喊痛,總像有一根箭穿過渾濁的空氣,急急在後面追趕,聽見後面大隊人馬的嘶喊,火般渦漩從激戰的海面飄來,烏雲密布,我總是處在逃遁的隊伍裡,拚命地想逃進遠處高大的草叢,喪失所有的心神和意志,在絕望焦灼的谷底,這才會想起,像有人適時提著一桶冰淋向腦袋,是的,我血液裡留著將軍的血,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忠勇的後裔。我應該停下來,轉過身,對著侵襲的那一方伸出我的拳頭。
最後的時候,將軍並沒有伸出他的拳頭。就在戰場附近,有名農夫開墾田地,挖掘出八百多具骸骨,考古學家認定,應該就是將軍和部兵的埋骨處。其中一副仍戴著完整的盔甲,綬印,他的刀還別在腰側,還準備要拔出來,向看不見的敵人揮砍。他們發現鐵彈貫穿他的額頭,在頭骨底下一個圓圓的窟窿,這樣的死去,一定來不及細思自己將至的結局。
新聞報導出來之後,學術機構前來聯繫,表示要找與將軍有直系血親關係的人前去驗DNA,以確認那具骸骨的身分,全家族的成人聚在一起開會,決議由我代表。那天,我坐在一具陌生的儀器前,伸出手臂,針頭刺進來時會有微微的刺痛,我用另一隻手掌捏著棉花,心裡想著:「是啊,我把自己的血還給將軍了。」想像那枚四百年前的荷蘭鐵彈嵌進將軍額頭的感覺,巨大的疼痛進入腦漿,替代了所有的思考,我唯有在這種遙遠的想像裡,才能覺察到體內一絲的勇敢。
世代傳承其實像是一場血的割香禮,一代一代地分靈出去,他血裡的血,肉裡的肉,在眾人血管裡踏著慢板節奏行走。如果勇敢也確實是可以遺傳的DNA密碼,在迷宮般的基因圖譜裡,生命的訊息拼湊組合,完成所有的形態。如同嬰之未孩,早在我擁有這副軀體的欲望、想像、意志、懦弱和勇氣前,都脫離不了將軍的凝視。
我把自己的血還給將軍了,心裡這樣想著,那才是我自己的戰爭。檢驗報告出來後,確認了將軍的身分,我們計議迎回將軍的骸骨。時辰接近,在廳堂外,擠滿了攝影機和採訪記者,家族全體論輩排列相迎,堪堪將近四百年,將軍從荒草古塚回到了子孫興建的祠堂,歸位,奉祀,一死豈憑丹心知,將軍從長久的夢裡醒來,穿過熱鬧的空氣,絆倒一名搶鏡頭的攝影記者,他一一檢視陌生的子孫們,好奇這已是什麼年代?那場海戰後來究竟有沒有打贏?那只是我的想像。
我排在行列的最後面,默默祝禱,想起我自己的十八歲,祖父從神案請下書卷的神情。陽光在廳堂的屋頂跳躍。祖父,這就是你要派我去打的那場戰爭嗎?行列的後面,我知道還會有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在靈魂未歸位為軀體前,混沌的未孩,已經寫好了宿命的篇章,墨色鮮明,我們血裡的血、肉裡的肉、將軍的後裔,等待他們自己的十八歲。
將軍,我細聲念著他的名字,如海岸邊的祈禱,再細聲,則念給自己知道。那一刻,我還給他的血,又再度返回脈搏,將軍匆匆掠過我的身旁,如一陣永遠的海風,他回過頭望我一眼,但該是回去的時候了,我打開包裹,南風吹來,讓將軍的骨灰灑向海洋,回到沉船間繼續發號施令,將一切還個清楚,回到肉身和靈魂未成形前的宇宙,意識悠悠蕩蕩,歷史的勝敗功過也就由它去吧。我回過頭,陽光耀眼的潟湖,那群鷺鳥仍停留在白色的木柱上,等待追捕魚群,木柱浸在海水裡,只剩一截露出,從什麼時候開始,那些木柱就已插在這裡了呢?從什麼時候開始,鷺鳥群就懂得守在海口,等待漲潮帶進來的魚群?
回程,遊覽車穿過鹽田,漫無邊際的甘蔗田,在海岸線外,落日剪影貼著車窗,追趕著我們,多像那年將軍最後的追趕。海面上烽火尚未澆熄,落日也曾追趕在他們身後,然而,他的死亡才是一切的開始,他垂下的手從來不及拔出腰刀。
我閉上眼睛,當記憶逐漸冰冷,灰燼散開,在回家的路途上,將軍,請為我敘說海洋的訊息,夏日圍繞的海洋。
(這篇後記〈沒有戰爭的海岸〉為呂政達先生二○○四年獲得第十七屆梁實秋文學獎文學創作類文建會優等獎的文學創作作品,並非個人親身經歷。《錦囊》一書的創作靈感來自沙永玲女士讀此文後的建議……一切,就從這裡開始;而戰爭,真的還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