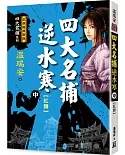推薦文一
陳雨航(出版人、小說家)
沉默於傳統武俠小說的書寫,其顛覆與創新不從今日始。人性對社會正義的需求,俠骨柔腸的嚮往,依舊存在,但已不為己足。《七大寇紀事》依然有著武俠小說特有的浪漫基因,但已非純然的江湖恩怨、兒女情長可言,那種浪漫已被更高更廣的理想與視野涵蓋了。
斯巴達寇斯奴隸起義,黑澤明《七武士》武士結合農民抗暴……斑斑革命史蹟,以及反映現實的藝術,莫不使人們熱血沸騰。《七大寇紀事》呼應歷史與現實,可說是一部武俠形式的「世界革命史」。亟待摧毀的舊世界,其意識形態和制度與若干現實世情若合符節,呈現了強烈的現代感。作者思索並安排各種制度和措施建立虛擬實真的世界,觀念既現代又前進。新的觀念結合新的形式,作者不避當代新辭,甚至學術名詞、論述。章節結構嚴整,文字密度高。是部超越類型、現實感極強的現代武俠文學。
武俠江湖固有退隱的傳統,但那畢竟是身在山林,本就是一種避世的態勢,不同於此,《七大寇紀事》是一個革命成功的廟堂,打下江山而能自動引退者幾希,小說主角幾乎從神格降至平民化的身份以及功成之後的飄然遠去,動作一樣,卻具有更深遠的意義,令人心嚮往之。
推薦文二
葉佳怡(小說家)
在由六帝神統御的廣遼土地上,代表死亡的「喪君」是最先消失的創世之神,卻也是永恆存在的魅影。於是世間起落皆為雙面刃:「自由」的敵人來自外在壓迫,卻也來自身體衰敗;「武功」同時抗拒並接受世界,卻也是存活必然的自毀。沈默告訴我們如何以肉身抵擋存在的虛無,如何以排拒成全平等的自由,如何以傷慟啟程,再以完整的面貌迎向絕美末日。
後記
武俠革命以後,武俠自由以前,在武俠末華麗裡
【大虛空記五部曲】終於來到第五部《七大寇紀事》,這是此一系列書寫計畫中的最後一部。從第一部的虛空王,到最後的七大寇,恰恰又回到溫瑞安的武俠角色,正成一個循環,也是我這三年間屢屢嘗試開發的書寫結構:環狀。
只是《七大寇紀事》不像《天敵》、《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有一明顯的雙向時間敘事,但仍然在各個方面都不難看到「環」的存有,如果閱讀中的你願意仔細想想的話。
說起來,波赫士〈環狀廢墟〉對我的影響十分重大。我意欲在小說徹底實踐他的想法,因此才有了《天敵》、《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而【大虛空記】最後的《七大寇紀事》某個程度來說也是我所能完成的、在廢墟上最淋漓的大幻影。
一開始,我對【大虛空記五部曲】的想法就是要每一部敘事結構皆不同,第一部《誰是虛空(王)》是多聲道獨白的噪音小說,第二部則是十三名人物的第二人稱敘事大集合,第三部《天敵》採用環狀書寫,以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正逆循環開展,第四部《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同樣是環狀書寫,但改為全第三人稱,以兩個人物際遇分開敘事,第五部《七大寇紀事》以說書人的引言帶出六十年的傳奇事蹟,將北境的當下與過往聯繫起來,是一種隱形(或潛行)的環狀結構之變體。很高興這樣子概念先行的書寫,我應該不算有搞砸,且不止是在武俠,就算是在嚴肅文學裡,也是初見或者少見的。
在溫瑞安寫下的眾多人物裡,最為吸引我的人物一直是沈虎禪。這個人的作為帶著某種特別的意味,尤其是他的思索與覺悟。而且他不介意自己為寇,擔當惡名這件事對他來說,顯然是無所謂的。他走他的正路上,即便變成他人口中的歪魔邪道,他亦是甘之如飴的(──這應該不難想到近來在漫畫英雄改編電影裡成為石破天驚之作的《黑暗騎士》吧)。
我不確定溫瑞安寫這個角色時是否一心讓他站在體制與權力的對面,但我在寫七大寇時則是紮紮實實地把這個層面演化開來。天衣憐魔一開始的人物原型確實是沈虎禪,當然後來天衣憐魔便脫離該角色的影響,自行其路,我投注了更多自己的殘片在天衣憐魔身上。實際上每一個七大寇都裝載著我的碎塊。這原來就是書寫的必然機制。你不可能禁止你所書寫的人物攜帶著你的某一些靈魂片段。
另外,七大寇的原型參考,自然不免要跟以下這些名作扯上關係,如《城邦暴力團》的七老、徐克的《七劍》、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乃至於黑澤明的《七武士》等等……
而其實,溫瑞安筆下的七大寇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確定的人選出來(一開始是五大寇,後來又變成六大寇,似乎溫瑞安初期還有點拿不準),主要是沈虎禪、溫柔、張炭、唐寶牛、方恨少五人,剩餘的兩個都還沒有真正現身。
但我的七大寇卻是一個都少不了,每個寇都有自己的故事想說、必須說。而七大寇要爭取的是就是自由。從武藝上的肉體自由,到擺脫神風帝聯階級統治的心靈自由。自由從來不是天生的,自由絕非只是一種愉悅姿勢而已。它很可能是與苦難孿生不棄不離的某種存有狀態。我的七大寇,如果說有什麼非說不可的意義,那必然是在於反叛,在於革命,在於思索吧。
這本書的武學系統特別要向詩人隱匿的第一本詩集《自由肉体》(雖然我更愛她的第二、第三本詩集《怎麼可能》、《冤獄》)致謝,七大寇江湖所用的武藝概念全都從自由肉體這四個字進行發想的。當然米蘭.昆德拉也是這本武俠最主要的精神支援者。小說每一部的名稱都是取自他的著作,並且竭盡我所能地描述與思索其書裡的各種觀點,將之轉換為武俠。而唐諾對個人戰爭的看法,以及本小說前頭所引用波赫士和卡爾維諾的文字,也都是我想要盡可能轉涉在小說行文之間的最好的觀點。我總是對這些偉大的書寫者充滿感激。因為有他們先行,我才能跟著後頭,逐漸走出一條崎嶇但自由的路徑來。
在多年以前,武俠曾經作為一充滿高度娛樂性的小說載體。但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是的,青春已逝去。自從2011年重新回到出版市場的《天敵》到2012年《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以及同年我開始擔任明日武俠電子報主編以來,至此我慢慢不得不接受武俠邁入老年時光的事實。電視、電影、電動、On-Line
Game、智慧型手機,等等,無一不是武俠的天敵。武俠在這些大敵的環繞下,已經垂垂朽矣。盛世邈遠,武俠再也無法回復到強大的位置。這是不爭的事實。
武俠的壯年期已然宣告完結。從遠古時期的《刺客列傳》到古典時期(也是嬰兒期)的還珠樓主、平江不肖生等人,還有少年期的王度廬、鄭證因等人,乃至於金庸、古龍、司馬翎、梁羽生、溫瑞安、黃易諸雄所盤據的黃金現代(壯年時光),以及現在的,看來百廢待舉的武俠──我所處的當代,確確實實是武俠的老年期無疑了。
武俠的偉大時光已經完全燃燒殆盡了。我也不再存有興盛復還之的妄想。
但也因為武俠是老人了,無須再理會市場機制,再也不需要去迎合某些固定的標準,所以能大大方方、毫無顧忌地寫著心目中武俠最後的絕響。這是武俠可以全力開拓晚期風格的年代。
是了,武俠衰老,走進末世,但也因此獲得了接近純粹的自由。在當代的武俠,自由敘事、自由風格、自由概念的可能,屢屢獲得創新。於是,武俠便擁有了我的結構派(魔幻派)、黃健的解構派、徐皓峰的禪派、滄海未知生的未來派、施達樂的台客派、徐行的連環派、趙晨光的BL派、盛顏的耽美派、喬靖夫的狼派等等,這正是「武俠末華麗」之景,難能可貴,爾後恐怕再也不容易目睹如此新鮮活辣的、多種迷人風光崛起的時代吧。
當代最重要的知識份子艾德華.薩依德說的晚期風格(或者也會是日本大小說家大江健三郎的,晚年的工作),我想正可以拿來印證武俠的老年風景,既是不合時宜的,不圓融的,也是否定性的風格,更是不願意被收編的異類主體,薩依德寫道:「……你其實根本不可能在『晚』之後繼續發展,不可能超越『晚』,也不可能把自己從晚期裡提升出來,而是指能增加晚期的深度。……」他且說:「……它們超越它們的時代,在大膽與驚人的新意上走在它們時代前面,另方面,它們比它們的時代晚,也就是說,它們返回或回家,回到被無情前進的歷史遺忘或遺落的境界。……似乎完全座落他們時代之外,他們返回古代神話或古代形式,向史詩或古代宗教儀式尋求靈感。現代主義是弔詭的,它與其說是求新的運動,不如說是一個老化與結束的運動……」
我以現代語感重塑武俠句法、人物經歷、場景和武藝,甚至採用史詩格局及大量神話(魔幻)的氣氛加入武俠裡,或者其他武俠人屢屢借用他領域成分擴大、加深武俠類型的焦慮性作法,無不是對武俠晚期風格的具體表現--
我一方面感覺到我這一代武俠人的集體悲劇,但一方面又欣喜地品味終於自由的滋味。武俠就要毀滅了,然而正因為如此,它才能擺脫某些先天的要求與限制,走向更具有深邃感的境界。從某個面向來說,武俠也正在啟動革命。
而這是每一種衰亡的藝文類型都要面臨的局面。一如曾經大風光的歌仔戲或黃梅調,眼下也只能在國家戲劇院裡倖存。武俠或許和它們一般,都已經退出大眾的通俗場域,必須走向精緻與藝術(也就是少數化)的完成領域。
是了,我們這一批武俠人恐怕是武俠現代主義的第一線戰力,也是最後唯一的了。我們正在返回或回家,我們正在被歷史遺棄、遺忘。但我們也正在繼續增加武俠的深度,繼續走向一個古老與結束的,晚期的運動風格裡。
寫完【大虛空記五部曲】,我終於更明白武俠對我的終極意義。一意孤行地跟著武俠展開大膽而新意但其實又是衰弱而年老的冒險的我,在往後要寫的【武林異色譜】九大卷,必然會更覺得安心與自在。【大虛空記】有龐大的天下五區,我具體構造中州、東土、南域、西疆、北境的風土民情、武林生態,但到了【武林異色譜】,將要打散統一的概念,轉向更輕靈、更片段的武俠存在。
在這裡,真的要特別感謝編輯鄭建宗、主編劉叔慧的辛苦與支持,以及所有協助過這本小說成形的明日人,還有願意讀武俠的妳∕你。謝謝你們願意和我一起繼續在武俠的蒼老餘生裡走這麼一段路。對我來說,是彌足珍貴的陪伴與見證。
接下來,我將會持續地書寫並目送著武俠緩慢而自由地走向墓穴,直到武俠消滅的徹底到來。而在武俠最後的歲月裡,也請你們跟我一起在解放後的武俠裡感受、呼吸它的全然自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