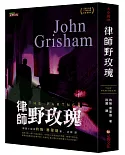推薦序
在深淵邊緣凝視黑暗,幽默與溫柔仍堅定放亮。文∕臥斧(作家)
一九八九年,詹姆斯.柯麥隆(James Cameron)拍了一部叫《無底洞》(The Abyss)的科幻片。
雖然許多評論認為一九八六年由柯麥隆執導的《異形2》(Aliens)當中隱含並成功地闡述了許多女性議題(包括對懷孕的恐懼及發揮母性時的力量),他在一九九七年的作品《鐵達尼號》(Titanic)甚至獲得了奧斯卡獎的肯定,但我始終認為柯麥隆的強項在運用特效製造聲光刺激,是個不折不扣的商業電影導演,他的電影爽快過癮,但也大多僅止於此;《異形2》當中的女性議題其實只是照第一集的原始設定、依好萊塢慣例於續集裡加油添醋的結果,而《鐵達尼號》當中的愛情敘述,根本是一廂情願地膚淺。
這樣的問題,在《無底洞》當中更是明顯。
請別誤會,《無底洞》其實是一部好看緊湊的科幻電影,問題在於,柯麥隆雖然巧妙地使用當年很少見到的電腦特效,創造了許多令人直呼不可思議的畫面,但他很明顯地並不想只做到這樣,所以試圖再將反戰∕反暴力以及愛情議題加進電影當中。可惜的是,反戰議題因為只被簡單帶過,雖然可取,但畢竟缺乏深度;而男女主角之間愛情議題的發展過程及結局,則可清楚地看出導演的男性本位取向。除此之外,柯麥隆還在本片開始的時候,引用了一句尼采的話:
「凝望無底洞的時候,無底洞也在凝望你。(If you gaze for long into an abyss, the abyss gazes also into you.)」
以《無底洞》一片視之,這句話沒有什麼問題;但事實上柯麥隆在尼采的話裡頭只挖出這一段來,不免有點兒斷章取義的味道。因為若要完整地明白原意,重點其實在柯麥隆沒有引用的前一句話;這段文字,完整看來應是如此:「對抗怪物的人,應當心別讓自己也成為怪物。倘若你凝望深淵的時間夠長,深淵也會凝望你。(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might take care
lest he thereby become a monster. And if you gaze for long into an abyss, the abyss gazes also into you.)」
這段話,用來描述《黑暗,帶我走》一書的中心主旨,似乎再恰當不過了。
我並不是為了引述這段話,所以先把大導演柯麥隆抓出來同大家發了一篇牢騷,而是因為除了我想用來描述《黑暗,帶我走》的句子與《無底洞》的引句有這麼點兒淵源之外,無獨有偶地,「暴力」與「愛」也是《黑暗,帶我走》一書中的重點,而且更要緊的是,《黑暗,帶我走》同樣是一個商業元素齊備的好看故事,但如果要比較內涵的話,勒翰的故事,講得可比柯麥隆好多了。
《黑暗,帶我走》是丹尼斯.勒翰「Kenzie/Gennero」系列的第二部作品。
這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是已經出版中譯本的《戰前酒》,系列主角是在波士頓執業的私家偵探二人組派崔克及安琪。故事的第一人稱主述者派崔克受地方政治角頭的請託,去尋找一個原來在市政大樓工作的黑人清潔婦--政治人物指稱,黑人清潔婦帶走一份機密文件,然後不告而別。派崔克與安琪找著了清潔婦,但對方辯稱自己帶走的不是文件,而是別的資料;在派崔克陪著清潔婦到銀行保險櫃要取出物件時,突然遭到伏擊……
延續這種由小問題扯出大事件的方式,《黑暗,帶我走》,故事開始。
勒翰先以自己慣用的手法替故事揭幕:主述者派崔克受了重傷,正在緩慢復原;幾個朋友偶爾來訪,安琪不知去向。在這種類似「結局」的開場之後,時空再拉回事發之前,開始敘述整個案件的始末經過--一位名為黛安德拉.華倫的心理醫師,透過派崔克在大學任教的舊識艾力克.高特牽線,向派崔克表示自己收到來自某人的威脅。一個自稱是黛安德拉.華倫學生的女子莫拉.肯錫向她坦承遭男友凱文.赫里易虐待,接著黛安德拉在凌晨四點接到凱文的電話,威脅要對她不利。黛安德拉擔心自己的兒子傑生可能會被牽連,惶惶不可終日;此時,經由艾力克的介紹,她發現派崔克也姓肯鍚,心想或許可以請派崔克介入調查。
於是在派崔克與安琪邊閒扯邊設法裝修辦公室的冷氣時,電話響起。
派崔克沒有叫做莫拉的姊妹、也不認識任何一個符合黛安德拉描述的莫拉.肯錫,但凱文是他和安琪從小就認識、一起長大的愛爾蘭黑幫分子,就派崔克和安琪所知,凱文與女人的相處情況不是買春就是硬來,並沒有固定的女友,在開始調查之後,也認為沒有人在暗中跟蹤傑生。正當他們覺得可以交差了事時,危機才真的漸漸逼近,不但安琪的丈夫菲爾牽扯其中,連派崔克的女友葛瑞絲及其女梅兒,都開始有了生命危險……
無論有沒有讀過前作《戰前酒》,大家大約都會對派崔克與安琪之間的關係感到好奇。
這兩個主要角色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好友,派崔克離過婚,根據《戰前酒》裡安琪的描述,派崔克的男女關係似乎有點混亂;安琪嫁給派崔克的童年好友菲爾,但卻長期忍受菲爾的拳腳相向,派崔克也因此與菲爾反目成仇。派崔克對安琪有毫不隱藏的好感,但安琪總是保持著適當的距離--這樣若即若離的關係,在經過《戰前酒》的事件後,似乎出現了更進一步的可能。
但在《黑暗,帶我走》當中,我們卻發現,事情似乎不是如此發展的。
安琪似乎仍與菲爾牽扯不清,而且還開始頻繁地更換男友;派崔克倒是開始與固定女伴交往,這位名叫葛瑞絲的醫生是個單親媽媽,與小女孩梅兒一起生活,不但與派崔克陷入熱戀,梅兒也很喜歡派崔克。於是原來有家庭的那人似乎開始動盪,而本來漂泊的那人則開始向安定靠攏--或者,看起來似乎是這麼回事。
因為,在這個故事裡,感情其實毫不遮掩地展露著它不可親、甚或殘忍的現實面向。
無論存在的是親情、愛情還是友情,相愛的人都可能會相互傷害,付出感情的一方可能只會得到暴虐的回應,彼此相互戀慕的角色還是可能同時與其他角色發展戀情、性愛甚至婚姻關係,而所謂愛情,在世間的道德標準當中,仍被分類成許多標籤不同的樣式:有些正確、有些不當、有些可以容忍默許,有些則需要被趕盡殺絕。感情從來不是終結暴力的良方,它會在暴力面前屈從、逃避、變形,或者毀滅。
有些時候,感情本身,其實就是暴力的。
無論是直接訴諸肢體行動的「愛之深,責之切」,還是以言語姿態漠視或刺激彼此,都是感情關係當中的暴力型式;這類情感暴力在《戰前酒》中著墨甚多,在《黑暗,帶我走》裡也隨處可見,勒翰告訴我們:在現實當中,各種情感都不像在童話故事裡的那樣單純,它們會混絞自私、慾望、利益及報復,雖然有無私的代稱,卻有市儈的長相。
而且,《黑暗,帶我走》當中的暴力,還有許多其他面向。
街頭幫派紊亂糾葛的衝突、政客光鮮外套下的謊言、已經沉潛許久現今終於反撲的過往陰影,以及各式日常生活的、不誇大華麗的、非好萊塢式的暴力,隨著故事的進展,開始一樁接一樁地浮出檯面;而在《黑暗,帶我走》當中埋得最深、關係牽扯最廣的伏筆,或許就是「因為要制止暴力而使用的暴力」了。
當然,提及「以暴制暴」的作品,數量其實很多,尤其是商業動作片。
許多創作者喜歡在電影裡用這種方式來反制暴力,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這種正反雙方硬碰硬、大幹一場快意恩仇的情節,不但具備商業的賣點、能夠傳達「邪不勝正」的傳統是非觀念,更能讓閱聽者藉此發洩情緒,畢竟在日常生活當中,不大可能有這麼直截了當、血花火光綜合大爆破的豪爽解結方式。
請容我插播一則真實小故事當做例子。
學生時代的某年,有回國文老師不知怎的,在課堂裡把話題扯到電影《終極警探》(Die
Hard)上頭;老師講到電影的最末,忙了大半部電影的布魯斯威利與劇中妻子一起離開案發現場時,一個記者上前想要採訪,被女主角二話不說地狠揍一拳。「人家明明很累了,他還硬想要追獨家;」老師說,「真是被打活該。」事隔多年,我仍記得平時溫和的老師在提及這個橋段時,臉上藏不住的那個表情--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愉悅,一種對劇中角色在面對言語暴力時、還以肢體暴力的一種認同。
但事實上,我們在銀幕外頭的現實生活裡,本就一直進行著「以暴制暴」的動作。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透過立法程序,賦予人民保母警察先生們「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尋常百姓如我們,希望能用這種方式保障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維護法治社會的平靜。許多人會認為以德報怨、以教育感化暴戾,才是消弭暴力的正確方法,但事實上,大部分人也都心知肚明:當暴力正在發生的時候,最簡單直接迅速有效的制止方式,就是實行另一個暴力。
這類的情節在推理小說裡頭也十分常見。
古典流派的神探們大多只管破案,其他事情就擱到旁邊去了,似乎同這個議題比較扯不上邊;但在冷硬派的故事裡,偵探們大多自己就攪和在整團爛污當中,警方政界等等擁有合法權柄的角色大多又使不上力,所以他們有時就會自己擔任起裁決的角色,以暴力反制暴力,在一己之力所及的範圍之內維持正義。在大部分的故事裡,閱聽大眾們也都能夠認同他們的做法,甚至一如我當年的老師那樣擊節讚好。但,勒翰在《黑暗,帶我走》當中,提出了另一個視角:
如果這些角色們認定的「正義」是偏斜的,那怎麼辦?
正義或許有某種普世認定的標準,但在每個人的心中,都還得加上自身經歷、教育水平、生長環境及其所服膺的道德準則等等條件,才會形塑出私我的正義樣貌--這些一概名為「正義」的觀念,其實個個不同。而為了這些「正義」,可以對不義之人使用多少暴力?用所謂的正當理由行使暴力時,身旁原來與暴力絕緣的親友,是否會因此受到波及?暴力的本質都一樣,但因不同理由使用時,是否當真就有不同的意義?
更重要的是,究竟有誰夠資格去判定何為「正義」、何為「不義」?
暴力這匹獸難以駕馭、極易失控,在以暴制暴的時候,我們能夠讓這匹獸停在哪條界線之內,才不會讓我們從抗暴者變成施暴者?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力氣,在把暴力放出籠柵之後再將它拉扯回來?此時此地讓我們決定釋放暴力的正義標準,是否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或者符合更高階、更無私的道德標準?我們在行使暴力的同時,是否讓暴力的黑暗影響也肆蔓到周遭其他根本無涉此事的角色身上?
《黑暗,帶我走》中每個主要角色的作為,都與這些暴力議題息息相關。
有的角色帶著暴力的血緣或者背景,卻極力不去碰觸;有的角色已經做過以暴制暴的行為,但無法控制闇暗的觸手向四周擴延浸透;有的角色只知道以直接、放肆的暴力模式來過日子;而有些角色則深深地沉入漆黑的黯裡,服從、陶醉、享受甚至教導別的角色如何接受黑暗的引領,讓黑暗執起他們的手,拉著他們向無底的人心根柢潛去。
而救贖的亮,還在伸長手臂仍無法觸及的遠處。
派崔克時而尖酸時而自嘲的敘述,讓故事的沉重基調顯得比較輕鬆,而角色之間的情感羈絆,則讓故事裡嚴苛現實的稜角稍稍和緩,多了一點溫暖。是的,當世界被黑暗緊牽著手朝濃稠的惡意中心狂奔時,幽默與溫柔,或許正是攢著另一隻手的反向力量,讓故事裡的角色勉力將自己維持在光明與闇暗交雜出現的灰階人間,讓他們在奮力對抗怪物之際不至於化為暴戾的獸,讓他們在長久凝望深淵的時候,不讓深淵望進他們的內裡;也讓我們在讀罷這個故事之後,仍能咧開一個笑臉,回頭面對書本之外,同樣充塞著不義與狂虐的世界。
勒翰牽起我們的手,帶領我們走向深淵的邊緣,向其中探望。
他沒有給我們什麼絕對的答案,他只是說了一個好看精采的故事,要我們在閱讀之後自行思索,在我們望進深淵時,陪在我們身邊。深淵當中的獸類正在相互撕咬殘殺,它們的裝扮個個不同,但長相大同小異;當它們扭過頸子向我們凝視、伸著臂膀歡迎我們的時候,勒翰提醒我們,我們的另一隻手掌當中,還緊緊握著某種值得保護的笑意和溫柔--這是靈魂當中永遠不會幻化成獸的部分,這是當我們站在深淵邊緣凝視黑暗時,仍持續綻放著的,微小、但堅定的光亮。
如此,當黑暗帶我們行走時,我們仍能在惡意肆流的人間,找到一種美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