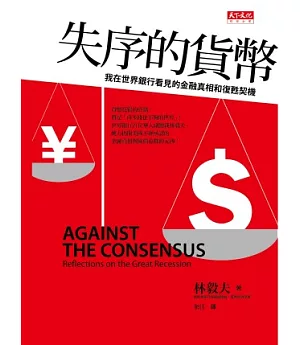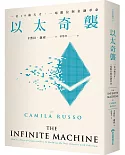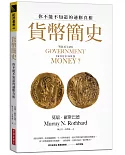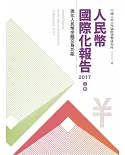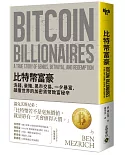推薦序
為全球經濟發展指引平穩新路
林毅夫教授是我當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同學。那是19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選派優秀人才,出國留學、攻讀博士的初期。在芝大的校園裡,林教授總顯得與眾不同。他是芝加哥大學曾獲諾貝爾獎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教授,特別從大陸吸引去芝大就讀的學生,林毅夫似乎是舒爾茨教授在「改造傳統農業」上,對開發中國家造成革命性影響的傳人。其後,林毅夫更將芝大嚴謹的經濟邏輯訓練,應用於中國制度改革之探討,並以系列方式,提出他獨到深入的見解。他的分析與意見,廣泛地在歐美學術圈受到極為高度的重視,並引發迴響。
以扎實研究助貧國擺脫窮困
林教授後來在北大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亦即現在的國家發展研究院),以及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為許多人所津津樂道,但他的貢獻,實不僅止於此。最主要的,林教授以中國經濟現象背後「人的行為」,建構一個能夠說明來龍去脈、因果關係的模型,因此,他不但在世界銀行時,在實務上幫助開發中國家邁向擺脫窮困之途,更在理論上,提出新的政策架構,做為追求健全、快速、永續、包容性成長之依循。
例如,林教授他在這本新書裡說明,「1988年時,中國政府推行雙軌制的轉型策略,一方面繼續給予傳統重工業部門的低效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開放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同時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成長」。書中更進一步闡釋,這種雙軌經濟制度的採行,雖在當時不為傳統經濟學界所認同,但卻是中國的改革之所以不至於出現後來東歐及蘇聯那樣大規模失業,以及社會和政治動盪的原因。林教授這些分析和洞察,對所有改革中的開發中國家,都有極大助益。
本書《失序的貨幣》分為四部,首部拆解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探究危機形成的真正原因;第二部則進入復甦共贏之路的討論,尤其針對全球基礎建設投資,如何創造全球共贏策略,有相當深入的著墨;第三部提出在危機後的多極化世界,低所得國家應如何把握機遇,追趕向前,尤其應如何發掘後進者優勢潛力,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在書中皆有許多具體建議。最後,第四部討論走向全新國際貨幣體系,更闡述在金融海嘯過後,世界為何邁向更多元的準備貨幣體系;美元在準備貨幣中的統治地位消失後,新國際貨幣崛起的可能,亦是第四部的探討主軸。
危機暫除、但風險處處的關鍵年代
展望未來,雖然危機暫除,但風險處處。美國財政懸崖,以拖待變暫時穩住;歐元制度在歐元國終於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也暫時得以維持;日本更在「安倍經濟學」寬鬆貨幣、積極財政、對外開放的三根支柱下,突破過去二十年困境。但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國際市場,只要一個不小心,這五年來的復甦之途,就可能功虧一簣。《失序的貨幣》探討的一些議題,更可做為觀察未來發展的指標,不論是金融監管、房地產泡沫、中國外匯存底的累積、世界各國收入差距的更加分歧、貧窮國家的難得機遇、全球貨幣秩序的重建,在在都是影響全球如何重新洗牌的關鍵。
前財政部長、台大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 劉憶如
自序
經濟解方在理論教條之外
世界銀行是國際上最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之一,其首席經濟學家被認為是全球經濟學界的最高職位,歷來都由人們仰之彌高的歐美已開發國家著名經濟學家擔任。我有幸成為第一位擔任此要職的開發中國家的學者,任期從2008年6月開始。
接受此任命時,我原打算根據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以及職責,將我二十多年來研究二次大戰以後,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改革和發展成功以及失敗經驗的心得,奉獻給全球的減貧事業。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剛上任三個月,就爆發了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
國際總體經濟和金融在分工上屬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業務範圍。這場危機突如其來,由已開發國家引爆,迅速波及開發中國家,給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和減貧事業增添了諸多困難。為了幫助開發中國家應對這場危機,避免開發中國家,甚至已開發國家再次發生同樣的危機,我必須分析這場危機的成因,思考其經驗教訓,並提出解決這場危機的建議。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正是我這些努力的成果,書中的視角將可能挑戰人們一般已接受的觀點。
身為一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知識份子,就像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去西天取經的唐僧那樣,我過去總相信西方已開發國家擁有一部真經,只需學會,帶回國來應用,就可以幫助家園實現現代化,走向繁榮昌盛,使中國重新屹立於世界已開發國家之林。幸運的是,在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初,我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機會,負笈現代經濟學的聖地—芝加哥大學,向包括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大師們學習現代經濟學。
四年寒窗苦讀,順利拿到博士學位後,我又到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1987年謝絕了幾所大學和世界銀行的工作邀請,滿懷信心回到改革開放事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家園,準備奉獻所學到的尖端知識,出謀劃策,幫助政府解決改革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但牛刀初試以後,卻讓我對在國外學到的那一套邏輯嚴謹、看似完美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否在中國運用,產生了疑惑。
1988年,歷經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首次遭遇到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一般經濟學教科書和尖端的總體經濟學理論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過熱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可是中國政府並沒有調整利率,而是進行治理整頓,以行政手段砍投資、砍專案,大量停止正在進行的工程計畫。若以當時的總體經濟學理論為準繩來評價,這樣的治理政策並不理性。
自亞當.斯密以降,整個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礎是假設人是理性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和尖端學刊上的理論,均以決策者的行為、選擇都合乎理性原則為前提,也就是決策者在面臨選擇時,總會從各種方案中選出其認為最好、最能實現他要達到的目標。
如果中國的通膨治理政策代表中國政府是不理性的,那麼現代經濟學的整個理論體系在中國就不適用。但既然中國政府的行為是不理性的,它的政策又怎麼能在1979年啟動改革開放以後,連續十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成長?很顯然,中國政府是理性的,面對1988年的高通膨,所採取的治理措施不同於教科書和尖端理論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不同於當時教科書和尖端理論中的假設條件。
那次經驗讓我體悟到,要分析中國改革開放的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不能簡單照搬教科書和學刊中的現成理論,必須深入中國經濟的現實,根據中國實際的條件限制,按照理性原則,自己進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論模型,才能發現問題的本質,提出對症下藥、藥到病除的方案。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導師西奧多.舒爾茨(Th eodore W. Schultz)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在他開始研究農業經濟學時,人們普遍認為傳統農業社會的農民是不理性的,因為他們不像現代工業社會的「理性」農民那樣儲蓄和投資,春耕、夏種、秋收、冬藏,一年忙下來以後,除了留些種子外,他們生產多少就消費多少。
但舒爾茨教授經過對落後國家農民的仔細觀察和研究後發現,這些傳統農業社會裡的農民不儲蓄、也不投資其實是理性的,因為在缺乏進步技術的情況下,儲蓄和投資的邊際報酬接近於0,對生活於生存邊緣的傳統農民來說,省吃儉用,進行投資卻不能多產多得,反而使自己進一步缺衣少食,是不理性的行為。
在舒爾茨發表於1964年的經典名作《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他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社會的關鍵不在於改造農民,而在於源源不斷地給落後國家的農民提供合適、較好、能使他們增產、增收的新技術;此洞見為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和農業政策帶來了革命性影響。
對於一位像我這樣以研究理論和政策問題為職志的年輕經濟學者來說,既然中國政府是理性的,那麼為何不願對1988年的通貨膨脹採取一般理論所主張的提高利率政策?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又讓我聯想到,為何中國已經進行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還要繼續給不少企業各種保護和補貼?往上追溯,為何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政府要採用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的各種市場扭曲?
深入考察和思索這一系列問題後,我豁然發現,這是因為許多大型國營企業的生存仰賴低利率貸款和其他人為扭曲所提供的隱性補貼。這些大型國營企業大多數是中國政府在1950年代推行「10年超英、15年趕美」的趕超戰略下的產物,具有資本密集的特點,技術比較先進。但是在50年代即使到80年代,中國還是個貧窮落後、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這些企業所需的產業不符合中國勞動力多、勞動力成本低、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國情,它們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生存能力。
如果1988年中國政府按照現代總體經濟學理論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膨,或者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府根據「華盛頓共識」採取休克療法,立即消除各種保護、扭曲,將會導致大量的國營企業破產,造成像後來出現於東歐和蘇聯轉型時那樣的大規模失業以及社會和政治動盪。這樣的結果顯然不利於中國的人民和中國的發展。
當時國內外經濟學術界有不少人根據那時的理論,抱持「計畫經濟不如市場經濟,雙軌經濟是最糟的經濟」的觀點。但是,中國政府卻推行雙軌制的轉型策略,一方面繼續給予傳統重工業部門的低效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開放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同時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成長。
蔡昉、李周和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闡述了這項論點,後來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專題》中也再次進行了論述。
1
思考中國政府治理1988年通貨膨脹政策的前因後果,啟發了我採取老子所主張的「如嬰兒之未孩」的「常無」心態來觀察世界各種事物。在考察問題、提出政策建議時,我不再直接根據現成的理論或者過去的經驗,而是每次都嘗試直接尋找經濟現象背後的行為人,分析他們要達到的目標、面臨的限制及可能的選擇,每次都從頭開始構造一個能夠說明問題來龍去脈的因果關係模型,就像我新近出版的《本體與常無:關於經濟學方法的對話》一書中所宣導的。
2
隨著中國經濟的奇蹟成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我跟著水漲船高,獲選為首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職責包括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的首席經濟顧問,領導世界銀行在發展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幫助開發中國家實現健全、快速、永續、包容性的成長,使全世界擺脫貧困。
儘管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全球經濟湧現出包括若干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多個成長極,但是非洲和其他地區的許多國家依然在低所得的泥沼中掙扎,未能縮小與先進經濟體的收入差距。在這波危機未爆發前,我認為自己在世界銀行的工作,面對的主要挑戰在於能否提出一個可行、有效、新的發展理論和政策架構,幫助那些貧窮國家改善發展績效。
任職後的第一週,我就訪問了南非、盧安達和衣索比亞,然而致力於促進貧窮國家發展經濟的原有計畫,很快就被雷曼兄弟的破產,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給打亂。總體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組成,但是現有的理論和諸多大師級總體經濟學家既未能預見這場危機到來,危機到來以後也未能對危機的程度和持久度做出準確判斷,提出解決問題、幫助世界擺脫危機的可行辦法。在國內工作時養成的「常無」心態,對我理解這場危機的本質、來龍去脈和出路大有幫助。
當我在2008年6月抵達華盛頓的時候,糧食和能源價格的飛漲占據了所有媒體的顯著版面,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我向同事提出:在通貨膨脹得到遏制後,接下來是否會發生通貨緊縮?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不以為然,因為他們相信「大穩定」的經驗和說法—從這波危機爆發前二十年的經驗可證明,歐美已開發國家的政府都已經能嫻熟地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成功緩和經濟的週期性波動—認為會發生通貨緊縮是無稽之談。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付通貨緊縮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雖然危機來勢洶洶,但是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二次大戰以後發生在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危機,短者3個季度,長者7個季度,危機就會過去,經濟就會復甦,這次危機也不會例外。
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理論,多數經濟學家主張政府只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給窮人和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支援,並依靠在危機中財政收入減少、社會開支增加所形成的財政赤字的「自動穩定機制」發揮作用就可以度過危機。
我則懷疑:由於全球經濟在危機前經歷了不尋常、靠投資拉動的長期榮景,創造不少產能,一旦危機爆發,各國失業率將提高,消費需求受到抑制,產能也必然過剩,尤其在已開發國家很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民間的投資意願會很低,缺少刺激需求的外在誘因,經濟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產能過剩、成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通貨緊縮惡性循環。
過去的危機一般只發生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政府可以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讓貨幣貶值、提高出口,靠外部需求的拉動走出危機。這次危機則同時發生在已開發國家間,問題從量變引起質變,各個已開發國家高失業率、產能過剩的問題不能靠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政策解決,如果沒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對策,這場危機將會曠日廢時,難以擺脫。
危機之初,我提議進行全球合作、反景氣循環、減少成長瓶頸的基礎建設投資,並將其命名為「超越凱恩斯主義」(BeyondKeynesianism),以啟動全球需求,消化全球過剩產能,恢復全球經濟的穩定和成長。當時多數經濟學家對各國政府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持保留態度,認為政府財政赤字的增加會增加民間未來稅負的預期,減少民間當前的消費意願,陷入政府債務迅速高築而總需求增加有限的「李嘉圖等價」困境,對全球合作的反景氣循環政策更是不以為然。
透過G20採取的協同刺激措施,全球經濟在2010年上半年出現了復甦的苗頭。據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秋季年會時提出建議,要求那些受危機困擾的國家緊縮財政、減少赤字,以恢復民間投資和消費的信心。我當時指出,這樣的政策可能導致經濟成長放緩、失業率增加,財政赤字反而激增,給經濟復甦蒙上一層新的陰影,進一步降低民間投資的意願。這一擔心不幸再次被證實。我當時提出財政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如何減少短期赤字,而在於提高政府財政支出的品質,使其在短期能夠創造需求、增加就業,在中長期提高生產力、經濟成長率和財政收入,實現中長期的財政平衡。這個觀點在2011年秋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導的主要政策方向。
如今,全球都在關注歐元區國家的債務危機。而我擔心的是,如果不採納我在危機爆發之初就提議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全球復甦計畫,化危為機,給發生危機的高所得國家提供結構改革的空間,全球經濟可能走向更為漫長的衰退「新常態」,甚至陷入多個「失落的十年」。我也高興地看到我這一主張在全球輿論和政策界獲得愈來愈多的贊同。
本書將闡述我對全球經濟危機根源的分析,指出可以引領全球走向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共贏策略和實現該策略預期的可能性,並提出避免同樣的危機再次發生的全球經濟新架構。自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尤其是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後,少數西方已開發國家雄踞全球霸主地位,在經濟、政治和理論思維上殖民於全世界。為了追求國家的現代化,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知識份子到已開發國家學習先進理論,但是根據西方主流理論制定發展或轉型政策的國家無一成功,發展或轉型成功的國家,其政策以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卻經常是離經叛道。
理論不管是社會科學的,還是自然科學的,都只是一套簡單、說明現象因果關係的邏輯。已開發國家的學者提出的理論,通常是根據自己社會的現狀來說明已開發國家的現象,或是以已開發國家的經驗為參照來看開發中國家的問題。
那樣的理論不能說沒有價值,但是,已開發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並非一成不變,舊理論經常被新理論否定,新理論又被更新的理論否定。例如,總體經濟學中,凱恩斯主義被理性預期學派所否定,理性預期又被後來的新古典綜合派及新凱恩斯理論所否定,開發中國家到底應該學習哪派理論?而且,開發中國家的條件經常不同於已開發國家,簡單照搬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
開發中國家的學者應該解放思想,包括自己傳統的和西方的思想,實事求是地根據自己國家的現狀,分析問題,了解背後的因果關係,自己獨立構建理論,這樣提出的理論可能和傳統的或西方的現有理論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努力進行這樣的創造性重構,才能發現問題本質,提出與時俱進、能推動國
家現代化、走向繁榮和長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這樣才算是科學,而不是理論教條。
在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的多極成長新格局中,開發中國家的學者不僅應該對本國的問題自己進行理論分析,而且應該根據自己的認識,對發生於全球,甚至已開發國家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理論見解和政策建議,這是開發中國家的學者面臨的機遇、挑戰和需要承擔的責任。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夠對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學者產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本書的原稿以英文寫成,英文版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世界銀行的同事Vandana Chandra、Jean-Jacques Dethier、Doerte Doemeland、Shahrokh Fardoust、Vivian Hon、Celestin Monga、Bruce Ross-Larson、David Rosenblatt、Volker Treichel、James
Trevino和王燕等人提供了許多協助;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簡體版則由余江翻譯,對上述諸人的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最後也感謝我的妻子陳雲英對我在世界銀行工作四年全心全意的支持。
林毅夫
2012 年8 月於北大朗潤園
結語
讓貨幣恢復秩序
唯有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及其可能的演變過程,才能不再重蹈覆轍。這次危機是起源於國際貨幣體系,也就是美國金融鬆綁與寬鬆貨幣政策使得流動性過剩,接著引發的財富效應,導致全球失衡。
然而,這種失衡的情況為何如此龐大,且歷時長久?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美國透過經常帳赤字與資本流出來創造其儲備。要預防金融危機再度發生,就必須建立更穩健的國際貨幣體系。本書提出以「紙黃金」做為新的全球儲備貨幣來建立這套體系。
經濟危機何時何地爆發,幾乎無人預料得到。雖然全球經常帳的失衡日趨擴大,但眾人依然對美國財政與政治體系有信心,對其金融規範有信心,相信這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及其堅若磐石的貨幣政策制度不會出問題。少有經濟學者對美國房市泡沫與全球失衡惡化、亂象叢生的狀況,表達嚴重關切。
不過,仍有人料到災難會降臨,他們擔憂的事果然在2008年9月爆發。G20國家通力合作,以挹注現金、債務擔保與其他形式的協助,砸10兆美元救市,讓全球經濟躲過衰退。然而,這次金融危機的起因仍眾說紛紜。
被綁架的金融政策
金融海嘯發生後,大家多把矛頭指向危機前全球失衡大幅攀升。但失衡的情形到底影響多大,經濟學家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認為這是主因,有人認為是催化劑。許多觀察者怪罪於東亞的出口導向政策、及這些國家在1998年金融風暴後累積外匯以自保,尤其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種觀念認為,全球經濟失衡與外匯儲備過剩,導致美國借貸成本便宜與房市泡沫。
但另一項說法則指出,其實美國流動性過剩及其原因,才是造成金融危機的禍首。美國金融鬆綁,讓財務槓桿更高,再加上低利率,於是大幅推升流動性,房市泡沫也愈吹愈大。家庭消費攀升,更推動了房市泡沫的財富效應及新金融工具。由於消費攀升,加上投入伊拉克及阿富汗戰事造成的財政赤字,讓美國產生龐大的貿易逆差與全球失衡。美國能在這麼嚴重的失衡情況下撐這麼久,完全是仰賴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流動性過剩,也導致流出到其他國家的資本總額極高,如此也助長投資與股市榮景。各國將貿易順差與資本流入所賺得的美元轉換為本國貨幣,並由各國央行做為外匯儲備。這些儲備之後又流回美國,投資美國國債與金融市場,讓人認為低利率背後是外匯過剩的非儲備貨幣國。當美國房市泡沫化、金融體系崩潰,便引發了全球危機。
同時,金融鬆綁與自由化也橫掃歐洲。歐洲大型銀行在東歐與南歐設立分行,運用高槓桿來支撐房市泡沫與消費支出。歐元擴張讓歐洲各國間的失衡惡化。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各國政府的盈餘增加,因此尚能控制其財政狀況,但在衰退時卻難以為繼,導致2010年以希臘為首的歐債風暴爆發。
金融鬆綁與自由化風潮主要是許多領導人深受金融界牽制,於是大力推動,而金融界的新工具叢生,更造成重要金融機構崩潰之後引發連鎖效應,衝擊全球經濟,許多國家產出中斷的情形至今仍尚未復原。
早在2003年,高所得國家的學者與決策者已指責過中國造成全球失衡惡化,雖然中國一直到2005年,才開始累積大量的順差。其實中國龐大的經常帳盈餘主要是反映國內的高儲蓄率。如果能提早理解,並處理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則可逆轉危機,至少能降低衝擊。
結構性改革是唯一解方
然而,各國該如何恢復經濟成長,預防另一次危機?答案還是老話一句:進行結構性改革。若缺乏結構性改革來強化競爭力,那麼債務纏身的南歐國家將一再要求愈來愈大的紓困方案。
如果日本與美國不進行結構性改革,勢必繼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維持低利率以支撐其金融體系,協助負債家庭,並降低舉債成本。如此可能造成的後果是,這些經濟體全將長期陷入成長遲緩、高風險、金融投資報酬低的「新常態」。低利率也會鼓勵短期投機性的資金流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導致物價波動)與新興經濟體(造成資產泡沫、貨幣升值及宏觀經濟調控困難)。
問題是,結構性改革會造成短期的經濟萎縮,在許多失業率屢屢攀高的國家將面臨政治上的阻礙。在這些國家,公私債務重整與財政整頓並非第一要務。高所得國家反而要刺激需求,以創造空間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這表示,反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須著重在能立即創造就業機會、提升未來生產力的計畫,特別是透過投資於基礎建設、綠色產業與教育來達成。但是,提升生產力的投資機會在先進經濟體往往有限,且不足以將國家拉出經濟泥淖。然而,在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的投資機會豐富,也能為高所得國家的出口帶來需求。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儲備貨幣發行國及儲備貨幣充足的持有國。在今天全球經濟態勢中,基礎建設項目對民間資金(含退休基金)及主權基金來說,是很好的投資標的。多邊開發銀行與政府可透過創新安排,讓基礎建設案件的投資更能吸引民間投資者,發揮民間資金的優勢。
要讓全球在開發中國家推動基礎建設的投資,唯有這些國家未來數十年能蓬勃成長才可行。但今天全球經濟態勢尚不明朗,這些國家是否有成長空間?如果有,又該如何把握契機?
發揮後進者的潛在優勢
二次大戰後,政府結構式的干預普遍失敗,致使「挑選贏家」的政策不受青睞,因為那種政策無法延續、扭曲社會成本,並引發尋租行為、停滯,及危機反覆發生。目前普遍認為,民間部門較能看出新興產業,但許多文獻無法分辨出哪些政策與經濟體的比較優勢無關,哪些政策卻能發揮比較優勢。前一類政策通常會失敗,而後者多半能成功。
「新結構經濟」著重於開發中國家的固有優勢,及這些國家可以發揮哪些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取決於固有優勢),進而推動大幅度的結構改變。對於低所得國家來說,要在全球化的世界讓經濟轉型的機會很多。如果國家注重比較優勢,發揮後進者的潛在優勢發展新科技,則可在數十年之內快速成長,促成經濟體轉型,經過一、兩個世代,即可躍升為中所得,或甚至高所得國家。
中國擁有8,500萬個勞力密集度高的製造業就業機會,然而,未來幾年將攀登產業階梯,從低技能、低薪資的產業,爬升到資本與技術密集度更高的產業。如此將釋出龐大的就業機會給低所得國家,為其提供工業化的動能。
若低所得國家的政府能遵循新結構經濟的建議,依據國家的比較優勢,實行扶植民間企業的政策,承接開發中國家領頭龍(如中國)所釋出的潛能,則可望每年成長8%以上達數十年。這種大幅度的轉型需要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以突破成長瓶頸。這些政策可將全球危機轉化為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雙贏機會,為當前創造就業,並推升日後的生產力。
金融危機突顯出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大缺失。雖然這體系熬過了最初的衝擊,但仍相當脆弱,完全復原遙遙無期。
紙黃金的繁榮時代
二次大戰之後,大蕭條的記憶猶新,於是先進經濟體的決策者設立新制度,監督國際貿易。這些制度稱為「布列敦森林體系」,目的是促進國際貿易與金融的成長與穩定性。接下來將近二十年的期間,這套體系靠著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標準來運作。
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期,這套黃金標準崩潰,全球經濟治理進入了「善意忽視」的階段。
現在各國遵循自己的貨幣與匯率政策,美元也成為最重要的國際準備貨幣。這種體系促使資金流動與匯率高度浮動,也造成龐大而持久的收支失衡與匯率失調,並缺乏充分的全球調整機制。相對的,需要一套國際貨幣體系,讓各國處理經常帳暫時的盈餘與赤字,並累積淨債權(這項任務當前的體系達成了)同時創造誘因,促使各國回歸平衡。無法達到平衡是目前貨幣體系最大的缺失。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全球正朝向國際貨幣體系的方向前進,有許多種貨幣在國際貿易與儲備上爭相成為儲備貨幣。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究竟會比目前的體系穩定或混亂?有些經濟學家相信,主要儲備貨幣之間的競爭,是一種約束機制。若某儲備貨幣國採取只符合國內利益的貨幣政策,但從全球角度來看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持有儲備貨幣的國家將轉換成其他儲備貨幣,「犯規」的貨幣就會失去儲備貨幣的優勢。
若所有的主要儲備貨幣國有強勁健全的經濟,這個論點就能成立。但多數潛在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有某種無法預測的結構性弱點,一旦暴露之後,將引發短期資金的出走潮,導致其他儲備貨幣急遽升值。升值讓實體經濟疲軟,並使結構上的瑕疵更惡化。若下一個儲備貨幣出現明顯弱點,則短期資金又可能會出走。因此,多種儲備貨幣體系可能比目前的更不穩定,對儲備貨幣國與非儲備貨幣國而言都沒有好處。
本書所提出的方式能走出這個僵局,雙方國家都能從中獲益。書中提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紙黃金」取代目前儲備貨幣「沒有制度的制度」。若各國同意讓國際貨幣機構發行一種超國家的儲備貨幣,全球經濟就有機會恢復穩定,解決存在儲備貨幣中的國內與國
際利益衝突。各國央行將持有紙黃金來做為儲備貨幣,並依據固定兌換率發行國內貨幣。紙黃金可藉由收取全球鑄幣稅而逐年增加,供國際貨幣機構當做營運費用,開發機構也能以此資助公共財。紙黃金系統可避免以黃金為準則的重大侷限(無法擴充,以滿足不斷成長的全球經濟需求),也可避免以某國貨幣做為儲備貨幣的缺失(國內與國際固有的利益衝突)。這能讓各國貨幣機構更有紀律,同時允許必要之時讓該國貨幣貶值。現在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適當時機,應該好好把握,以免新的危機再對目前體系使出致命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