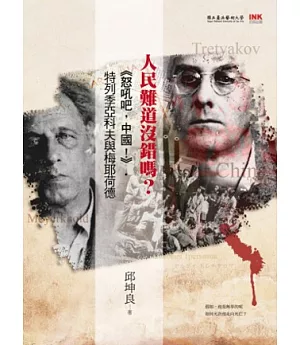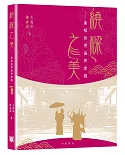自序
一九三九年秋冬間,因反對納粹政權而流亡國外的德國劇作家,詩人布萊希特(1898-1956)聽到摯友蘇俄作家特列季亞科夫(1892-1939)經由人民法庭審判,於秋天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內被槍決時,悲憤之下,寫下一首詩。
藉由這首名為〈人民難道沒錯嗎?〉(Ist das Volk unfehlbar)的詩,布萊希特表達他的無奈與感慨,並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人民思考:「假如,他是無辜的呢?」布萊希特的詩說:真正的罪犯手上拿著無罪的證明,無辜之人卻苦無證據證明自己無罪;這首詩的最後一段,他更語重心長地控訴「人民」:為何沒有人為特列季亞科夫辯護,為何容忍一位無辜者受害,「允許他走向死亡?」
布萊希特詩作中有四首直指「人民」,除了悼念特列季亞科夫的〈人民難道沒錯嗎?〉,當特列季亞科夫的同志,來自高加索、曾寫過《革命滑稽劇》、《臭蟲》、《澡堂》等劇的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二○年代後期,被領導階層視為麻煩人物,導致孤立無援,終於一九三○年舉槍結束生命,這位俄羅斯未來派詩人的悲劇,也讓布萊希特耿耿於懷,創作了簡潔有力的詩作〈馬雅可夫斯基墓誌銘〉。這首四行詩言簡意賅,道出勇敢機智的馬雅可夫斯基即使有智慧逃脫鯊魚的追逐、有能力獵殺強壯的老虎,在面對看似不起眼的「臭蟲」,卻呈現出被吞蝕殆盡的無力感;「人民」在面對政府機器時之絕望心情表露無遺。
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從帝制、共和到納粹集權,曾經是俄國以外的歐洲各國中,革命勢力最熾熱的國家,左翼勢力屢仆屢起,戰後東西冷戰,兩德對峙,局勢變化,詭異多端。作為一名左翼作家、共產主義信徒的布萊希特,對「人民」感受必然極為深刻,甚至有切膚之痛。布萊希特在戰後冷戰時期的兩首對「人民」有感的詩作,一首寫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德國歷史上的「人民起義」(或工人暴動)時,布萊希特關於這個事件的態度與「人民」觀點反映在〈解決之道〉中。〈解決之道〉有名的結束句更極盡嘲諷之能事:面對不滿的「人民」,政府的解決之道就是「解散人民」,「挑選另一群?」短短幾個字令人拍案驚奇!
與這一首詩作約略同時完成的〈人民的麵包〉,詩中除了突顯「人民」的精神食糧──「正義」的重要性,更區分優質與劣質正義麵包的差異。布萊希特最後強調,優質的正義麵包必須符合「人民」的需求,所以「正義麵包必須由人民來烘焙」,它也必定是「豐富的,健康的,天天的」。古今中外,人民始終是知識份子理念的根源。縱然知識份子對人民懷抱無上期許,希望他們「明天會更好」,但歷史證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事件履見不鮮。布萊希特極為推崇特列季亞科夫,以及他編劇的《怒吼吧,中國!》,甚至視他為良師,對特列季亞科夫而言,布萊希特可謂他一輩子難得的知音。
二十世紀的俄國,到處都標記著「人民」,中央人民委員會、人民法庭等以「人民」為名的政府機構林林總總。俄國人如此熱衷「人民」一詞──應該就是從俄國知識份子開始的罷!豈止俄國言必稱人民,布爾什維克推動的革命影響東西方,「人民」這個名詞廣泛流布,中共革命史就一直把「人民」與「黨」掛在一起,建國成功後,「人民」為名的機關、組織……不勝枚舉,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等等到處都有人民。政客逐鹿天下常強調所作所為皆為「人民」,要給人民過太平幸福的生活,即使革命或反革命也是打著「弔民伐罪、解民倒懸」的旗號。
「人民」兩字如此具有檄文、符咒意象,是經過政治人物、知識份子不斷的定義、詮釋,賦予其正當性與神聖性。政客把人民放在口中,吐進吐出,知識分子則藉作品表達對人民的關愛,歷史愈悠久的民族、國家,「人民」口號史的流傳就愈久遠。雖然人類「民為上」的概念源遠流長,俄國的「人民」與「知識份子」的關係確是「以人民之名」議題中,最值得討論的部分。
俄羅斯社會的中堅份子──知識份子──對於飽受極權摧殘的人民,向來持兩面態度:一方面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猛力批判。普希金以《上尉的女兒》表明對農民起義首腦普加喬夫的理解與認同,但他在〈詩人與群眾〉一詩中,卻以尖銳的負面字眼形容群眾:「愚痴的蟲子」、「不會思考的人民」、「奴隸」,表現他對於人民的負面態度。詩人萊蒙托夫也曾在〈再會了,未曾沐浴的俄羅斯!……〉一詩中,稱祖國為「奴隸的國度、老爺的國度」,視人民所受苦楚為其自身的奴性使然:「身穿藍色制服的官老爺,還有你,服膺他們的人民」。
象徵主義詩人、俄國哲學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這個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俄國知識份子的力量不在於理智,而在於情感與良心。其情感與良心基本上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理智卻經常迷路。」 這句話為一切為人民的知識份子作了鮮活的註腳。
特列季亞科夫被處死的罪名是「日本間諜」,對於年輕時代曾經在蘇俄遠東地區反抗入侵日本軍的詩人、劇作家來說,毋寧是十分諷刺的。特列季亞科夫冤死,是一九三○年代史達林大清洗(Graet
Purge)下,眾多亡魂之一,與他命運相同的,還包括當時最有名的左派戲劇家,對前衛劇場產生重大影響的梅耶荷德。他們都是俄國十月革命後,最積極投入人民革命行列的狂熱份子,兩人最重要的合作,是一齣以中國人民為背景的《怒吼吧,中國!》,這是特列季亞科夫根據一九二四年六一九萬縣事件創作劇本,這齣戲明顯的反帝國主義,為無產階級發聲。最後劇作家、導演都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犧牲,而當權者處死他們,想必也是為了人民,至少人民允許當權者這麼做!
《怒吼吧,中國!》是一九二○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宣傳鼓動戲劇或革命劇場,於一九二六年元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梅耶荷德劇院首演,曾經在國際廣泛流傳。從事件發生、劇作家創作到首演,戲劇搬演的中國──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或國民政府正處於風雨飄搖、內憂外患交逼的時刻,外有列強瓜分勢力範圍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內則軍閥割據、民生困苦。以萬縣所屬的四川而言,其軍閥混戰時期之長、次數之多以及為禍之烈,堪稱全國之最,單從辛亥革命至一九三三年劉湘、劉文輝之戰結束,四川盆地二十多年間,平均每半個月就有一次戰爭,各軍防區所預徵之田賦竟達四、五十年(灌縣甚至預徵至一九九五年)。
特列季亞科夫《怒吼吧,中國!》要求「怒吼」的「中國」應該是中國人,而不是中國政府。而一九二○至四○年代的中國,面對帝國主義或殖民統治者的壓迫,高喊「怒吼吧,中國!」,的確可能讓人血脈噴張,當時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或弱小民族,都可運用《怒吼吧,中國!》傳達他們被壓迫的聲音,而「怒吼吧,╳╳!」這個語詞結構,換個國家、地名,也能達到宣傳鼓動的效果。當時的中國就常有人把這句話作為標題,運用到版畫、詩歌或地方文藝。特列季亞科夫創作劇本之前,就已發表一首同樣以《怒吼吧,中國!》為名的詩歌。
那個年代的中國戲劇家不清楚六一九萬縣事件,也不知道這齣戲已經在莫斯科隆重上演,還是日本築地小劇場與新築地在東京等地公演之後,中國藝文界才知道這齣戲,對此田漢感嘆在土耳其壓迫下的希臘人不自哀而拜倫哀之,在國際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人沒有出息,特列季雅科夫乃為寫《怒吼吧,中國!》至於這齣戲先響應的,不在被壓迫者的中國而是壓迫者的日本,田漢是用這樣的觀點:「哦,對呀,日本也有被壓迫者呀!」。
今日生活在台灣的人──無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或戰後來台,包括國共戰爭中隨著國民政府撤退的中國人,以及他們半世紀在島嶼繁衍的家族,對於《怒吼吧,中國!》的來龍去脈未必清楚,卻很少會對「怒吼吧,中國!」這幾個字沒有感覺,它讓人充滿各種視覺畫面與情緒想像。台灣人如果知道《怒吼吧,中國!》這齣戲,多半來自楊逵。楊逵在一九四三年太平洋戰爭打得火熱的時候,與台中藝能奉公會同仁推出這齣戲,與一九三三年左翼劇團──上海戲劇協社的演出,屬性完全不同。台灣演出《怒吼吧,中國!》有那個時代的背景,當時的文宣都著重藉劇中英美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罪行,鼓舞民眾,打倒英美,也等於把對日本殖民者的怨氣轉移(或擴大)到西方帝國主義。楊逵演出的劇本來自日本作家竹內好的日譯本,而竹內好是從南京劇藝社周雨人的改編本翻譯,周版《怒吼吧,中國!》又源自上海反英美協會蕭憐萍的《江舟泣血記》。
楊逵的《怒吼吧,中國!》除了留下劇本,其他資料(如導演手記、舞台圖像、劇照)甚少,但由於他本人長期反抗殖民統治,為工農階級發聲的作家性格,是日本時代台灣人的象徵,戰後也一直是藝文作家仰慕的對象。楊逵這齣從頭至尾吶喊東亞人聯合起來打倒英美的宣傳劇,常被兩岸民族主義者解讀為帶有抗日色彩的戲劇,很少人相信楊逵會「屈從」日本殖民政府演戲反英美,除非他有一定目的──例如藉戲劇反諷日本帝國主義?
《怒吼吧,中國!》牽扯的文化層面極為寬闊,也扮演宣揚社會理念與政治批判的角色,然而,《怒吼吧,中國!》不只是一齣戲,更是一群人的集體表演活動,作戲劇的也是人,也往往有七情六慾,以及趨炎附勢的人性弱點,義無反顧的戲劇家做義無反顧的戲劇,在威權的時代,並非絕無僅有,但是他們的下場經常淒慘,以至戲劇極少能站在時代前端批判政治或引導思潮,反倒是常被政治所操控。近百年來的台灣與中國,瞬息萬變,回頭談論與「怒吼吧,中國!」有關的議題,有今夕何夕的感覺,尤其面對崛起的中國,對中華民國國民或台灣人來說,光是《怒吼吧,中國!》的劇名就充滿複雜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