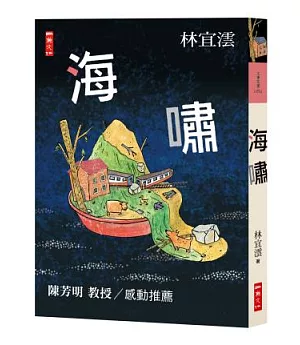推薦序
權力與暴力--讀林宜澐《海嘯》
後山的命名,林宜澐認為這是臺灣版的東方主義。小小臺灣可以分成前山與後山,其實是早期漢人移民的地理觀點;因為前山的拓墾較為發達,而後山在整個清朝時代仍停留在混沌不明狀態。花東地區一旦被劃入後山,似乎是意味著文化落後的象徵。就像歐洲人的世界觀,把地球劃分為東方與西方,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暗示文明與野蠻的分野。林宜澐的調侃,當然是對這種前後之分的觀點表達不屑。
他的小說,足夠證明後山文學毫不遜於前山。至少對他而言,所謂人性,無分東西南北。無論是臺北觀點,或西部觀點,都不足以解釋完整的臺灣。來自花蓮的作家,常常對文明發達的臺北嘲弄並奚落。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王禎和短篇小說〈小林來臺北〉,以及長篇小說《美人圖》與《玫瑰玫瑰我愛你》。站在花蓮,瞭望臺北,可以清楚看見許多滑稽突梯的故事不斷發生。論者恆謂,林宜澐的文字裡滲透著王禎和的影子,如果從人性挖掘的角度來看,或許言之成理。但是最大的不同,在於林宜澐總是聚焦花蓮小城所浮現的人情世故。
長於營造短篇小說的林宜澐,此書開始嘗試把筆尖觸探到長篇格局,到目前為止他已完成六部作品,包括《人人愛讀喜劇》、《藍色玫瑰》、《惡魚》、《夏日鋼琴》、《耳朵游泳》、《晾著》。他擅長站在疏離的角度,冷眼觀察人間。而所謂人間,大部分都是以花蓮為中心。他筆下的花蓮人,其實就是臺灣人。而事實上,花蓮小城的空間正是整個臺灣的縮影。在那裡有豐富的族群文化,也有精采的自然景觀,凡是小小海島承受的各種氣候變化,以及流傳的各種語言腔調,都能夠在花蓮獲得見證。
如果後山的「後」,可以解讀為後結構的「後」,花蓮的文化特質便彰顯出來。在西部平原流行的漢人沙文主義,在花蓮平原簡直就行不通。因為在那裡,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的文化可以平起平坐。花蓮的文化主體,絕對不可能由特定族群所構成,而是由具備文化差異的四大族群共同建構起來。相對於北部或西部,後山文化充分表現出後結構主義的精神。具體而言,所有族群文化的差異性,都得到尊重。縱然微微流動著意識形態的緊張關係,卻不可能出現霸凌的霸權文化。林宜澐的小說,正是後山立場與後結構思考的混融產物。
從鄉土文學的系譜來看,林宜澐確實在風格上繼承了王禎和,而且還更發揚光大。一九七○年代以來,王禎和與黃春明往往是公認的鄉土書寫的健將。他們兩個都不樂於被劃入鄉土文學陣營,尤其鄉土文學運動變得更加浮濫之後。他們都寫小人物,但是出發點並不相同。黃春明喜歡寫世間的人情冷暖,王禎和則善於寫社會的人性明暗。前者對小人物帶著一定程度的寬容,後者對小人物則常常表達嘲弄。許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王禎和對小人物充滿譏刺,如果仔細觀察,當可理解他主要在於揭露人性的真實。這個社會常常以身分、名位的表象來判準人格,如果卸掉他們的外衣、面具、榮譽,就是赤裸裸的小人物。在這點上,林宜澐也總是穿透被遮蔽的表象,而直接進入凡人內心的真實世界。在隱密的底層,可以看見自私、邪惡的幽暗人性。
撰寫《海嘯》這部小說,似乎就是他文學作品的集大成。林宜澐偏愛使用全景觀點,來掌握故事中的人物。對於芸芸眾生中的小人物,總是貼身描寫愛恨交織的情感。尋常無奇的日常生活中,似乎每個人都維持著合理軌跡,也保持著相互默契的人際關係。但是,當災難降臨時,被壓抑在內心底層的人性,忽然一夜之間全部裸裎出來。這樣的災難,可能是戰爭,可能是風災,或者是地震與海嘯。當一個碩大無朋的暴力逼近時,人與人之間的暴力也會被開發出來。花蓮這濱海的小城,突然受到劇烈地震的襲擊,殘酷人性於焉徹底釋出無窮的能量。
《海嘯》的故事,始於一場地震的衝擊。這種大自然的暴力,維持公平的伎倆,剎那間極其均勻地讓災害落在每個人的身上。這種公平,想必出於上帝寬大的手,非常人所能及。因為是公平,所以必須訴諸於全景式的描寫。大難來時,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細膩牽扯著,無分官民,無分男女,無分貴賤,都捲入了人間地獄。每位受難者,未受地震檢驗之前,其實都各自擁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偷情男女的故事,黑白兩道的糾葛,知識分子的自私,都伴隨著地震的降臨而揭露。這部小說似乎在暗示,人間的善良與醜惡長期就維持著一種平衡生態。社會能夠正常運作,就在於使這種文化生態持續運作。在更大的破壞力量到來之前,人們只看到一個溫良恭儉讓的社會。
地震驟然搖撼著每顆靈魂,卻也有麻木不仁者。如耽溺於棒球的阿鼻仙,沉醉在巴哈音樂的陳新老師,以及關心創作的詩人莫君;他們情有所鍾,所以對大災難無動於衷。整個故事的主軸人物是馬納,一位新聞記者,對於地震慘況瞭若指掌。不僅見證他的姊姊與情夫被壓死於屋下,也看到整個城市全盤毀滅。他成為市長的精神支柱,也動員黑道幫派出來維持秩序。在小說裡,馬納扮演著攝取全景的鏡頭,凡是故事的重要關鍵,都完全被他捕捉。因為他掌握全局,能夠洞燭最黑暗、最私密的角落。
故事精彩處,微妙地出現在市長與黑道之間的權力鬥爭。當行政體系陷入癱瘓之際,救災工作便落在紀律嚴明的地方角頭大樹手上。大樹展現他領導的手腕,救人之餘,還維持地方秩序。比起神經衰弱的市長還更具魄力,名聲一夜之間就凌駕市長之上。就像臺灣社會所有的政治脾性,一旦出名,便馬上聯想到選舉。短短兩天的地震後,大樹已經開始規畫下任市長的選舉,並且也儼然威脅到現任市長。這種救災政治學,似乎也在臺灣各個鄉鎮屢見不鮮。
林宜澐構思小說時最高明之處,便是謠傳著一個巨大海嘯即將襲來。海嘯彷彿在蓄積能量,伺機要吞噬這海邊城市。它變成了小說中的極大張力,人性的考驗也相對更加嚴酷。累積數天的謠言,果真另有一場規模龐大的海嘯正要席捲而來。處在欲來未來的過程中,一股逃亡潮也漸漸形塑而成。林宜澐在小說末端並未揭開謎底,便足以道盡人間的爾虞我詐。這樣的結局,近乎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的終結。但是,海嘯的毀滅力量,較諸美軍即將登岸尋歡,還更令人動容。王禎和的小說點出「美軍就是美金」的誘惑,而林宜澐卻製造海嘯疑雲,以毀滅取代誘惑。
在四年級的作家群中,已有不少人逐漸減產,或甚至近乎封筆。林宜澐則相當入戲,上臺之後,便再也沒有下臺的打算。他不是多產的作家,卻是長期穩定生產。《海嘯》的完成,證明他對臺灣社會的觀察,始終保持銳利的眼睛。暴力陰影與權力誘惑,一直在島上徘徊不去,折磨著每個世代的人文心靈。小說不可能是靜態的存在,林宜澐未嘗須臾放下手術刀,時時都準備對脆弱的社會體質進行解剖。這部小說是一則寓言,真正的海嘯不是來自大自然,而是釀造在貪婪的人。這部小說也是一個預言,林宜澐將源源不絕寫出卓越的作品,當他的觀察力與批判力仍然高漲。
陳芳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