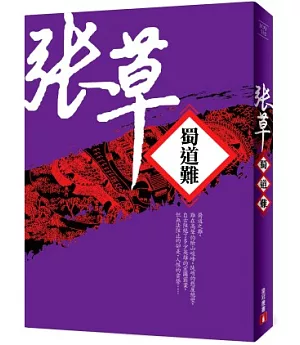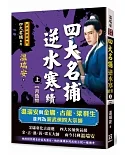推薦文
茅山道術的成都會戰文◎張國立
我父親來自江蘇省金壇縣(如今是市),母親則是鄰縣的句容市,聽老媽說起以前談戀愛的故事,老爸得翻過橫亙在兩縣中間的一座山才能約會。
嗯,有點勞累。
中央的那座山就叫茅山。
父親早逝,做兒子的我偏又是好奇寶寶,成天問老媽關於老爸的事,最常出現的問題是:
「把拔以前是做什麼的?」
「中央造幣廠呀,文書科的。」
「再之前呢?」
「中央銀行。」
「再之前呢?」
「念書。」老媽開始煩了。
「再之前呢?」
這時老媽放下手中的毛線,朝我瞪圓兩顆大眼珠,用威嚇的口吻吼我:
「當道士。」
厚厚厚,我爸是,師公?
事情是這樣的,我爸的家鄉在金壇茅山腳下的一個小村子,按照幾百年來的傳統,十多歲時的男生都得上山服義務役,當道士。想想看,老爸是師公,能填在家庭連絡簿內表揚一番嗎?
直到高中我終於搞清楚,茅山是道教的聖地之一,而且茅山最厲害的是降魔抓鬼的道術,名聞兩岸三地的電影界。於是問老媽的問題就有了變化:
「老爸以前是茅山道士喔。」
「小道士,當了兩三年。」
「他會不會道術?」
「什麼道術?」
「就是驅鬼降魔,什麼灑豆成兵,把死人從棺材裡叫出來之類的。」
「亂七八糟,你爸只會念書寫字。」
「真的,書上說的,電影裡也有演,茅山道士一手拿木劍,一手搖鈴,嘴裡念咒語,鬼就現身和他比武功,大部分都是道士贏。」
「在茅山混了這麼久,你爸也許會法術吧。」
好極了,說不定老爸留給我什麼《茅山法術一百種》、《降鬼十八招》之類的世不二出寶典,然後我苦練三個月,就成了當代頭號法師,不必考什麼屁大學,受盡數學的煎熬。甚至我給自己起了個法號:張一刀。
「你爸可能會抓鬼。」
老媽總算有記憶了,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生了你這個討債鬼。」
大約幾年前我還回江蘇老家去看茅山,它在群山之中,要下雨的樣子,只見雲霧飄渺,瑞氣千條,也見到穿道服的道士,不過老道士抓著我說:
「來,算個命,一條命二十人民幣。」
這不影響我對茅山道術的憧憬,一直想寫本以茅山道術為背景的小說,不過一時陷入推理旋渦之中不可自拔,一延再延,現在不必延了,因為張草的《蜀道難》寫了,而且寫得很武俠,將道術與武術結合在一起,面對張獻忠入侵成都的這場世紀大戰。
明末的流寇裡面,李自成最英雄,張獻忠則最殘酷,殺人如麻,《明史》裡明確指出他以殺人多寡做為記功的標準,他的部隊一共殺了「六萬萬有奇」,就是六億多人,顯然過於誇張,但至少殺了幾百萬。其中記錄最詳細的是他攻進朱元璋的故鄉鳳陽(如今江蘇北部與安徽接壤處),《明史》裡說:
「士民被殺者數萬,刨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千六百五十餘間。」
殘忍至極。
張草筆下,三名道士雖全無武功,卻憑著道術與張獻忠派進四川的間諜部隊展開搏血戰。這個安排使故事由奇幻,更加血淋淋的真實。
我沒寫成茅山道術沒關係,張草寫得精采,於此再得強調一下,我,張某,真的是茅山張小道士的兒子,在此推薦《蜀道難》,絕對貨真價實。
前言
蜀道果然難行
上一部作品《庖人誌》費時九年方成,當出版社知道尚有續集時,他們也不禁頭皮發麻了:讀者等得了這麼久嗎?我不太擔心,因為《蜀道難》是從前作衍生出來的故事,應該可以寫得比以往快一些,因為手頭上都已經備足了資料,乍看沒什麼難處。這部作品是我在寫〈弈士誌〉時,發現筆下一發不可收拾,趕緊懸崖勒馬,將一大塊寫好的部分切去一旁,打算另開一條線,好讓《庖人誌》的主線更加明顯。其實兩部小說在時空和人物上皆相連,甚至重疊,所以我相信可以在一年內整理出來。
無奈事與願違,我碰上了最大的難題,亦即貫穿故事最重要的人物:張獻忠。我應該寫多少張獻忠,才不至於變成一部《張獻忠傳》?我應該在交待一件歷史事件時,如何避免將來龍去脈寫成教科書?張獻忠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他一定跟普通人一般有複雜的個性,而歷史中有關他的行為紀錄有多少真實性?如何分辨?如何才能找到最接近他原貌的文獻?
我對「張獻忠屠川」,乃至於後來滿清人「湖廣填四川」一直有高度興趣,張獻忠真的殺光了四川人嗎?在十年研究中,我漸漸看出歷史紀錄有趣的一面:隱藏在文字表面底下的「第三種歷史」(「滅亡三部曲」語),那是一種隱藏的訊息。比如有一段野史文字紀錄說,張獻忠自謂「其實我一生最大的願望是當個商人」,這句自白說明了什麼?透露了他多少心事?我不敢說發現了真相,但真相的確可以從不同文獻的矛盾衝突中浮現。即使是今日的新聞事件,都可以出現羅生門式的各說各話,所以我們又如何強求這些久遠的舊聞,有辦法完全還原真相?官方歷史不免為政治喉舌,但草民自有草民的觀點,因此民間野史多少道出了庶民角度的歷史(當然,也可能只是未經證實的八卦)。
寫這故事時,不免引發我的思緒:當天下大亂,前朝已滅,後朝未穩,國不成國,家不成家的時刻,試問該如何選擇效忠對象?忠義該如何定義? 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由個人至天下逐步擴大,此刻該選擇何者為重?自身、家園、國家或更大的,天下?
當然,各人有各人的選擇,有人選擇為已亡的國家盡忠,被評為愚忠,我看也沒什麼不對,畢竟這是他個人的抉擇,因為惟有如此方能令他的觀值觀臻於完美。但若我們不再立足於政治中心的高度來看待家國,除去忠義的包袱後,以低姿態站在民間環顧四方,看見的會是個人的掙扎求生,還有為大節的捨生取義,此時的義,不為自我而為他人,才是人性的最大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