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劉瑞琪
肖像是謎樣的視覺文化論域,吸引了無數學者欲語還休的思辯與絮語。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探討(自)畫像的《盲人回憶》(1990)這本圖錄,別出心裁地選取盲眼及哭泣為主題,以解構西方以目睹為主的哲學與文化。他強調,其實所有西方的(自我)畫像,盲目是主要的關懷,甚至使其可能的狀況。因為,當畫家在繪畫之時,他就無法注視描繪對象,因此繪畫必須由記憶媒介,而這種媒介的過程是盲目的,所以在某些意味上(自我)再現的根本可說是廢墟:「一開始就是廢墟,廢墟是從開始觀看那刻起,就發生在意象上的。」
對於德希達來說,(自)畫像的神祕難解在於該如何解讀人類面目與身體的廢墟?
這本書呈現近十五年探索近代肖像謎題的重要成果,匯集了中文世界研究從十七世紀迄今西方、台灣、中國肖像的重要論文。本書依照主題編排,分為五個主題,每個主題收錄兩、三篇研究論文,展現新近肖像研究的多元切入角度與方法。本書的五個主題並非各自獨立存在,而是彼此交織與補充,形成豐富的論述網絡。每個主題之下的論文,並非展現針鋒相對的觀點,而是緣起於類同關懷而開拓了相互對照的切磋空間。整體而言,這十一篇論文所探討的肖像論域,彼此相輔相成、穿梭融涉,開展了參差對照、多元開放的對話與論辯空間。
筆者在此嘗試從肖像的符號學出發,說明編排這十一篇論文的思路。從皮爾斯(Charles S. Pierce)的符號學理論來看,肖像由於展現與(曾經)活著的某人面貌上的相似性,所以是一種呈現符號和其對象在某方面相似性的「肖似性符號」(icon), 當代探討肖像的專書亦一再提及肖像這個核心定義。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號學系統,則可以進一步釐清做為「肖似性符號」的肖像,在表現形似與神似之間的差異。索緒爾提出,符號是符徵(signifier)與符旨(signified)的結合所構成,符徵為符號的物質形式,符旨為符徵在心靈所喚起的意象或概念。另外,指涉物(referent)則為符徵在真實世界所指涉的對象。符徵與符旨之間的關係原為武斷與約定俗成的,在傳統模仿(mimesis)觀的運作底下,形似來自於觀者感覺肖像符徵肖似其所指涉的模特兒之時,神似則出自肖像符徵在觀者心靈喚起了模特兒內在本質的意象。
以西方近代時期的肖像而論,符徵、符旨與指涉物之間,可以在表意過程(signification)產生緊密一致的關係,但是從十九世紀中葉的印象派開始,現代肖像在走向抽象的過程,逐漸脫離傳統肖像的模仿觀,愈來愈不肖似模特兒,與符旨也逐漸失去對應關係。從逐漸進入後現代的1960年代末期開始,肖像的符徵不僅在現實世界中沒有指涉的對象,而且與符旨完全斷裂,成為自由流動的符徵,使得意義不斷在從符徵轉移到下一個符徵的運動中暫時浮現、流轉不止,而演變成後現代的擬像(simulacrum)。
義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在1917年曾經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這句名言深刻地指出歷史分析是一種古今的對話,當代的狀況與需要會影響史家對過往歷史的詮釋。本書以「面對女性主體」為第一個主題,正是本著對近代數百年肖像歷史的探析,必須立足於當代關懷的學術立場。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歷經學生運動、女性主義運動、黑人人權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反越戰等等的洗禮,歐美的社會與文化發生從現代性邁入後現代性的巨大的轉變。各種後現代的邊緣團體湧現,一反現代時期凸顯普遍化的男性主體,開始以尊重差異與多元為訴求,群起發動各類爭取權力與主體性的社會運動。其中,當代女性主義理論與藝術實踐在探討差異政治方面,有極為深刻的劃時代表現。在「面對女性主體」這個主題,本書收錄了兩篇援引當代女性主義
/ 後結構論述來解讀女性主義肖像的論文。劉瑞琪的論文奠基於肖像呈現「面貌的相似性」的觀點出發,張靄珠的論文卻解構了肖像呈現「面貌的相似性」的看法。但是,兩位女性主義學者皆認為女性主義藝術家的肖像創作,開拓了女性對自我認同的探索。
劉瑞琪的〈莎莉?曼恩兒童攝影中的母性拜物主義〉一文,將肖像攝影視作拍攝者與被攝者的觀視(gaze)與主體的交會場域。劉瑞琪以曼恩(Sally Mann)拍於1984年至1990年代前期的子女肖像攝影為主題,開拓性地從母性拜物主義(maternal fetishism)的理論與觀點,詮釋這些相片所建構的母親 /
攝影家與女兒的觀視與主體性。在攝影美學方面,劉瑞琪援引探討攝影拜物主義的理論,來分析曼恩以攝影紀念性地保存子女消逝的模樣。在寓言的面向,曼恩經常藉攝影來重溫與凝止子女在母體孕育成形的感受,以寓言的手法來展現她的母性拜物主義。在觀視的角度,曼恩還以母親 / 攝影家特有的觸覺性的觀看方式,營造與子女的形象親密無間的拜物幻想。法國的女性主義者伊希嘉黑(Luce
Irigaray)等人提出,女性具親密感與觸覺性的認識論,可以顛覆男性以距離與控制為本的視覺中心認識論,劉瑞琪依循這條理論路線去詮釋曼恩所展現具親密感與觸覺性的母性拜物主義,所建立的母親 / 攝影家的主體性,以及其顛覆父權社會認識論的力量。劉瑞琪也進一步演繹:在曼恩觸覺性的觀視之下,她的女兒逐漸學習與展演和親人、事物及自然較為強烈的聯繫感與親密感,形塑了擁有陰性認識論的女性主體。
張靄珠的〈怪物、人機合體、與後人類女性主體:歐蘭肖像及身體藝術〉一文,探討法國當代表演藝術家歐蘭(Saint
Orlan)的自我形塑,歐蘭導演、錄影並且轉播自己九次的美容整形手術過程,以文藝復興名畫中美女們最吸引她的局部形象植入她的臉部,包括蒙娜麗莎的額頭、黛安娜的眉眼、賽姬的鼻子、歐羅巴的嘴、以及維納斯的下巴。歐蘭也以電腦合成的手法,創作結合自己肉身與多媒體的自畫像,探索怪物 / 母親 / 機器的虛擬連續體形象。張靄珠以哈樂崴(Donna
Haraway)的人機合體之後人類女性主義(cyborg feminism)觀點,探討歐蘭翻轉身體內 / 外疆界的表演,並以德勒茲和瓜達里(Gi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的「無器官身體」概念,剖析歐蘭如何將女人變形為「原子女人」,以「去體現」到「再體現」的過程進行性 / 別操演。
張靄珠所論的歐蘭整形的變臉肖像,展現了後現代女性主義藝術以擬像的自我再現,來拆解女性氣質的社會建構。歐蘭不斷暴露皮開肉綻的整形過程,以及面貌不斷的毀形與重塑,以血肉肖像再現電腦重組過後的理想女性面貌。在大眾傳播與數位科技盛行的後現代,歐蘭以不斷變化與再現的面貌,抹消了與自己原有面貌的相似性,以展演女性亟欲臻至、卻無法迄及的理想認同,來探索與暴露女性氣質的社會建構。歐蘭所展演後現代沒有原真的主體面相,也解構了肖像呈現「面貌的相似性」的傳統模仿觀念,逆轉了傳統的肖像觀念。
在第二部分「認同與變相」這個主題,顏娟英、濮安(Anne
Burkus-Chasson)、徐澄琪三人的論文,都將肖像視為畫家的社會文化認同符號。顏娟英的論文以「面貌的相似性」概念,對日治時期台灣畫家的自畫像與家族像提出精湛的解讀。濮安與徐澄琪的論文則獨闢蹊徑,不以「面貌的相似性」概念,來詮釋十七、十八世紀中國畫家的自我再現。她們透過對畫中圖文的多層次解讀,探討畫家如何在畫面上以變相來表達豐富的自我認同,展現當代改變中的肖像研究典範。
顏娟英的〈自畫像、家族像與文化認同問題--試析日治時期三位畫家〉一文,探討陳植棋、陳進與李石樵三位日治時期的台灣畫家,如何以自畫像與家族肖像來表達他們的社會文化認同。顏娟英認為,他們以多元的藝術詮釋手法,表現身為台灣人的文化認同。陳植棋以堅毅的台灣婦人肖像,傳達堅強與反抗的台灣人認同。女性畫家陳進學習與轉化殖民母國的繪畫語言,表現純潔唯美又具女性自覺的台灣女性肖像。李石樵則以學院派的語言描繪家族肖像,捍衛台灣殖民地上人民的自信與尊嚴。
濮安的〈雅或俗?--陳洪綬獻壽圖及其職業畫家身分〉一文,曾經榮獲1995年美國大學藝術學會的阿瑟金斯利波特獎(the Arthur Kingsley Porter Prize, College Art
Association)。濮安以探討陳洪綬的獻壽圖為主,大量引用題跋、詩作、書信與史料,分層縷析陳洪綬在明末清初的社會變動與政治亂局,如何利用繪畫中的圖文符號,來表達他的自我再現與身分認同。濮安在陳洪綬為親友所作獻壽圖的題跋與圖像之間,看到畫家層疊的身影。她尤其別出心裁地將《宣文君授經圖》(1638)中宣文君身後屏風上孤獨的舟子,詮釋為陳洪綬的化身,一方面代表他超然的史學家角色,另一方面代表他反抗歸順異族的遺民身分。在分析陳洪綬如何以視覺與文學策略來再現自我之後,濮安發現他既非業餘文人畫家、亦非職業平民畫匠的社會認同,展現受過教育的畫家的新定義,解構了明代作家將畫壇截然兩分為雅俗對立的看法。
徐澄琪的〈金農畫梅,君子自寫真?〉一文,則藉由題跋與畫面的交互解讀,發現金農的《梅花圖》(1759)雖然不見肖像,卻滿載金農自我再現的符號。徐澄琪解讀題跋中的文學典故,並對照金農的藝術生涯與時代脈絡,來詮釋金農以梅娛人自娛、自況自嘲的心情。徐澄琪認為,金農在詼諧戲謔之間,以梅花作為自我形象,並在題跋自比女人姬妾,借女人的附屬地位,來感嘆文人在商業畫的揚州待價而沽,又傾吐自己懷才不遇的胸中塊壘。
第三部分的主題為「政治神話」,兩篇論文皆探討呈現「面貌的相似性」的政治肖像出發,進行意識型態的批判性閱讀。法國的符號學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從結構主義的立場更新索緒爾的符號學概念,拓展符號學的領域至社會文化的層面,提出極具批判力的「神話」(myth)概念。巴特認為,索緒爾描述了符徵、符旨與指涉物之間的關係,只分析了符號在第一個層次上的意義,也就是明示義(denotation)。符號在第二個層次上的意義,包含隱含義(connotation)與「神話」等。隱含義是指在某個社會文化的價值體系當中,符徵在表意過程所產生的符旨。「神話」則指當某件事物在特定的社會與文化當中傳播,大眾經由將這件事物與相關的概念或價值聯繫,接受與理解這個符徵在社會文化中的意涵,形成約定俗成的符旨,並成為該社會文化內自然化的看法之時,就形成了一個「神話」。
黃猷欽的〈台灣偉人塑像的興與衰--以1949-1985年的《中央日報》為例〉一文,從巴特所建立的「神話」概念出發,探討偉人塑像的意義是如何透過傳播被建構出來的?並藉此去自然化「神話」,揭露其在當時社會文化中被概念化的過程,以理解其意識型態。黃猷欽提出,從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以降,孫逸仙和蔣介石的塑像陸續豎立在台灣各地的特定空間,成為行使紀念活動的場域,這些偉人塑像經常透過大眾媒介的傳播與詮釋,來發揮實際的功能。黃猷欽以1949年10月台北市中山堂的國父銅像塑像運動為代表個案,將《中央日報》對偉人塑像過程的圖文報導,詮釋成以統治階級所擁有的傳播媒體,以權威的發聲自然化偉人崇拜的價值觀,以公共性與藝術性的論述策略,賦予孫逸仙和蔣介石的偉人肖像不朽的正當性,以建立其「神話」言談。黃猷欽也分析,從1975年蔣介石逝世後,台灣偉人塑像作為「神話」言談逐漸衰頹的過程,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複製的商業性塑像所造成的藝術性消失,另一方面則由於官方傳播媒體已經失去對塑像公共性議題的細緻論述。
意識型態批判經常會去自然化「神話」,段馨君的〈戲劇中的政治肖像與性別扮演〉一文,以周慧玲編導的《少年金釵男孟母》(2010)為主要焦點,剖析戲劇舞台背景懸掛的政治肖像,與劇中同性角色的結婚照,還有演員陰陽倒錯或娘娘腔的肢體展演,形成極大的反差,因而嘲諷了國族、父權、男權三位一體的政治「神話」,以及曝露歧視與壓抑女性或陰柔的身體風格的性 /
別「神話」。換句話說,劇中以藉由性別倒錯與變裝所展露的性別諧擬(parody),解構父權與異性戀自然化男女二分的性別意識型態,並反襯與包抄構築於傳統的模仿觀念之下的政治肖像,其所構築之偉人崇拜價值觀之虛妄。
第四部分以「社會面相」為主題,兩篇論文都將肖像視作傳遞社會意義的符號。曾少千的〈杜米埃的《古代史》:文化記憶與社會類型〉一文,探討杜米埃(Honore
Daumier)的石版畫系列《古代史》(1841-43)以開放和創新的方式再造文化記憶,將社會類型的集體肖像疊印在人物造型與表情描繪。曾少千指出,杜米埃也為當時流行的生理學手冊畫插圖,記錄當時市井小民的行業與生活,而《古代史》中的人物造型就以視覺聯想與類比的手法,融入了生理學手冊中沐浴者與演員類型的身體樣貌與行為舉止,編排現代平凡小民喬裝古代人物,以充滿喜感的方式嘲諷當時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經驗。
許綺玲的〈尋找《明室》中的〈未來的文盲〉……〉一文,探問巴特在1970年代末寫《明室》一書,是否受到班雅明刊於1977年的《新觀察者》畫報攝影專刊內的〈攝影小史〉法文節譯影響?在經過一番文本對照閱讀之後,許綺玲認為,巴特雖然未曾直接引用班雅明,但是從章節主旨、關鍵字鑰、字裡行間,可以揣想巴特對班雅明觀點的迴響。肖像攝影可以說是兩人關注的主要焦點,班雅明在〈攝影小史〉提倡攝影識讀教育,呼籲透過攝影肖像讓觀者學習社會面相之解讀,並且希望大眾(甚至攝影者)可以透過圖說文字導正政治觀點。作為社會符號學家的巴特,則提出肖像攝影是否捕捉人的面目的社會意涵,有很大的程度取決於觀者的主動解讀。此外,兩人都關注於肖像靈性的捕捉與主觀的感受的議題,班雅明藉定義浮動的「靈光」來闡釋,巴特則用「假面」、「氣質」與「刺點」等辭彙探討。
第五部分的主題為「跨文化轉化」,兩篇論文皆處理在西方攝影技術的衝擊之下,中國或台灣的肖像表現如何受其影響,卻又可以順應原有社會的認知與文化特色,轉化成適應當地市場需求的肖像表現。伍美華(Roberta Wue)的〈本質上中國:十九世紀攝影的中國肖像照主體〉
一文,探討在十九世紀中葉肖像攝影引進中國之時,中國肖像攝影師如何追隨在通商港市的歐洲攝影師,建立他們自己的攝影工作室,為中國市場生產暢銷的肖像攝影。伍美華藉由對照在通商港市開業的歐洲與中國肖像攝影師作品的跨文化符號差異,來展現兩種視覺與文化系統的衝突,以及中國肖像攝影師如何以西方攝影技術,融入中國民間肖像畫傳統,並順應當時社會禮儀所期許的人物外觀,以滿足中國顧客的需求。扼要來說,歐洲攝影師喜好捕捉拍攝對象的個人性,呈現笑容、動態、陰影等暫時現象,而且人物的立體與空間的深度都表現得清晰精確。相對而言,中國攝影師的肖像照片注重展現人物身體的完整性,避免陰影的呈現,且整體畫面較具平面感。他們尤其偏好展現人物的社會身分,人物靜態坐在正式的客廳空間中,以合乎禮節的標準化表情與姿勢入鏡,只容許小地方展現活力,並且穿著最好的服裝,用攜帶個人物品來主動建構自己的形象與重要性,以展現符合社會禮儀的理想典型。這種東西對於呈現理想自我的不同概念,導致西方批評家經常嘲諷中國肖像攝影過於死板、公式化,而且手法建立在許多奇怪的前提之下。
蘇碩斌的〈傳神式寫實:日治台灣的攝影認知與民間肖像〉一文,處理日治時期台灣民間流行的祖先炭精肖像畫,在傳統重彩肖像畫、攝影肖像同時存在的十字路口,其高度發展的社會認知因素。蘇碩斌認為,傳統重彩肖像畫延續中國文人「神似」的繪畫傳統,而逐漸取而代之的炭精肖像畫則受到攝影的衝擊,以寫實的表現與重彩肖像畫傳統斷裂。蘇碩斌將攝影術視作一種社會媒介,其機械複製的傳播特色帶來寫實概念的大眾化,為台灣社會帶來認知的變化。然而,台灣民間肖像畫不僅未被攝影取代,而且還以炭精肖像畫的形式流行,乃因台灣社會的認知雖受光學寫實概念的影響,卻仍然繼續保有繪畫需表現「神似」的認知之故。換言之,炭精肖像畫乃是特殊的「傳神式寫實」符號,其歷史位置在於既汲取攝影作品的光學寫實性,又能夠表現人文神韻。
這本書中的中文論文皆經過學術審查,除了原來刊登於有匿名審稿制度的中英文優良期刊與專書的論文之外,其中有四篇新撰的論文皆通過慎重的匿名審稿。在此衷心感謝所有參與本書的作者們,同意轉載或翻譯的學術期刊與專書,以及審稿委員隱藏在字裡行間的學術論辯與熱忱。這本書是一個團隊的心血結晶,特別感謝傅大為、徐澄琪、陳儒修、蘇碩斌與黃桂瑩前後一起在編委會所做的討論與激盪,張思婷、林容伊與章晉唯的翻譯,以及專任助理劉仁洲與遠流的曾淑正在執行編務過程的悉心協助。我們也想共同感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大、中央、清華、陽明)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處(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的部分經費支持,以及其中視覺文化研究群七位老師在此貢獻與交流研究成果。
這本書緣起於本人在陽明大學人社院與傅大為、徐澄琪、蘇碩斌、陳香君的多次聚會醞釀,令人萬分惋惜地是,在我們開始以肖像為主題向台聯大與國內外學者邀稿之時,香君已經因為癌症住院療養。在西方肖像源起於希臘神話中科林斯少女(Maid of Corinth)的故事,她在愛人遠遊前夕,將他在牆上的側影描繪下來。
這本以肖像為主題的論文集,深藏著我們親愛的同仁香君離逝的記憶。德希達在前述《盲人回憶》一書,指出「眼淚而非視力是眼睛的本質」,「只有人類知道如何超越看見與知道,因為只有他知道如何哭泣」。當我們的視象被淚水弄得朦朧不清,我們才最接近「眼睛的真理」。 眼淚是同情的瞭解,我們為香君的受苦流淚,並以本書緬懷陳香君(1969-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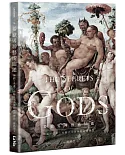



![工藝製造現場 第一話:鍛・練[線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90%2F14%2F0010901427.jpg&width=125&height=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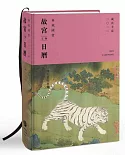
![第十九屆風城美展:展出作品專輯[軟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9%2F73%2F0010897326.jpg&width=125&height=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