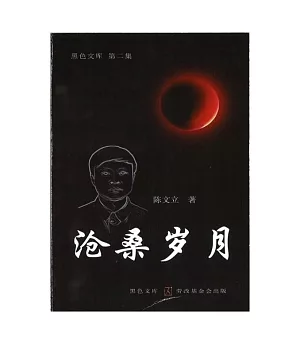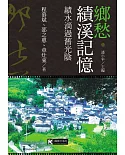序
在美國西岸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陳文立。他看上去白白淨淨,有點靦腆,說話有些兒木訥。他很像為數不少的在加州高科技公司裡做技術工作的中國移民,一個平常而規矩的人,我實在難以將《滄桑歲月》中一段又一段令人駭異的沉重故事與這個人聯繫起來。
陳文立讀過的覺民小學、時代中學(聖芳濟中學)都是我曾就讀過的學校。《滄桑歲月》中提到他的一些鄰居、朋友、同學,其中有一些還是我相熟的。他當年在上海的那種生活環境我十分熟悉,因為我們的家庭背景和出身相仿。
陳文立同我談起過他的十年勞改生涯。我向他擺了一點“老資格”,因為我在勞改營中待過十九年。他的勞改經歷,不消多費唇舌,我心領神會十分瞭解。如果他想誇大或者隱瞞一點,也許別人不會覺察,而我馬上就能“拆穿西洋鏡”。我認為作者在這本書裡對獄中形形色色的人和物所作的描寫,具體而微又十分翔實可信。
作者是個虔誠的天主教信徒,因而有一個和平善良的性格及寬闊的胸懷,對物質慾念也看得十分恬淡。歷經劫難,得以倖存之後,也並未懷著報復和仇恨的心情,要把這個世界虧欠他的加倍追討回來。他在共產政權下,吃足了人間苦頭,連宗教信仰的權利也被剝奪,天天生存在恐懼的階級鬥爭中。如今在自由世界的他,又回覆了那種灑脫平實的真面貌,令人格外感到彌足珍貴。我權且把這詮釋為宗教的善和正,戰勝了中共意識形態的惡和邪吧。
面對精神上的恐懼、絕望,肉體上的摧殘、蹂躪和物質上的匱乏,一個凡人有多少承受力和容納量?這是因人而異的,多數人承受力薄弱,容納量淺短。在大陸的浩劫之中,成千上萬的人不願也不能承受壓力,因而跳樓、服毒、上吊等自殺的慘劇成了人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讀了《滄桑歲月》,不免要問,陳文立具有超乎尋常的承受能力嗎?他不是凡人吧?陳文立這樣的倖存者是多數還是少數?這五十年來,老舍、傅雷這樣的人又有多少?
我們認識多年之後,這位文質彬彬的天主教信徒——當年的解放軍戰士,終於向我吐出了他胸中塊壘——他殺過人。我曾經歷過多次這一類的共產黨的“正義行動”——殺人給人看,或者說“人民民主專政的教育”。但是,我面前這個陳文立竟然曾是中共的劊子手,這一下子把我駭住了,許久回不過神來。
讀過《滄桑歲月》,會有一種想法,人有時會比魔鬼更魔鬼。人不僅自己可以成為魔鬼,而且可以驅使別人變為魔鬼的魔鬼。陳文立就是一個實例。他被選中當刑場槍手,擊斃了二名犯人之後,他一轉念,使出神槍手的高招,再接下來的五次射擊中,故意將犯人的腦袋打開花,腦漿四濺,殺得性起,“眼露凶光”。他說當時除了覺得濺粘在自己身上的甜甜的腦漿味道噁心之外,沒有別的感覺。怎麼會是這樣?這麼一個有家庭教養的人,一向自愛向上,甚至愛憎分明,具有正義感的人,怎麼一得到上級的指令,就從“人”到“魔”殺起人來,而且還殺得那麼理直氣壯,殺得痛快而漂亮呢?原因在此:他當時是一個“革命戰士”,執行“黨的革命任務”,因此這一切是神聖的、光榮的。中共把人“改造”到這般地步,恐怕古今中外還沒有先例。
誰割了張志新的喉管再槍斃了她?答案:某一個“陳文立”。
誰在鐘海源槍決以前,強行把她的腎臟摘割去做器官移植?答案:又一個“陳文立”。
給違反計劃生育、懷孕八個月的母親腹中胎兒打鹽水針強行墮胎的又是誰?答案:另外一個“陳文立”。
什麼人揮著解放軍的銅頭寬皮帶,把自己的老師打得頭破血流?答案:某一些“陳文立”。
舞文弄墨,當年的“梁效”寫作班子,或曾是文化部長的才子,用筆桿子殺人的人又是誰呢?答案:還是那一批一批的“陳文立”。
“陳文立”到底是誰?
我們是“陳文立”嗎?!我們不是?!誰是?
“陳文立”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每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凡是“陳文立”都唱過“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是一首上至周恩來,下至我那樣的勞改反革命分子都唱得響徹雲霄的歌。這是那個時代的歌。
今天,這個時代並沒有過去。這是一個荒誕的年代,半個世紀的荒誕使人無淚、無言。也許,只會使人發噱。
《滄桑歲月》讀完之後,留下一片空白。
勞改基金會執行主任 吳弘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