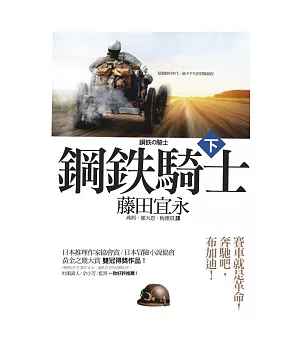解說
人性與正義的狹間—鋼鐵騎士 熊次郎
1930年代的歐陸充滿不穩定的氣氛,經濟暴跌、強人政治、軍備問題、姑息主義、左右派激鬥、國際政治暗雲密佈。這段令人眼花撩亂的年代,正是《鋼鐵騎士》一書的舞台所在。
本書主角為日本貴族青年千代延義正,他在1930年曾參與共產黨活動,後來因為向同黨供認兄長是間諜而使兄長被殺,失意之餘在1935年隨父親(陸軍武官)渡法來到巴黎。因緣際會下他去看了的黎波里賽車,便立志成為車手,進入修車廠學習並和同好強.路易立志組成一個車隊。義正陪同強.路易找尋失蹤的母親而捲入當時國際諜報戰之中;他在日、德、蘇、在法白俄人的糾葛之中,被列為追殺目標;同時他認識了盜賊弓王子一夥,也變成法國警察追逐的對象。在這混沌的國際諜報戰中,以賽車手為主軸,以傑出的構成力。編織出一幅30年代華麗的大型繪卷。作者甚至想把30年代的時代感覺與歷史完整地寫出,同時處理時代的大哉問─「革命」、蘇維埃、左右翼的矛盾和相容。
革命=正義=政權=黨?
在20世紀2、30年代的知識份子間,讀馬列是一種進步時髦的象徵。知識份子受到人道主義以及馬列的吸引而傾心於蘇聯,把當時唯一的「無產階級國度」想像成心中的祖國,把共產主義當做人類的答案。在書中,主角義正也參與了共產黨活動。到了巴黎之後雖與政治無緣,仍然一直對蘇聯抱有好感。不過隨著故事內容的進展,他開始聽到一些人透露蘇聯的真相。他想知道,究竟真相是什麼?當時的年輕人熱中於共產主義,是不是只因為覺得新思想很酷?
無產階級推翻沙皇的革命令人熱血沸騰,但革命建立的政權未必就是正確答案,這種想像是把「革命」和「政權」做了不當的聯結。對革命的憧憬最終轉為對蘇聯的歌頌,但這完全是兩回事。無論是哪個政權都不可能歡迎革命─包括革命政權也一樣。本書認為:革命是自動的發生,可是在那一瞬間之後就什麼都不是。新政府登場的瞬間,革命就消滅了─革命本身與革命政府其實是天差地別。
另外,一切由黨來指導、下定義,也讓獨裁黨成為離正義與革命越來越遠的怪物:
「黨以讓階級成其為階級的思想為根基去指導階級鬥爭,聽起來是很好,但結果變成走在前端先進的黨做什麼事都可以…。並且,在黨的指導下,勞工努力變成所謂的『勞動階級』。你不覺得這很怪嗎?」
黨下定義之後,所有人都要變成黨所要的模樣。為了保全「革命」(其實是政權)是否可將一切的惡事合法化,這也是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和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終極關懷:為了某個至上目標,一切都可以被容許嗎?革命成就後的清算與鎮壓,若是把今日的痛苦當作美好將來的擔保,但如果那將來並不存在呢?這也正是「目的」、「手段」均要正當之辨的哲學命題。
「伊凡:如果無產階級專政是正義的話,保衛它的恐怖手段自然也是正義了。」
畫出了美好將來的藍圖之後,將所有的屠殺合法化。屠夫們個個都對此抱持堅定不移的信念;白天人人雙手血腥,晚上回家和樂團圓-既然信念不容質疑,自然也不會有罪惡感。「真理」是霸道的,它在某種層面剝奪了獨立性的思考,讓人必須毫不懷疑地全盤接受整套價值觀。但人若失去懷疑的能力,也完全失去進步的空間了。
蘇聯的真實狀況:革命政權的真相?
人道主義者、大文豪紀德(Andre Paul Guillaume Gide),曾經問了當時知識份子最沉痛的問題:
『蘇維埃的現況,與其最初的理想大相逕庭,事到如今這一點已毋庸置疑。但是,即便如此,我們就能質疑他們最初所期望的可能性嗎?他們的理想破滅了嗎?又或只是面對無預警的困難,因而暫時勉為其難的退讓妥協呢?』
30年代的當時,他身為蘇聯的支持者,然而去嚮往的蘇聯看到真實狀況後感到幻滅,反而被某些知識份子孤立。但是他的沈痛告白:或許這僅是實踐上一時的不順,但可以因此就否定讓兩個世紀的知識份子為之瘋狂的共產天堂遠景嗎?馬克思主義反映西方在啟蒙運動之後是多麼地欲求甚至在社會科學中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理論體系。但在與「人」相關的體系總有例外,沒有真正和諧完美的唯一解答;馬克思唯物的科學分析完全忽略了最基本的變因─人性。無所不包的一元體系勢必忽略個體的精彩及不可預測性,終究只會是空中樓閣。
蘇聯的五年計畫是相當蠻橫,強迫遷徙、勞改,並動用秘密警察清洗反對份子,不容任何異議。對憧憬共產主義的無數外國青年如義正而言,知道「革命政權」真實的情況是有多麼痛苦!
「因為共產主義國家只是空中樓閣。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不對,應該說為了讓它看起來像可能,需要許多勉強。史達林越勉強地高舉共產的旗幟,對周圍的猜疑心越深…原本一黨獨裁這樣的想法就有著產生獨裁者的要素。史達林把列寧思想粗略地解釋及放大,這和他的權力慾混合,現在蘇聯就變成這樣前所未有的扭曲的國家。」
確實史達林是個罕見的劊子手,但整個蘇共政權的建立者其實也雙手血腥。蘇聯革命的成就只證明了即使無產階級政權誕生,民眾想像的烏托邦也不會出現。許多人抱著鴕鳥心態,把所有傳達真相的話語、以及蘇聯30年代數次審判的新聞都當作是誹謗。然而就像義正說的─沒有一個叛國者在法庭上堅持自己的清白。自證己罪的被告或是洗腦政策下的產物,或是為了換來家人平安的承諾。然而一個被告沒有人權的國家,還能相信國家有什麼對人性尊嚴的基本尊重嗎?
本書中義正一直追尋的問題是:革命是什麼?蘇聯的真相是什麼?然而答案卻只是偽善的體制和理想的幻滅。
「失去絕對的對立」
閱讀雙重、三重間諜的心理,也是間諜小說中饒富興味之處。本書創作的一位雙重間諜,如是說道:
「我的命運就是無法找到能切合自己心靈的歸處…所以我的命運就是雙重間諜…要同等地愛兩個人,勢必每次不得不背叛某一方。要維持這個精神狀態很辛苦。要選擇某一邊作為心靈的答案,只能欺騙另外一方別無他法。大部分的人都會受到良心的苛責,最後選擇了其中一方。這個行為看起來很專情,事實上只不過是保護自己的內心不要崩壞罷了。我從小就嘗盡不得不腳踏兩條船的苦痛。…這個世界上沒有真切地可以把握的東西,唯有同時背叛雙方的生存方式,好像才最適合我。」
該名間諜在蘇聯陣營,義正被抓時他再度倒戈,並對義正說:
「藉著背叛蘇聯密警察,我想回到一直以來處在不安定狀態的自己。但是沒辦法。不知道為什麼,或許我們的周圍已經不像以前絕對的對立了。」
失去絕對的對立─這句話,暗示著30年代最大的驚奇:1939年,蘇聯與納粹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納粹是以反共反猶起家的政權,共產主義也以納粹為假想敵。這兩個國家的對立,也正是讓英法在姑息主義步步退讓之餘並未用心拉攏蘇聯的原因。英法對蘇聯要求簽訂互助條約一事僅給予冷淡回應,導致不安的蘇聯終究投向納粹懷抱,種下敗因。這個攜手也提前在本書登場─歐盧羅夫斯基元帥(歷史上的圖哈切夫斯基)叛國事件。
30年代國際最大的驚爆點就是左翼與右翼國家的聯手。乍看之下完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卻殊途同歸,使兩主義的信徒都相當震撼。對他們而言,這種價值觀的崩壞並不是易於接受的。而活在對立的裂縫兩側的雙面間諜,也這樣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儘管只寫到1938年,納入這件大事,讓這本小說呈現了一個很完整的三零年代。
無用的極致、浪費的美感:革命、貴族、賽車
知道了共產革命真相的義正,還是抱存一個最終的疑問:為什麼貴族出身的自己,會為革命和賽車這兩個看似毫無關係的事物著迷?
千代延少將想不透自己的兒子義正為什麼要把生命捐給高危險性又”無意義”的賽車,殊不知他將性命奉獻給軍部的狼子野心,其實也是相同的。「有意義的死」,世間幾許?或許「無意義的死」,才是生命的常態。
抽離人們在「革命」上面追加的標語和意識形態,在小說中作者想要處理這個問題:革命為什麼使人熱血沸騰、賽車與革命有何關連。這也就是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學說─人並不是只為了追求有用的東西而活著。革命只是一個超越善惡的狂熱瞬間:
「革命雖然是對富裕浪費的反動,但是革命的手段沒有『浪費生命』這樣的封建時代感覺是辦不到的。粗魯點說,沒有蠻勇精神之地,群眾蜂起和暴動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和漸漸崩解的封建社會有著某種連結的大革命,在中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兩者之間是不可能會發生的。因為兩者都是以生產和累積為目的的異種花朵,根本否定了封建社會所擁有的『毫無意義的浪費』。」
賽車雖然花費大筆金額研發製造,但很可能一上場就報銷,可以說更是「無用」的極致。然而,上萬人卻來到賽場只為觀賞它的奔馳。或許是被賽車喚醒了近代人潛意識下的、毫無目的浪擲財富與生命的美感吧。
「你在革命中所尋求之物和賽車的狂喜流著共同的血液。革命和賽車,都給人似我非我的瞬間。我想似乎在那一瞬間,已無成敗得失和善惡之分。以『善』為目標的革命、一擲千金的貴族、為毫無意義的事犧牲生命,在那個時點全都是一樣的。」
忘我地高速駕駛,是不是和革命暴動時一樣的心境?這樣一來,義正的問題有了答案。須崎老人說,義正其實還帶著一顆古風的心。那也就是封建時代留下來的豪情─超越價值觀的浪擲之美。
現代人口口聲聲「要活得有意義」,但或許生命永遠找不出何謂「有意義」的答案。帶著巴提耶所謂封建時代的基因的我們,若能在自己所愛的事物上浪擲生命,或許就是相當值得的人生了。
作者:熊次郎,文字評論者,現任職於法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