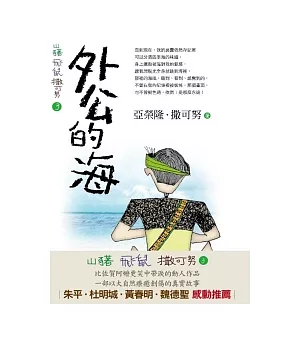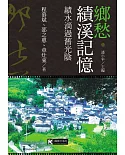推薦序一
杜明城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一位鍾愛口語傳統的同事在讀了《外公的海》之後,頗為自得的對我說:「你看,我沒說錯吧,他們原住民朋友,只要把自己的生活經驗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就已經是一部精采的作品了。」我聽了點點頭,然後又搖搖頭。是的,原住民自有他人所沒有的歷練與體驗,因此讀他們的作品,確實帶有一種新奇的享受。重點在於「原原本本」四個字,每個人都能夠敘說自己的過去,但要能做到讓讀者一口氣「欲知其詳」,就必須具備過人的敘述技巧,同時必須語氣真誠,才能讓讀者有如親臨其境,與之同悲共喜。撒可努確實發揮了這樣的才情,不著痕跡的展現他的口語文學本色,讓閱讀的過程充滿愉悅。
《外公的海》讓我想到一部重要的西方文學作品,也就是《小癩子》(Lazarrillo de Tormes)。這本篇幅不長,形式粗糙的小說,以口語的方式記載了後中世紀一個乞丐的童年史,因此開啟了流浪漢小說(novella
picaresque)的文學傳統。小說中的主角出身寒微,當時的制度必須要依附一個主人,小癩子在艱難的生存鬥爭中不斷的更換主人,養成過人的街頭智慧,也見證了整個時代的虛假。撒可努的故事最大的魅力來自於他能擁有深厚的口語文學傳統,所以,《外公的海》和《小癩子》一樣,我們感覺是聽故事,甚於讀故事。原住民的生活處境無疑是艱難的,撒可努也就把他的街頭智慧也發揮得淋漓盡致。差別在於《小癩子》的詼諧口吻其實摻雜了尖銳的控訴,《外公的海》則詼諧之外帶著達觀,所有的苦難似乎都被哭笑洗淨沖盡了。淚水可能多了一點,情感也少了一些含蓄,但這正是撒可努式的「原原本本」。認識撒可努的人,肯定更能心領神會他特有的語法,口氣與神態都是不折不扣屬於作者本人的。好的作家必須能讓讀者分辨出獨特的面貌,我相信任何不識作者的人都能在閱讀中勾畫出作者的模樣。
近些年來,大概是要標榜多元文化吧,作家常常被劃分到各個不同的族裔,像是女性的、原住民的、客家的、同志的……好像不如此就無以彰顯其作品的特色一樣。我對此頗不以為然。好的作品固然須建立在作者的生活體驗,也因此必然不脫其族裔的痕跡。但真正一流的文學自然能超越這個藩籬,擺脫族群的疆界,豐富集體的生命。我也不想按照學院的分類,把《外公的海》歸為兒童文學、寫實文學、生態文學、山海文學或是少數民族文學。事實上,撒可努的故事跨越了種種類型,是有血有肉的生活文學。
服膺杜威學說的讀者,在讀了〈外公的海〉、〈跟石頭說話的人〉和〈山裡的小獵人〉這系列的自傳小說時,一定會覺得如獲至寶,為「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這句琅琅上口的箴言找到絕佳的範例。學校教育的蒼白,在《外公的海》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證。學校不會教孩子怎麼抓蝸牛,不會讓孩子去捕魚撈溪蝦,更不會讓孩子上山打獵。游泳也不是上課學來的,生活是最好的老師。我想到泰戈爾說的,「貧窮是最好的教育」。我們當然不希望為了教育讓孩子陷入窮苦之境,但過度的安逸確實讓孩童無以成長。撒可努畢竟是幸運的,他能像許多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中的主人翁那樣,歷經山海的錘鍊,從嚴苛的生活挑戰中茁壯。《外公的海》記載的不只是排灣族童年的共同經驗,也豐富了我們對台灣這片土地的集體記憶。
撒可努目前的職業是警察,身分是作家兼研究生,同時也是孩子的爸爸,他的生活顯然已經進入了「後」(post)《外公的海》的年代。英文的post帶有既延續而又逆反的意涵,生活本來就是不斷與週遭環境相互辯證的旅程,他的天地又添增了多少可以為我們敘說的題材呢?這本書為撒可努的童年經驗畫上了句點,而「作為愉悅讀者的我們」(仿撒可努的語法),應該可以合理的期待他的下一個故事,下下一個故事……。
自序
亞榮隆.撒可努
第十五年,我的第三本書《外公的海》,它,很多人都在等。寫了什麼?我不知道要從何說起,但這本書的確讓我寫了十五年,這十五年,有很多的時間花在像穿越小叮噹的任意門,或是坐時光機器回到我的記憶裡去找我的童年,我也不知道這本書會不會是大家所期待的,但對我來說這是我寫的,很有撒可努的風格。
在我快要四十歲、三九.八歲時將這本書作為我生命經歷的一個很大的里程碑。距離我第一本書到現在,很多人都在問:「什麼時候出書?為什麼這麼久?要等十五年?」
對我來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就當作家了!這是我未曾想過的,記得我第一次將我的手稿拿給不是我現在的出版社,是另一家在出版界很有名的出版社時;從編輯到老闆各寫了三封信給我,寫的內容,給了我很多在寫作上的建議和想法,但都不被我接受和理會。那個感受,讓我想到了小時候我的老師看不懂我寫的作文一樣。形容水果很多,我沒有辦法像一般同學那樣寫出「滿山滿谷」或「堆積如山」及「像繁星一樣多」的文字,我只能在我的作文簿上這樣寫著:我的眼睛裝不滿啦!又或是太陽下山的形容,我寫不出「太陽公公滾著火輪子回去」或「太陽西下伴我歸」的形容,而只能是這樣的形容:太陽被山的稜線吃掉了。當時,看不懂我文章的老師卻在我的作文簿上批示:「文藻詞彙不通」、「跳耀式邏輯不切實際」,但我自認為寫得很好啊!老師怎麼會看不懂?所以當有次老師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示「朽木不可雕也」時,我便在旁邊寫道﹕可是可以種香菇。
有很多次對外的演講,我常這樣說:「我會寫文章,不是學校老師教的,而是我的阿公、阿嬤給我的。」這是我長大後才慢慢了解的,原來;我的身上有著那麼多阿公、阿嬤的思維方式和從很早以前就植入在我身上的元素,我的寫法、文法就只有我有。
還好我沒有聽出版社的建議,將原來的文章改變或朝著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去寫,我連想都沒有想過!就是這樣個性的我,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堅持還是固執。有一天,經朋友簡唐夫婦的介紹,認識了現在出版社的老闆嘉慧姐,才改變了我之後十五年至今的生活。我開始演講,多了另一個演講的領域,還去到美國和日本;尤其在美國認識了老爹和老媽,這又是我生命中另一個轉折。老爹說:我從來沒有一次把一本書,用我坐飛機「由台灣到美國」的時間,一次看完。在美國見到很多的新奇,對他們兩個老人家來說,他們可能都不知道那一次的美國之行對我的視野和想法影響很大。這是我想都沒有想過的,得獎更是驚喜的意外,有一天當自己的文章收錄在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或國外學校成為學校的教材或讀本時,那種意外才更大!我怎麼可能跟李白、杜甫他們並列出現在課本裡面﹖以前讀書我是讀別人的文章,現在是別人要讀我的文章,那種感覺真的很奇特!當自己的作品被拍成電影,還到美國去參加影展時,我竟然能在九一一事件後帶著我必帶、必備的三把刀子進出美國,穿傳統服飾走在好萊塢的街上,我只能說;真的很酷!
那一次,真的感謝電影的老闆徐順理,讓我見識到更不一樣領域的東西。當電影老闆跑來找我,要把我的作品改編成電影時,我問了她:「為什麼想拍它?」
她說:「這才是台灣,這是我們可以對外宣傳的台灣精神。」
我說:「好!拍吧!」
我一直記得電影在美國參展,觀眾看完電影之後,有位印地安的酋長問我:「你會一直這樣堅持你的自我文化和族群部落嗎?」當時,我非常堅決的回答他說:我會!因為,不用半個世紀或三十年,我的孩子如果還能穿上我身上的服飾,並且深愛著自己的文化,那麼,我們便替這個世界留下了美麗的遺產,替台灣留下了美麗的資產,替自己的孩子留下了他們未來的財產。又之後做成了卡通,這些對我來說,甚至自己有時候再回想,也都會覺得「真的很不可思議」!那些改變都在一瞬間,讓我不僅心想,還好我沒有去聽××出版社的建議和改變,不然,今天不會是這樣,被大家看見。
我的心有很多的感謝和感恩,這十五年來受到很多人的關心、鼓勵和支持、照顧及提拔,讓我的視野無限的延伸和廣大。這幾年我由台北的工作請調回到台東,回到台東後,那種像回到母體的親暱感,充滿了自己的身體,我的心安了!我開始蓋我的房子給我的家人,又有了三個各自不同性格的女兒︱︱戴雲、戴晴、戴嵐,看著她們自由無拘、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一直在玩」的長大,就會有一種莫名的成就和喜悅。我的心裡一直有一個聲音︱︱去讀書吧!也不知道為什麼?五年前,我到空大讀書,又開始開啟了我生命的不一樣。現在的我;正在台東大學的兒童文學研究所讀書,在過去很多的場合很難再看到我,很多人很訝異的問我:「你去讀書囉?你那麼老了還去讀書?讀那個能夠幹什麼?對你現在的工作又沒有什麼幫助?」我很難去解釋也不想再做解釋了,讀書是為了自己讀書吧!讀書後,才又讓我繼續想寫書,寫書是因為在學校聽到了很多不一樣思維的東西,對我來說,這些在我寫作上給了我不一樣的思考和元素。
在這裡,我要感謝的人有很多——一大串講不完,我深怕寫了誰的名字,又怕誰的名字被遺漏了!但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我的妻子阿真,感謝她幫我搞定我那三個女兒,讓我不用擔心她們會跳到我的書桌上吵我;還有感謝在出書的前夕,台東區弟弟和妹妹們的幫忙,將我的文章再做整理,讓《外公的海》能趕在發表會的前夕完成。我知道很多人在期待這本書,看吧!就讓我帶著你們穿越現在,回到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