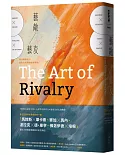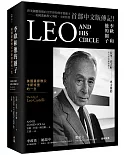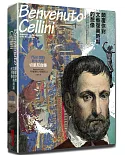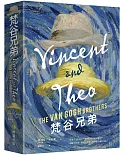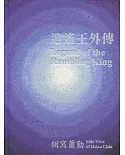序
裸體公民艾未未 貝嶺
艾未未留著大鬍子, 曾是個兩百八十磅重的龐然大物, 他虎背熊腰,有著中國北方爺們的相貌。他雖笑容憨厚,可言談及神態中總帶著不難察覺的不屑,他話不多,句子簡練,敏銳中透著犀利。他對中國的政治現實有著非比尋常的清醒和充分的認識。他那曾有著近三百七十(3,697,000) 閱覽人數和七萬粉絲的部落格(www.bullogger.com/blogs/aiww/)
曾是一個網上的公民社會, 當部落格被封後, 他又經由推特(twitter)上的互動對話,讓網民產生公民意識,以了解及面對當下中國的黑暗面。
探討艾未未,不能忽略他的叛逆性格,他的野性。他在北京出生,兩歲多即隨詩人父親艾青、母親高瑛流放新疆,1966 年至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 時期,約有五年的歲月,艾未未目睹父親每天打掃十多個廁所,他甚至自嘲十七歲以前從未用牙刷刷過牙。他或對學院沒有什麼好感,也沒從任何一所大學畢業。
1978年夏,他入讀北京電影學院,1981年,他退學飛往紐約,先後在費城及加州就讀語言學校,1983年,艾未未進入紐約帕森設計學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學習,可不到一年,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據說是因為蹺課太多,學校停了他的獎學金,因此,艾未未不再去學校註冊學生身份,索性「黑了1」,成為紐約龐大逾期居留者中的一員。
「裸一下! 」
裸或赤裸成照,本是艾未未個性中的一部份,也是艾未未藝術家生涯中的一個執著點。從1980 年代中後期他在紐約東村(EastVillage) 的地下室公寓及紐約街頭裸體自拍開始, 艾未未以裸示人、以裸挑戰禁忌,由最初的嬉鬧、叛逆,走到以裸嘲弄、以裸消解、以裸不屑世間的權力,最後,走向以裸的肉身和國家暴力直接對峙。
艾未未在紐約東村街頭晃蕩了十年, 有著非同一般的生存經驗。東村是詩人、作家、歌手、嬉皮、龐克、佛教徒、錫克教徒、光頭黨、吸毒客及賊、銷贓者出沒的區域,可他和他們如兄弟般熟悉。1988 年10
月,我初次踏上紐約,「星星畫會2」畫家、詩人嚴力帶著我去見艾未未,還沒走到他東七街的家,就在半路上撞見了他。我始終忘不了在紐約街頭初遇艾未未時的第一印象,他穿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士兵軍大衣,一頭亂髮,人已開始發胖。未未與不熟的人見面時靦腆,甚至羞赧臉紅,可笑容中藏著想捉弄初到者的「不懷好意」。他會輕鬆地勸說你:「裸一下吧!這是紐約!」我初來乍到, 正被五花八門的紐約搞得暈頭轉向,
內心就算再叛逆,還是不敢裸。他看出我初到紐約的生怯,「壞」笑著說:「拍張裸照吧!」、「咱們一起裸一下!」。當我們跟著他晃蕩了幾條街, 快被他說服, 正要脫, 讓他拍張裸照的時候,
我及時「清醒」,在瀕臨被說服的臨界點煞車。回想我當年在紐約三天兩頭就要換個住處的窘況,我若「不幸」在艾未未家住了幾晚,肯定是逃不過他的相機的。實在很無聊時,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這是艾未未「裸」熱衷的初期,那些照片中的他有時裸著,有時穿衣。我甚至以為,他在紐約最喜歡幹的事兒,就是在不允許全裸的街頭,乘警察不備,隨時脫!拍上一張,然後迅速穿上衣服離開。我在他東村的家裡看過不下十數張認識的藝術家或友人的裸照,不少是艾未未和他們一起裸,其中以他和嚴力在紐約世貿廣場雙子星大廈前的裸照最「養眼」,兩個瘦男子一絲不掛地裸著,雖然雞雞縮到快看不見了,可笑容燦爛。艾未未曾這樣描述這張照片當年的面世:「嚴力說咱們倆合個影,我想這多無聊,我說那咱們脫光了合影。他有點猶豫,但是他覺得他體形比我好,還是脫了。太高興了,
陽光下面就是我們, 沒有別人。那是個沒有皇帝的年代。」
而他東村的家也曾是買賣二手相機的「黑店」,其中一間黑不見底的房間門一開,床上總擺著幾十部相機。他是東村街邊地攤上的常客,這些相機是他從地攤或急著脫手的竊賊手上廉價購來的。漸漸地,他就也成了修照相機的高手,修好的相機,會賣給那些想要相機的人。1990 年, 我, 一個因1989 年「六四」而留在美國的「文學難民」, 受布朗大學校長格列高利(Vartan Gregorian)
的邀請,獲任駐校作家,「掛」在英語系創作專業(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名下, 每月竟有一千五百美元的「高薪」, 我如同中彩,突然「發」了。這事兒讓未未知道了,在我某次回紐約時,將.....
我約到他的「著名」公寓,領我到那個床上堆滿相機的房間,未未天花亂墜地向我介紹著一款款相機,非要分享一下「彩」運,我被他「連哄帶騙」,加上嚴力在旁敲邊鼓,當即掏出四百多美元買了一台。記得未未收下「宰」到的錢後,高興地帶著我們到中國城吃了一頓。這台沒有變焦鏡頭的相機我始終沒使用過,後來,它在我動蕩、遷徙流離的生活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