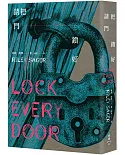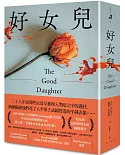序
尚建國先生並不是因為政治問題被共產黨政府判刑勞改的,今天他把實際服刑九年中的所見所聞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是很難得的。這是《黑色文庫》中第一部九十年代非政治犯勞改生活的寫實。
199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停止使用「勞改」兩字,將所有的勞改隊改名為監獄,司法部下轄的勞改工作管理局改名為監獄工作管理局。當局聲稱這將有利於北京政府在國際社會中有關人權問題方面的鬥爭。意思是使用國際上通用的監獄一詞,不再用有中國特色的勞改二字,也許能避免同蘇聯的「古拉格」那樣被世人譴責。但是聲明中強調「監獄對罪犯的強迫勞動及改造思想」的基本政策及內涵不變,這是名副其實的換湯不換藥。尚建國在書中提到「囚服上面還用紅的油漆刷著'勞改'二字」。這就再次印證了今天的「監獄」與昔日的「勞改隊」只是名詞不同而已。
中共的監獄(勞改隊)中從來是刑事犯為多數。政治犯所佔比例在五十、六十年代是相當高的,但總是少數。許多刑事犯罪分子確實做下了無論在哪個時候、哪個社會都不能容忍、應予以懲罰的罪行。當世人批判中共的勞改制度,認為它是共產黨專政的鎮壓工具,呼籲廢除勞改制度的同時,是否也讓作為勞改對象的刑事犯罪分子,歸到無辜者的行列,「一二三」闊步走出監獄(勞改隊)呢?也有人提出,
他們只關心那些因政治、宗教、信仰等原因被中共關進監獄的人──即所謂「良心犯」或者政治犯,為之呼籲,為之爭抗。至於刑事犯罪分子,則不在考慮之列,他們罪有應得,怎麼懲罰都不為過。我們應該怎麼回答這樣的問題?
尚建國在本書中描述的人物,大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且不論他們所經歷的司法審判是否公正,僅從他們在監獄中的待遇來看,應該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即──不應該這樣對待「人」。即使犯了罪,犯人也首先是一個「人」。犯了罪應受懲罰,但應尊重他們作為人的權利。呼籲把他們當作人看待,保護他們的人權,並不是庇護他們犯的罪。如果這樣一些被認為十惡不赦的壞人亦在人權考慮範圍之內,那當然更不用說良心犯、政治犯了。
五、六十年代,許多刑事犯罪問題都用政治罪行清算,例如一個地主子弟因飢餓偷了人民公社的糧食,這是反革命罪行,是反革命階級的「反撲」,判刑很重的。近十多年來,中共當局刻意避免用政治罪名進行鎮壓,「反革命」一詞已廢除,而代之以「顛覆」、「盜竊國家機密」,普遍地使用「嫖妓」、「非法集會」、 「邪教」等罪名來行鎮壓之實。
中共的政治理論奠基於馬列主義的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點,認為犯罪的根源來自於剝削階級的思想及本質,它認為對刑事犯罪的鬥爭是政治問題,是影響到政權穩定的問題。懲罰刑事犯罪的最終目的是「改造」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尚建國書中提到,每一個囚犯必須牢記及背誦「罪犯改造行為規範」,其中首要的一條是「擁護共產黨,服從黨的領導」,其次才是遵守紀律,不准打架...不准留鬍鬚等等。所謂對犯人進行「思想改造」,不僅僅是從道德上、思想上、和心理上去矯正,更重要的是有一個政治服從標準,這是世界上其他監獄所沒有的。
我本身在勞改隊中的十九年生活經驗,與尚建國九十年代的有相同之處,亦有不同之處。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勞改隊中從沒有聽說過可以用錢來達到減刑或假釋的,現在幾乎比比皆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現象,與整個社會上上下下的腐敗狀況是相呼應的。其他方面,如批鬥會、思想總結、強迫勞動、牢頭獄霸都大同小異,沒太多差別。共產黨認為監獄、軍隊、警察、法院等等是國家機器、
是鎮壓工具,這個基本出發點並沒有改變。
1956年蘇聯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關閉了許多勞動營,包括最有名的遠東地區的馬加丹勞動營。從三十年代起,斯大林遣送了約一百萬人到這個規模巨大的勞動營,其中大多數是刑事犯罪分子。赫魯曉夫及蘇共廢棄了階級鬥爭的理論,改成全民國家,但是蘇聯還是共產黨統治的國家,還是一個黨一個主義的國家,還是一個專制制度,所以勞動營依然存在,克格勃照舊橫行霸道。一直到1991年蘇聯共產黨解散,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解體,勞動營及克格勃才壽終正寢。
今天中國大陸的社會,不論在經濟、文化、政治以及監獄方面,與前三十年毛澤東時代有相當程度的不同之處,本書中所描寫的一些監獄狀況, 從犯人可以吃飽到有些幹部的相對仁慈和「愛才」上看,的確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以前刑期滿了的犯人還得「留場就業」,
可以說一旦入獄,牢底坐穿,終身為奴,如今刑事犯通過關係能獲得減刑或假釋,再不然刑滿後也可以回家。這種表像上的改善並不意味著中共政治本質有根本的變化。毛澤東的基本觀念、理論、政治架構及制度都由現今共產黨統治者所繼承,並奉為圭臬,這一點在尚建國的書中亦可見其一斑。只不過今天的勞改制度受到經濟熱浪的衝擊,變得更為商業化,社會上的腐敗風氣滲透到監獄系統中,原本是執法機構的監獄,現在也以金錢和關係來支配犯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命運了。
尚建國的這本獄中紀實是目前中國監獄的一幅白描,讀者在其中也可以捕捉到當今中國社會的縮影。
吳弘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