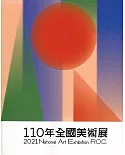序
《後民國》即《理想國》
藝術一族這個向來弱勢的少數族裔,往往遍尋安身立命之地不著,可「應許之地」(ThePromised Land)一朝不存在,生活便永遠在他方。一直有夢,想要在南太平洋海域中尋找一座與世無爭的蕞爾小島,成立所謂的「藝術文化共和國」(RAC, Republic of Arts &
Culture),作為所有苦無棲地的藝術文化工作者的棲居之所。原以為純屬天馬行空的妄想,不意卻在非常廟藝文空間與高雄市立美術館齊心協力策劃以及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經費奧援之下,突破萬難地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實現「立國」大夢。
英國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巨擘摩爾爵士(SirThomas More, 1478-1536),公認以傳世鉅作《烏托邦》(Utopia, 1516)而不朽。他依希臘文造字原理,假託地處亞特蘭提斯(Atlantis)
汪洋中有座名曰「烏托邦」的「無有之鄉」,這個虛構島國一切全憑純理性運作,因此社會、政治、法律無不完美。儘管策展人吳達坤引此典故,提出了《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的策展論述,但筆者寧視「後民國」為藝術家以藝術興邦、文化建國的宏圖所建立的「理想國」。
至今仍然不解,《後民國》這樣一個參展作者均一時之選而作品質量均精的展覽計畫,當初在通過國藝會策展專案補助的優勢條件下,遍洽中北部公立展覽機構之時,何以會苦無立錐之地。據告乃是在此岸「建國一百」、彼岸「辛亥一百」大勢所趨的政治氛圍下,辦理此展難免招徠主辦單位落入「政治不正確」的尷尬處境。然則,過度渲染其政治性而僅以政治解讀,恐怕既武斷、片面而有失公允,徒然小覷了藝術品的苦心詣旨,更辜負了藝術家與用心良苦。
兩岸主權歸屬的實情,由於盤根錯節的歷史共業不由分說,無論如何抽絲剝繭詳加鑑識,注定是越釐清越是無解的徒勞無功。所謂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由於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先行,人民自覺折衷為集體心智,所以人民難免遁形, 成為「A republic without people?;所謂的Republic of China,
則因為地理上偏安台灣幅員未及大陸,所以實際上「A republic without China」。《後民國》的主張,或許可視為老、中、青三代藝術家根據既有文脈(context),試圖從實體空間地圖製圖(mapping)的宰制,轉移到重製(re-mapping)出精神心靈地圖(mental-psycho
map)的連番作為。面對廿世紀二戰戰後出生的世代共同繼承的過去,目前落入了」either ∕ or」的窠臼,究竟如何前進未來的表態與表述。
畢竟左∕右、統∕獨、傳統∕創新等等讓一切「一分為二」慣性思維,形成的祇是兩難局面與對決態勢,藝術文化人作為人民與政府之外的「第三勢力」,又不願權宜於鄉愿地採行中間路線,進而在制約性二元思考之外,提出」neither∕ nor」、「以上皆非」的第三種替代性選項(the third
alternative)。但是將《後民國》羅列的「第三選項」,一律視為「反烏托邦」(Dystopia,又稱敵托邦或廢托邦),又是否得宜﹖畢竟,反烏托邦作為逆向思考犯映出的虛擬境界,反證的是究極理想社會的不可行,物質文明極端泛濫終究戕害精神文明,刻畫出自由民主不再、令人絕望的未來。
反烏托邦作為文學類型(genre),尤其是作為科幻小說的體裁和重要一支,的確產出了許多寓言式傑作, 如詹雅亭(Yevgeny Zamyatin,1884-1937) 的《我們》(We, 1921)、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
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 1945) 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 1948)、布萊貝禮(Ray Bradbury, 1920-) 的《華氏451 度》(Fahrenheit 451,
1953)等,均影響當代絕深。假設真要將《後民國》類比為反烏托邦主義的實踐,那麼至少該說廿六位藝術家提出的廿四組作品,顯然已擺脫了解嚴後遺症—訴諸直白激情的情緒宣洩進行正面交鋒的意識型態戰爭,不再執著於非理性的衝撞對決、非人性的撕裂拉扯、非人道的冷眼橫眉。
鑑於現實永遠不能盡如人意,所以我們需要創造理想超越現況,以便改變現實。吊詭之處是在於一但理想被實踐化為現實,吾人難免再度對其產生不滿,興起時必須追求另一理想取而代之,突破現狀開創新局。正因如此週而復始的良性循環,人類會社與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地不斷生發、演繹、昇華、與時俱進。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424/423– 348/347 BC)
藉其傳世經典《理想國》(Politeia, The Republic),主張理想社會「哲學家君王」(philosopherkings)的概念,希冀全新典範,呼籲國家的最高領導非哲學家莫屬。倘爰此理路,《後民國》即《理想國》,而在《後民國》這個唯藝術是尚的國度中,藝術家則理應當家做主。
1863 年底, 為了促使因解放黑奴而南北對峙的國家統一, 美國前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發表了著名的《蓋茲堡演說辭》( The Gettysburg Address),大聲疾呼政府應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從此成為全球共和國護衛民主的圭臬。套用此倡議,那麼在《後民國》裡,便會是「藝術家有、藝術家治、藝術家享」的民主共和國。
《後民國》的子民之所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甚且前仆後繼、奮戰不懈、愈挫愈勇,著實是因其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與過河卒子般的理想主義使然。爭了一時還有千秋,藝術之路永無止境,這是藝術人永恆的共同宿命。長夜漫漫路迢迢,藝術建國大業方興未艾,儘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不過在過去的一百多天當中,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前旗竿上《後民國》國旗飄揚,三樓的500
坪的土地上總算短暫成立《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相信此舉宣示貫徹「說到做到」的決心,已讓參與其中的所有人大受鼓舞激勵,繼續大步前行。有幸受藝術家「擁戴」出任「臨時大總統」的我,於是想感性的說:「吾願足矣!」末了便引美國現代詩人(Robert. Frost,1874-1963) 名詩《未擇之路》(The Road Not Taken) 的結語,作為這篇代序感言的小結:
我將會邊嘆息邊說道,
在某處,在許久許久之後;
曾有兩條路分歧於林中,
而我—選擇了人跡罕至者,
而結果一切截然不同。
謝佩霓
策展序
「後民國」展覽概念一部份來自小說家喬治. 歐威爾(George Orwell) 於1948 年所寫的一部經典科幻小說《一九八四》;另一部份則是對臺灣現實政經局勢與國際現況的觀察。雖然一九八四年早已經過去,
世界也未如書中一樣的改變。但卻激發筆者對未來的無限想像。我們是否準備好面臨民國百年的到來?本展覽試圖將「中華民國」─臺灣的過去歷史、當下作一個參照,進而提出一個以民國百年的未來為藍圖的虛擬國度─「後民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本展的主要目的,即是透過這樣的展覽提出對於「民國百年之後」臺灣的主體性提問。這個提問,同時企圖點出島嶼居民對於未來生活的想像,我們同時也看到臺灣當代藝術家對於當今世界未來局勢的不斷提問,透過這種多面向的軸線並進突圍出一種存在生態的活力。本展另一主軸,是以未來學(Futurology)1
的觀點來面對此一政治與歷史課題,同時談論一個充滿可能想像的虛擬(Virtual)國度—「後民國」。
另外一方面,「後民國」這個互應現實的虛構國家,藉由形態對現實與幻想兩者鏡射的深層指涉,以一個充滿未來想像的虛擬國度來敘述,並與展覽子題「沒人共和國」(Republic without
People);雙重語意道破了當下民眾對社會及政治未來方向不確定所產生的焦慮感,繼而反映出當今臺灣島嶼普遍瀰漫的一種去中心、缺乏身分認同的集體意識形態。經由實體展覽介入現實的一個干擾動作,恰恰反應了「後民國」這一展名與臺灣之間吊詭的鏡像關連:今日我們面臨到更大的形態轉變,這是一個新的、越來越不可抗拒的處境,將來也一定不容易改善。諸多不確定的危機已超越過去臺灣數百年來建立的經驗法則與現今政經體制所能處理的範疇。藝術家透過展覽作品的暗示現狀來揭示(∕暗示)某種認識上的島嶼政治理型,或許政治機器的不可逆並非單純只是歷史使命上的正義可以扭轉,藝術對於社會政治的正義使命應該在質感上與政治意圖的正確性有所區隔。因此,每一個新增加的問題都揭示著藝術的象限與現實相切的座標位置。將每個點串聯起來,也造就了「後民國」展覽的成立。
此展覽不僅從虛構文本獲得脈絡上的藍本,更體現了經由現實再現所捕捉的「真實」。「後民國」一展即是基於這個理解,提出一個「偽裝」的策略:改變體制最快的方式即是矇混進入體制中,摹仿它、干擾它、瓦解它、然後再重新建構。當然,對藝術家而言,當下就要預測未來社會的狀態,以及根據歷史與現況情勢來判斷即將發生的事,是大膽又猖狂的想像。「未來」承受太多的意外,「歷史」無時無刻在改寫,或許我們的未來就是如此。
也因為如此,這個似是而非的展覽本身變得十分有趣。
一、未來學的預言—關於自我去勢的危機
「這是一種必要的替換,一個幻影將覆蓋另一個幻影,成就一種以退為進的社會集體策略。」
當文化藝術工作者面對政府體制調控與自由主義雙向兩極進行選擇時,
接受進入體制,似乎比面對處於不明確狀況的當代思維來得容易。但這是一種雙重否定的過程;一方面否定了「當代藝術」作為核心價值的理想性,另一方面,現實早已對我們進行反撲,被機制認可外的一切在此亦被吞噬殆盡。如同體制往往意味著無所不包的系統性控制,一點一點餵養包裹糖衣的毒藥。最終還可能失去自身價值,淪為被體制收編的「順民」,自我去勢卻又無計可施。其實,我們面臨的強大敵人是來自於自己內心。永遠在邊陲中尋覓他們的主
體和身份,也讓島嶼人民處在永恆漂浮缺乏認同的集體意識形態中。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城市之間的交流遠比國與國之間來的頻繁,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已到雲端概念,諸多事務能在電腦前一指搞定。政治疆界早被打破,人們不再以「國家」這個概念來討論國際事務。跨越國界的經濟、社會互動也在成長和強化,政府也可能基於國家利益而讓渡其領土內人民之部份統治權利。取而替換的是跨國企業的成長壟斷、區域自由貿易、能源開發等攸關眾人生存的議題,傳統的政治主權觀念因此削弱。無可避免的是,我們的島嶼正面臨這些巨大改變而帶來的「雙面刃」(諸如氣候變化、產業變化與財富分配失衡等危機問題)。
以上兩大因素,將是未來影響島嶼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未來; 承受太多意外也無從預測,我們的未來也許就是如此。今天,我們將透過展覽的「偽裝策略」試圖描繪出屬於過去與未來島嶼的文化輪廓。
二、過去、當下的兩項不確定因素
母體—演化中的島嶼。在短短數百年裡我們在這裡見證種種政治學論述─時代的、種族的、國家的、文化的、地域的變遷。影響島嶼居民對於過往的留念,就像長期被殖民者一樣;自我否定往往大於當下的肯定。過去種種將島嶼牢牢綑綁,作為可能已逝的體制、文化的悼亡者,懷抱追思已然變質的正朔。結果;像是望著一面照不出自己形象的鏡子,極力認清自己的容貌。
過去的第一不確定因素:模糊的定位。
然而,「沒人共和國」就字面上的意思是:沒有人的國家,(也可以解釋成沒有人認同的國家)。構成國家的三要素:領土、人民、主權在這島嶼上都存在,但也可以說都沒有。因為歷史因素,這島嶼成為國際政治現況下特例中的特例,無法明確地被接受,經過諸多因果交互扭曲纏繞下產生一種特殊定位。長久以來,身為國際事務上缺席的政治實體,主權的脆弱也直接影響到文化主體長期被忽視。同時,「弱國無外交」的歷史教訓也不斷告誡我們。過去,
情非得已的生存之道是選邊靠攏庇蔭在各個強權之下,讓島嶼成為宿命裡不斷追求安全保護傘的附庸國,在列強的競逐中找出一條活路......。可以說,這島嶼在過去不斷承受自我身分切換的尷尬場面,以至於面臨定位模糊的錯亂。
當下的第二不確定因素:弔詭的現狀。
從後殖民的觀點來說,島嶼「民主化」過程絕非一片安詳,島嶼早期有強大的政治壓力;政治上扭曲,也有物質上的扭曲。引發一連串充滿殖民剝削歷史場景與重複暴力衝撞之惡。也因臺灣特殊的經濟環境與戰略位置,無論從島嶼內部或外部的力量,經濟上和社會上被現實洪流拉進世界的軌道中,全球化的過程導致臺商為了延續產業生命將生產線移到中國這世界工廠裡,目前暫時擱置政治爭議以尋求雙方最大經濟利益,但這些繁榮表象後面仍是問題密佈;相對於中國的以商逼政策略,島內未來的發展實際上存在諸多不確定的弔詭。而這幾十年來開放的政治情勢所激發島嶼內部本土意識的抬頭,對當家做主的渴望也更加清晰明確。
三、這島嶼如何可能?
記得小時候有一個用鏡子傳接光線的遊戲︰幾位同伴手持鏡子由外自內將陽光傳接引入室內,觀察光的行進情形,讓沒有光的幽暗地方也能照射到光線,照亮整個空間的輪廓。
自1971 年退出聯合國以來,
島嶼便失去參與國際社會的實際地位,成為被世界忽略的影子國度。數十年下來,島嶼在強調經濟發展的現實主義掛帥和華府的東亞政策影響之下成為世上舉足輕重的「科技島」。而「文化藝術」只在節慶時被政府拿出來點綴亮相一番。過分重視經濟發展的畸形思維反而讓生活在島嶼上的居民面臨缺乏國家認同的自我否定,淪為無法被看清歸類的身分。過去,政治藝術在島嶼上缺席的狀況慎為嚴重,除了解嚴後的曇花一現,千禧年之後只出現在少數專注此議題的藝術家創作脈絡。筆者認為這並不是臺灣藝術家對政治議題失去興趣,而是被總體機制營造出來的氛圍模糊焦點而噤聲,熱情成為現實然燒後的餘燼。失去抗爭目標後,現實主義襲來的強大力量往往讓人挫敗。倘若,藝術創作中的政治(議題)討論不再熱烈,藝術家也只能退後思考個人經驗與形式的其它問題。討論著普遍性原則的美學問題或是哲學思考的個人體驗,缺乏自身的政治脈絡與歷史深度。然而如果說缺乏歷史脈絡是島嶼的藝術本質,那更深層的狀態是什麼?是符號不停地流動,抑或是主體性提問永遠地匱乏闕漏嗎?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好的策略總是出現在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透過藝術讓我們認清自己的容顏;生活在哪裡,就該面對哪裡的問題,用藝術文化去面對真實的情境,不啻也是突破當今島嶼困境的方式;反之,藝術論述亦不需迴避政治與歷史的難題,建立於事實的文化主體論述絕對有其必要。
四、藝術家眼中的島嶼
「後民國」展覽邀集了跨越三個世代共二十四組(二十六位)生長工作於這島嶼的藝術家參展。計有:楊茂林、陳界仁、吳天章、梅丁衍、姚瑞中、瓦歷斯. 拉拜
、王俊傑、涂維政、陳浚豪、周育正、崔廣宇、蘇匯宇、陳擎耀、陳萬仁、邱昭財、饒加恩、黃海欣、葉廷皓、余政達、杜珮詩、陳敬元、高雅婷、萬德畫會(蘇育賢、黃彥穎、江忠倫)。本展跨越三個世代藝術家的組合,交織出島嶼數十年來不為人知的歷史厚度和縱深;儘管同樣透過政治和時代社會之間的關連來討論,卻產生出不同的觀點與文化厚度。面對「在地化」與「全球化」問題結合脈絡之下,展出藝術家們分別就國族、身份認同、政治、歷史文化等龐雜的認知議題與過去、當下、未來的各種角度切入,藉由藝術語言的轉進側擊面對著各項關於島嶼的符號與象徵系統。
過去,創作者最初受到西方教育訓練下的影響,
用一種移植摹寫的方式來呈現作品,直接移植對西方「現代性」的擁抱,然而這樣的形式移植,也激發隱藏於臺灣現代化過程背後的文化焦慮或是草莽底層醞釀的社會能量。激情造就了第一波政治藝術的高潮,從早期對社會的激情進入到中間輩關注的從藝術與社會的脈動關係;冷靜中隱藏人文關照和對社會不公義的嘲諷,結合得如此緊密又那麼疏離,延續激情後的藝術運動。而新生代創作者受到大量資訊衝擊,開啟新的自主性語言系統,網際網路所打開的就是這類型社會圖像的重建。千禧年後崛起的創作者,成長在最開放自由的時代,未受到物質及社會的扭曲,可說是最富有創意的一代。他們大多接受過正統學院訓練,藝術語言更加成熟,更關心作品內在呈現的準確性。作品語彙往往經過精巧轉折打到痛點,借力使力羅織虛構各種語境情節,常常令人會心一笑。這類作品往往結合藝術主體性與藝術自主性的現代性美學議題,並反思屬於島嶼共同的生活記憶與文化面貌。
我們的歷史是經歷多次不同文化融合的「過程」,在這之中的對應方式,能檢驗的只有同時把時間軸線拉大宏觀地去看待此一「過程」,以及把焦距調近,以「微觀」的方式去看待某單一事件。這些放大與特寫的拿捏,是展覽中藝術家描繪出島嶼拼圖最困難的部份,他們將以自己的觀點來詮釋他們所認為屬於這島嶼的「路徑圖」。
五、「後民國」─虛構與真實的縫合
「後民國」這個虛構的主題本身即帶有積極的政治目標,這展覽討論的是這島嶼處在於無法被歸類的範疇跟模糊的界限,而「現狀」本身就隱含著時間的遽變。
如何透過「後民國」這樣一個縫合真實與虛構命題的展覽呈現出島嶼文化脈絡?如何重新思考新世紀的島嶼該呈現什麼樣的身分認同跟文化自覺?本展做為呼應當代政治態度的藝術調查。因此,策展團隊將為本展在這個政治美學崩解的年代裡提供一個短暫卻積極可行的轉進策略:
一個對應真實卻只在展覽期間才存在的自由國度!某程度上本展提供了藝術家們如同政論節目能夠肆意妄為無賴不負責任的「場域」。藝術家化身為「名嘴」自發地對於「當下」做出戲謔的回應。藉由作品的陳述,機巧的指出某種彼此都心知肚明,卻說不出口的曖昧狀態。讓作品的存在除了在敘事層面外得以反饋到另一個真實層次,體現「藝術在政治當下」的有效性。這樣後設的「逆」策展也正好呼應了前述本展的對於「後」的命題。
因此,面對島嶼將來的危機與轉機,諸多問題紛擾之下的思索。當政客們總是繳出讓人失望的成績單時,我們且看藝術家們如何面對新世紀的嚴峻考驗,描繪出屬於「後民國」的特殊標記。提出一條可能的前行路徑,揭櫫島嶼迎向新紀元的大航海時代!
六、結語
綜上所述,所謂的「後民國」展覽論述,已慢慢開始浮出地表:我們提供一個短暫的只有在展覽其間才存在的虛構國度—「後民國」。最美妙的是,它不是「中華民國」(R.O.C)
也不是「中國」(P.R.C),它只存在於一個藝術的虛構認知框架之內,同時卻與原有的真實世界縫接重疊!而這展覽操作模式恰如反應「島嶼」的自身,透過藝術的創造力提出一套可以與現實共存(分享)的價值,映射在它自己名字之上。
我想,最應該看這展覽的,是脫離於「統一」和「獨立」等狀況外的島嶼主人—臺灣全體人民。
吳達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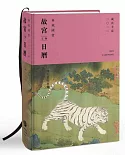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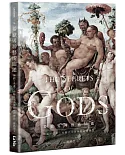





![現代美術[季刊]NO:200期[110/03]](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8%2F92%2F0010889265.jpg&width=125&height=155)







![2021桃源國際藝術獎[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90%2F14%2F0010901421.jpg&width=125&height=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