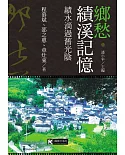遠方軍號聲
一篇文章、一本書,自己看久了就生厭,一天莫名其妙地將它交給副刊編輯或者寄給出版社,要他們看看到底如何。想不到評價不錯,不久文章「見了報」,書則出版社的負責人來信表歡迎,說已排定某時出版,那時即使有點後悔,不過鬧到這個田地,心想只好算了,就讓它順其自然吧,心裡還是有點不安。所以當自己對一篇文章生厭時,最好的方法是立刻扯了撕了,勿留穢名天地之間,一本書厚度的文稿不太好撕,但焚之燬之,還是有辦法的。
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困難,不是說「敝帚自珍」嗎?每個人對自己的東西(包括自己的孩子),都有護短的心裡,說是生厭,文章一旦在副刊登出,或者以一本小書的樣貌在書店的櫥窗出現,看起來也不至於那麼可「厭」了。這是為什麼李卓吾把自己的書取名叫《焚書》、《藏書》,並沒有把書真正給「焚」了「藏」了一樣,張岱說:「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可能道盡了其中的意思。
這本小書收了幾篇由我「家族」引發出來的故事,原本只是「私事」。我與我家族的成員,都是小人物,包括我書裡寫的我童年周圍的一些人與事,嚴格說來,在這個「大時代」裡都無關緊要、可有可無,也可說是「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的,本來沒什麼可寫,也不想寫,想不到竟寫了。我後來到台北闖蕩,教學上庠,也經歷過一些以前想不到的經驗,所與之中,有一些可以稱為「國之髦士」的重要人士,那些人物大多裝腔作態,很少以真面目示人,更不要說其中還有爾虞我詐的事端穿插出現。與這類人物相處得處處提防,時時緊繃,瞻前顧後,左支右絀,比較之下,還是小人物、小故事接近人情,而且花開花落,自成季節。
大陸青年評論家張彥武(筆名燕舞)看了我的小書《同學少年》之後,謬加贊許,說是台灣「眷村文學」的代表作。我去信表示不同意,我的《同學少年》其實不是為眷村而寫,只不過內容有幾篇跟眷村有關,那是我曾生長的地方,我想捨棄也捨棄不了的。我在與他書信往來的時候,心想我也許可以把我在眷村的見聞單獨寫成一本書,我在出版了《記憶之塔》之後,開始陸續寫這本書裡的文章,也有小一部分,在《記憶之塔》之前已開始寫了。
這本《家族合照》,寫的是我家的事,裡面出現的眷村生活要比《同學少年》要多,尤其是第二輯裡面的幾個人物,都是與我童年的眷村生活有關,第三輯中的幾篇,慢慢向外面拓展開去,但再遠,距那個早已根植在內心的「基地」,還是無法離得太遠。義大利名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4)有次說:「長久以來我一直想拍一部關於我老家的電影,我是說,我出生的地方。但有人向我提出異議,說我根本沒有拍過別的。」再偉大的藝術,其實還是在自我的小範圍裡兜圈子,就跟《西遊記》裡的孫猴子一樣,自以為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周遊無限了,但在如來佛看來,還根本沒超過祂的手掌心呢。因此我想了想,燕舞的說法也不見得不正確。
燕舞曾來信請我描述我以前住過的地方,怎麼說呢,那種事確是說不清的,何況只用短短幾篇文字。我以前住過的眷村已埋入歷史,現在一點痕跡都沒有了,這世界大部分人沒有歷史感,什麼事一埋入歷史就表示沒人再注意到甚至意識到,對他們而言,那就等於不存在了。我的家庭很小,人都是平凡的人,當然也各有興衰起伏,但與世上一些大開大闔的人比較,總缺少精彩可言。我少年時住的眷村也不大,當它最盛大輝煌的時候,也只不過六、七十戶,後來雖然有人遷出也有人遷進,而總戶數不見增反而逐漸減少,這跟它處於比較不繁華的東部有關,還有它是「外省人」的聚落,它必須面對在台灣所有外省族群凋零分散的共同命運。
我想起顏色。當我少年時,宜蘭的天空總不是怎麼晴朗,我腦中的顏色是黑白的居多,偶爾加上一點灰色與褐色,都低暗的很,唯一比較有亮度的色調,是土黃與青紫的交錯,但也亮度不足。那兩個對比又神經質的顏色好像與我關係深遠,有時填補在我童年生活雲與山之間的空隙,也填補在我周圍戶與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空隙。所以我面前的這一幅畫,像一幅色調以黑白為主的木版畫,雖然線條嚴密,而人的關係是疏離的,情緒是緊張的,缺乏橙黃、大紅,還有成片連綿的綠與坦蕩無垠的藍,對我來說,那些才是真正的顏色,愉悅又大快人心的,我覺得一個自足又飽滿的農人或者一個懷有理想的知識份子,該有那種顏色,但它們很少、幾乎沒有在我少年時的畫中出現。幸好還可從另外一點來看,缺乏形成渴望,渴望引領你用以後的一生去尋找。
嗅覺倒是飽滿的,眷村雖小而氣味豐富。只須幾分鐘,就可走過眷村的所有門戶,每當下午放學,也是各家煮晚飯的時候,各種特殊的氣味從空中「發射」出來,如同陣地的子彈炮火,令人躲也無處躲。菜色各家不同,像吃火鍋都用共同的「鍋底」一樣,每家的鍋底同樣是很不純粹的花生油,公家發的花生油多雜質,必須用大火猛「爆」才會減少它的「油哈」味。用廉價油爆出來的菜,辣的會更辣,酸的會更酸,臭的則會更臭,眷村的居民的鼻腔早已習慣各式強烈的氣味,最後因為刺激過多都變得無動於衷了。人的五官是連在一起的,鼻腔的折磨連帶使得五官的功能俱失,至少大打折扣,藏在更深的人性之中的「五情」與「五蘊」也都一樣,當人生活在有色彩的世界卻分不出色彩,久而久之,他視覺裡就沒有色彩了。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或許就是這個道理。
平台上五色、五味甚至人的四體雜陳,所有東西就大剌剌的擺在那裡,初看起來光怪陸離,但只讓它那樣的擺著,時間久了也就默默無聞了,沒人把它串聯成垂直的、有意義的故事,從思考層面來說,眷村是個水平的世界。偶爾有人發了點癡,產生了點幻想,想要把世界弄得「不一樣」一點,像火花在夜晚閃爍,短暫的光敵不過籠罩全局的黑夜,不一會兒也就消沉了。不過眷村的世界也不見得真小,也會有大些的事發生的,諸如生與死、突發的疾病引起的改變,還有堅持與背叛的故事、戀愛與失戀等等的,都可以算是大事了。然而所有的事都發生得太快,有一段時候又發生得太密集了,讓人很難全數反應過來。像看到遠方閃電,聽到雷聲總要一陣之後,當人反應過來了,事情早已過去,又彷彿幾滴雨落在滾燙的柏油路面上,雨滴儘管很大,也一下子就不見了。
眷村對大多數小孩來說,更像一個大而化之的母親,她生了太多子女,以致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她像是供應大鍋飯的公共廚房,你來了任你吃,又像供應熱水的公共浴池,你想泡多久就多久。其實大鍋菜一無可吃,澡堂的水又其髒無比,你不吃不洗她也不管你,對她與你來說,雙方的關係都自由極了。由於我與我住的眷村在身份上有「隔」,我不是這個村子登記有案的正式居民,我只是寄居在二姐眷村的家中,那裡沒有我的空間,也沒有我的配給,這個在別人視為母親的眷村,我也用母親的意象來看她的話,她只能算是我的後母,她並不會對我刻薄,但對我確實更不關心。說也奇怪,當時我很喜歡我尷尬的身份,我比起其他的孩子,更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這樣卻讓我更加左右逢源,至少感覺上是。表面的困頓給了我更多的機會,我看起來什麼也不是,卻表示我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而且不用擔心失敗。對我而言,什麼地方都是結束,也是起始,只要我心裡想要,沒人能阻攔我。
羅東有一個軍營,在鎮西的一個叫北城的地方,那裡有一個日據時代留下的神社,通往神社的道路兩旁,有秩序的排著刻著「奉獻」字樣的石燈,再旁邊就是成排的俗名叫做油加利的大葉桉樹,軍營就在旁邊。因為不是要塞,小鎮也無險可守,所以軍營的駐軍並不多,曾經駐過一個輕裝師的團部,與重裝師相較,挺多一個加強連的人數罷了,我記得我二姐夫做副團長的時候,曾在這兒短暫駐防過。軍營沒什麼特殊的,唯一可記的是軍號的聲音。所有軍營無論大小,都是用號聲來指揮,軍號沒有像一般管樂器的按鍵,彷彿把銅管隨便扭曲幾道,把出口敲成漏斗樣,加上個吹頭就成了。軍號手沒有識譜的,好在軍號只有Do、Mi、Sol三個音,他記譜就用阿拉伯數字123來表示,如果是低音,就在數字下點一點,簡單的不得了。
北城離我們的眷村很遠,但以前世界寧靜,早晚還聽得到軍營傳來的號聲,只Do、Mi、Sol三個音,也能組成繁複的故事似的。晚上十點,大多數的人都忙完了一天,遙遠的軍營傳來忽明忽暗的熄燈號,整個多紛的世界就也都要埋入昏睡的黑夜了,但我聽了總是睡不著,熄燈號裡藏著睡眠與死亡的暗示。秋冬之際,東北季風在空中呼嘯,裡面夾雜著從五結那邊傳來的海濤,海濤十分有節奏,從未斷絕過,但不細聽是聽不到的,晚上則可聽得清楚,證明無聲其實藏有更多的聲音。已經有幾萬年了或者幾十萬年了吧,海浪拍打著沙岸,一刻也沒停息過,那時還沒有人類的文明呢,我想,濤聲中一定藏有關乎全世界或全宇宙最根本的秘密,卻從來沒有人注意。
諸如此類,在我人生的那一個時代,一切彷彿是靜止的,卻都憂心忡忡的存在。不時的幻想使我對乏味的眼前不覺慵倦,未來的生活,包括意志與命運的爭鬥,性愛的憧憬、死亡的預感,更多繁複的想像,都從那裡開始。世界末日也從那裡開始,只是到今天還沒真正的結束。
不經意的事反而重要,一件事看起來很短又無聲,但不應忽略,也許就是一個人的一生呢。當然只要地球與太陽仍保持同樣的距離,而且維持目前自轉的速度,所有事情是還要繼續下去的,淹滅了沉淪了的小事有一天會再從漩渦外浮出,消失了的人影,也會再度出現,到時看你要如何對待。我讀陳明克的詩,裡面有這樣的句子:
停停走走的車流中
我小心控制車行的速度
蒲公英等了這麼久
絨毛輕輕顫動
就這麼一次
不要這個時候下雨
讓蒲公英飛起來
從我無法離開的公路
我喜歡這首詩,因為與我此時的心情相同。
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寫於台北永昌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