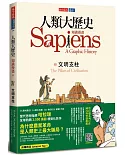導言
文化中的生活,生活中的文化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
社會文化分析的核心問題,是人的生活。更準確的說,是生活中的文化、規範、價值、行動、衝突等等。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所接觸到的社會、文化,包含不同的方面、部門與層次;它們並非相互分割,而是彼此扣連。更重要的是,各個部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通過日常生活而互相交織,構成生活中的社會環境。社會文化分析嘗試捕捉的,是生活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生活。這也就是說,社會文化嵌於生活,而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嵌於社會、文化之中。社會文化分析對於社會、文化、生活三者之間的界面,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互動,特別敏感和好奇。大概就是這個原因,社會文化分析的選題從來都是相當廣泛,更不會自我約束,將討論局限某些範圍之內:源於生活的議題帶動社會文化分析的討論方向,同時也不停地改變研究員切入問題的方法與角度。
長期以來,社會文化分析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要面對最為人所熟悉(而因此就往往會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細節,並給我們揭開被常規掩蓋的利益、權力關係與矛盾。雖然這樣說並不表示文化、日常生活沒有其自主性及獨特的運作邏輯,更不是認為文化生活的各種價值、習性、儀式都是依附於經濟、政治的表象,或是其他更為決定性的社會結構或制度的外殼;但在分析、討論的過程之中,社會文化分析通常都不會只停留於文本或現象的描述和分類,而是要把另有一個「現實」、權力關係、未為人所察覺的社會過程呈現在公眾面前。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文化分析不能避免地會不甘止於提出學術的問題,而是對現狀有所批判。因此,社會文化研究經常包含了一些政治經濟學或是對權力關係的分析。研究人員在提出觀點
、構成論題,和選取研究與討論的對象時,背後多少總會有一點政治經濟學的、針對不同形式與性質的權力關係的批判。
而批判的意義,在於超越。超越並不只是建構(或反建構),也不只是想像(或逆想像);論述的威力並非源於論述本身,而是它能扣連到社會與人的生活,產生一種物質性的轉化,令不是以「物」的形式存在的論述,在社會上產生影響。亦即是說,有效的社會文化文析都會切入生活,或多或少干預了物質意義層面上的社會。沒有認真處理文化、論述、日常生活的社會性,忽視了社會機制對改變權力關係的重要性,則所有反建構、逆想像,恐怕都只會是一場自我想像的「鬥爭」,未有進場的競賽。
本文集所收文章,曾於第三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2008年11月1日)上宣讀,經修訂後編輯成書。這些文章的特點有二。一是它們所接觸的題目及討論範圍頗為廣泛,涉及不同的社會部門與生活的各個方面。除近年討論得較為熱鬧的話題如身份認同、城市社會運動、媒體與公民社會之外,還有接觸到社會生活中不同層次與維度的問題──由父母育兒對策到公共知識份子,成衣工人的處境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殖民性、地緣政治與香港研究。這裡所涉及的研究旨趣,不止關乎宏觀與微觀的不同層次、當代與歷史的不同時間維度的現象與課題,而且還凸顯出各項研究課題與討論架構多元重疊的特點。例如蔡寶瓊所報告的14位成衣工人的生命故事,矛頭直指新資本主義文化的大趨勢,但同時又將她的討論放在工人的日常生活環境之中──工作、勞動過程、工藝精神、以及僱傭關係與概念的變化──並且有力的呈現出全球化與新資本主義如何磨蝕了舊有的社會關係,衝擊著工人的自我身份建構。新資本主義文化所帶來的衝擊,嵌於勞動關係,通過生活中的細節(文章的焦點在於工作的生活環節),產生作用。
又舉另一個例子:蔡穎儀走進尋常香港家庭,展現當前整個社會於日常生活層面上,最引人議論的問題:育兒對策與風格。她的文章分析了家長與子女的互動和權力關係,但更重要的是,字裡行間同時也提醒讀者要如何思考來自家庭以外,支配著所謂的「快樂成長」、「親子」的育兒安排。
二是社會文化分析的經驗與實證基礎。這裡所指的實證基礎,當然並非指狹窄定義的實證資料。本書內各位作者所採用的方法並不統一,有的引用問卷調查的統計資料,有的翻開歷史檔案文件,有的以政策文件或學術文獻為本,也有作者進行深入訪談,或進行深入的個案分析,總之各自按其研究的題材與需要回答的問題,選擇適合的方法與材料,來支持其分析與論點。這一種以經驗與實證材料的基礎的社會文化分析,強調的是交叉佐證,要求分析有其客觀基礎。
必須強調,如前面已經提到,客觀基礎的意思並不是只認同統計數字或量性的資料,而是交叉考查,從不同方位來檢查研究與分析的準確性。或者有人會認為,這一種對準確性的重視,背後似乎已經假設了有所謂「真實的」與「不真實的」二分法和二元思維,而且更先設了「真實」的存在,在追求所謂客觀與準確性的時候,封殺了不同演譯的可能性。讀者有這樣的懷疑,可以理解。但我們不是提倡天真的實證主義。這種實證主義假設社會是穩定而且真實存在的。我們重視實證,但並不追求單一的真相。我們認為社會真實是在複雜的互動以及權力關係中呈現,所以是亂中有序,亦可修正改動。因此我們強調不同的演譯亦需要各自有其論證的基礎;閱讀、演譯、建構等等從來都不是──也不可能、更不應該──是一個「隨心所欲」的過程。一種理解、分析應保留它的開放性,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但我們卻不可能因為容許有不同演譯的可能性,而放棄研究方法上嚴謹的要求。如何在研究方法、分析材料上的交叉佐證做得更好,是社會文化分析的一大挑戰。事實上,這個問題對自覺要提出批判的社會文化分析尤其重要。試問缺乏嚴謹的資料搜集、論證、分析,社會文化分析又如何可以批判及超越現存的論述,並且可以成為在學院以外跟市民大眾對話的知識。它本來的承諾之一是保持一份公眾性,研究的成果能夠成為與社會對話的材料,而不是小圈子裡的自由想像。
本文集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的四篇文章以不同的介入點來探討後九七的身份認同問題。張炳良以政治科學學者及身在局中的政治人的身份,回顧1997年前後香港的政治與香港身份的變化。可以想像,他的一些想法──正如其他作者所提出的結論一樣──不乏可以商榷之處。但重要的是,他的分析凸出了香港身份的歷史軌跡,為有關的討論提供一個歷史背景。謝均才參考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展現出後殖民時期的國民教育或愛國教育,是如何通過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策略行為、互動所打造而成。他的分析不單指出民族主義的政治與情感能量,能將市民大眾歸於其下;更有趣的是,連反對力量亦要服膺於「我們都是中國人」的大前提,需要選擇在這個框架內的一個位置來發言。馬傑偉、馮應謙及林萃光既談後北京奧運的香港身份認同,同時他們在過渡期間對這個課題的研究的反思。他們由1996年起先後進行了七次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電話調查,在2008年10月(即發生毒奶粉案及舉辦奧運之後)又再有新一回調查訪問。另外,在2007年又以香港電視播放國民教育宣傳短片為題,進行了焦點小組來收集材料。他們的觀察與分析心得是,港人對國族認同一方面會受到情感因素的影響,但很快又會因理性的實用思維而另有看法。在他們眼中,這正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特點。而徐婉詩寫香港記者的中國故事,選取了很獨特的研究對象,將分析焦點放在個人、敘事、時空與身份的互動之上。她分析了受訪者如何界定自己為香港記者,並為這個身份賦與特有的意義。
第二部份是城市社會運動,三篇文章均涉及文化與社會抗爭的連繫。谷淑美談的是城市保育運動的文化政治,以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兩次抗爭為案例,分析社會運動如何把官方記憶重整,再而建構具備新的意義的空間。葉蔭聰同樣論及以上兩次抗爭,但他的重點不在於事件,而是「本土行動」本身。他的文字充份反映出一份反思性,將整個運動如何重整主體的位置、建構「自由空間」、充權與體現民眾能量,展示於讀者面前之外,亦有反思建制對抗爭的制約,令新的訴求與行動被邊緣化、孤立。梁啟智探索城市社會運動本身的結構失憶,通過重新整理與分析九十年代九龍灣麗晶花園事件,反思城市社會運動本身的不同可能性,同時也檢討得失。他以回顧、比較的方式,道出抗爭的歷史傳承的重要性。
第三部份以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為主題,探討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陳韜文和李立峰處理了一個研究當代香港社會不可能不正面面對的社會現實: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在香港人及香港社會留下一個深刻的烙印;談香港政治、社會記憶等,總會扯到這個題目之上。事實上,每年六月都有大量港人參與記念六四的活動。他們以一個媒介、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三者互動的分析架構,探討為何六四事件會在香港形成穩定的集體記憶。陳韜文和李立峰在分析六四事件作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時提到,這份記憶並不只是回望過去,同樣重要的是面對未來。傳媒對公民社會所能發揮的作用,從來不成疑問,但梁麗娟在分析公共廣播在香港的發展時,則指出了本地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有所欠缺。公共廣播作為一種社會理想之能夠成功,有賴民眾的積極支持。但現時在香港的情況,則只停留在公共領域內的討論,而未能有效地與公民社會建立有機的連繫。而在大環境的轉變下,公共廣播能否有效推行,可謂前途未卜。陳智傑、吳俊雄和馬傑偉對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互動,有進一步的闡釋。他們在2008年訪問了10位活躍於本地學術、評論、文化、社會運動界的公共知識份子,探討他們在公共領域裡的活動、空間,也看看他們如何以介入社會的方式,來書寫香港故事。
最後部份所觸及的課題,從不同層次、領域去探討不同形式與性質的權力關係。前面已經簡略介紹了蔡穎儀與蔡寶瓊的選題,在此不再重複,只想補充一點,就是儘管她們分別以家庭、工人的生命故事作為討論的單元,但在分析的過程中,卻能凸顯到這些生活上的問題,嵌入社會制度,連繫到更宏觀層次的議題(對「理想父母子女關係」、「親子」的定型,到新資本主義文化)。呂大樂和張少強分別探討「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香港研究的「消失」,則由宏觀的議題回到貼近身邊的權力關係。前者通過翻閱政府檔案,重新思考七十年代港英管治的殖民性,不但質疑過去的研究對這方面的忽視,更認為只有重新瞭解殖民性及殖民政府,才能夠更全面的掌握當時的香港社會歷史,及很多香港人成長經歷的社會歷史背景。後者以香港研究的文獻為材料,以地緣政治來分析它的發展路徑,並提出一個值得討論的論點:長期以來,香港研究往往以一種「正在消失」的狀態弔詭地存在。他認為我們要發展香港研究,便必需要急謀新的自我空間與出路。
社會文化分析作為香港研究的其中一環,必須回應與介入社會,才能繼續找尋空間與出路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