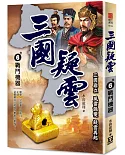序
張愛玲是怎樣煉成的
今年春天的某個上午,一如往常被「囚禁」在電腦前,突然接到區號是石家莊的電話,一個中氣十足的聲音說,你好,我是張愛玲的堂弟。
我首先是驚奇一下,當然也有點半信半疑,但還是可以想像,幾個月來一直在《燕趙都市報》上開專欄,講述張愛玲的親人們的人生,張家祖籍正是河北,那麼,招來一個「張愛玲的堂弟」,就不足為奇了。
關鍵是,張愛玲的堂弟找我幹嗎呢?雖自認為下筆謹慎且充滿善意,但既有的經驗告訴我,被寫體的感覺,和局外人的感覺,往往差了十萬八千里,局外人覺得無傷大雅的軼聞,在當事人心中,沒准就是諱莫如深的陰影,難不成,這位也是「尋仇」來了?
我還在細細揣度,便聽見那邊熱情的聲音,說,我要謝謝你,謝謝你為我十一叔說了句公道話,我看過的關於十一叔的文字裡,沒有誰提到他是愛張愛玲的,謝謝你看出這一點。
「十一叔」這稱呼,讓我想起《胭脂扣》裡的十三少,那年頭大約都是按照族中排序來稱呼,如今想來,一個交際場合要接觸到那麼多數目字,一定讓人暈頭轉向。不過,這位「十一叔」倒是指向明確,一定是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我曾寫到他和張愛玲之間那千瘡百孔千轉百合的愛,彼此默契的恩怨。
果然,這位來電者,張允儻先生,正是和張愛玲同一個曾祖父的堂弟,張志沂是他的堂叔,他幼年也在上海,六歲那年,和家門裡另外兩位兄弟去張志沂家拜年,每人得了一百塊銀元的壓歲錢,在當時,這是一個不菲的數額。
那是一九四二年,張愛玲早已搬走,他只見到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大家都喊他「tan先生」,他始終沒鬧清楚那個「tan」應該是哪個字,隱約感到是個諢號,好像是在嘲弄張子靜的斯文孱弱。
他的印象中,張志沂是個很有才華的人,而堂嬸孫用蕃也不像張愛玲書中描畫得那麼刁惡,是一個溫柔的知書達理的女人,當然,各人有各人的角度,這都無所謂,但沒有人看出張志沂對女兒的那份情感,讓他覺得很遺憾。
他說,張愛玲離去之後,她的房子仍然保持著原有的擺設,誰也不許進去,連對孫用蕃都是禁區,只有張志沂沒事時就會進去坐坐,發上一會兒愣。
張愛玲的文章中曾說,孫用蕃把她的東西都送了人,叫囂著就當她死了,但對於七十二歲老人張允儻先生提供的這個細節,我還是決定采信,他沒有必要對我撒這個謊,而張志沂對女兒的心情確實如此矛盾,他很有可能一方面任由妻子將張愛玲的東西送人,另一方面,又獨留一隅,獨自品味。
一九五一年,張先生最後一次來到十一叔家,卻在巷口看見十一嬸正在賣古董,見到他就說,別去看了,你十一叔現在太慘了!那時,張志沂已經家徒四壁,極度落魄,之後不久,張允儻就搬離了上海。
關於十一叔的往事,張先生就留下這麼些柔和而又恍惚的記憶,他似乎有些抱歉,覺得不能為我提供更多,說族中還有一位張輔合先生,現居鞍山,對張家往事特別知情,還曾編過一部家譜,他告訴了我張輔合先生的電話號碼。
我遲遲沒打那個號碼,主動跟陌生人聯絡,我總有些心理壓力,不知道對方性情如何,手邊是否忙碌,是否願意跟我交流,直拖到初秋,某個早晨,對自己說,好吧,今天一定要打這個電話了。
與張允儻先生的熱情不同,張輔合先生的聲音平穩而從容,說起張家往事,彷彿腦子裡就有一部紀年,不,紀年還不夠,他對那些細節,細節之後的人情世故,亦能娓娓道來,聽他說話,如對這明晃晃的秋天,如觀略略泛黃但韌性依舊的書卷,不由得要屏息靜氣。
談及愛玲父親與姑姑之間的那段官司,張輔合先生道出些內情。按照張愛玲的說法,她祖母死後,她姑姑和父親便跟著異母兄生活,直到張愛玲的弟弟出生,才分了家,各自過活。可是那財產分得頗不公道,核心是一套宋版書的歸屬。張愛玲的父親和姑姑聯手,一道將她伯父告上法庭,原本是個十拿九穩的官司,但最後,張愛玲的伯父贏了。
張愛玲她爸臨陣反戈,撇下妹妹,倒向異母兄,繼母孫用蕃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說起這樁恩怨又是一堆車□轆話,不管怎麼說吧,張愛玲伯父張志潛昧下弟弟和妹妹的財產,這一醜惡行為是坐實了。
我曾與一位張氏家史研究者談起這個,他站到張志潛立場上,氣咻咻地說:「幸好沒給他們,不然也是送進當鋪。」他有點意氣用事了,倒是張輔合先生說得清楚。
這批宋版書,原是張佩綸用李鞠耦的嫁妝,從前任舅子那裡買來的,辛亥革命時,舊日的貴族從京城出逃,這批書輾轉落到了於右任手中,看著都沒可能再回來,塵埃落定之後,是張志潛寫了信去要,這批書等於是失而復得,而張志潛功莫大焉。
張志潛向來作風強勢,照顧家人,承擔祭祀,編印父親著作,有典型的家族中老大的做派,他決定留下這些書,既強詞奪理,也自說自話,卻不見得就那麼黑暗骯髒,確實有珍惜父親遺物的緣故,經濟價值倒在其次,上世紀八○年代初,他將書一股腦兒捐獻給了上海圖書館,那是個讓人放心的去處。
雖然這不足以讓我認同張志潛的做法,但對他的形象有所改觀,生活總有源源不盡的層次,須得一層層看下去。
那年,張愛玲「考證」出李家跟寫《孽海花》的曾樸的交情,感到很得意;如今,跟張家兩位老先生談話,能得到這一鱗片爪的細節,我也很高興。它使我穿越張愛玲筆下那清楚決絕的親情世界,看到生活的混沌與豐富,而追問這個,也是張愛玲喜歡幹的。
她的口號是要從傳奇裡看普通人,又從普通人身上看傳奇,她習慣於嚴格地寫實,唯恐有脫離了生活的荒腔走板。只是寫到自己的家族,儘管力作公允,還是難免帶點偏見,我這樣熱衷於探佚,我想她是會贊同的。
而我對於張愛玲的家事如此熱衷,則因為,張愛玲所以能成為張愛玲,才華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在於她有那樣一個滄桑堆積的家族背景。
她初露崢嶸時,傅雷這麼形容廣大讀者的目瞪口呆,「太突兀了,太像奇蹟了」,後來胡蘭成初讀她的小說,也有似真非真的魔幻之感——她那一手犀利又華麗的文字,實在不像出自二十出頭的女生之手。
不過,天上或許可以掉下一個林妹妹,卻掉不下一個張愛玲,她如此早熟,跟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有關,人來人往間,成就多少世故人心,我自己就是通過親戚間噪噪切切的閒言碎語開始閱讀理解人生的。她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張佩綸,曾外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鴻章,隨著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變故,昔日的輝煌已經變成「蹉跎暮容色,顯赫舊家聲」的慨歎,但正是那夕陽餘燼,照進張愛玲的字裡行間,如飛金走彩,韻味無窮。
《金鎖記》裡七巧的原型,張愛玲稱作「三媽媽」的,是李鴻章的孫媳婦;《創世紀》裡紫薇的原型,是張愛玲的姨奶,李鴻章的小女兒;《茉莉香片》裡的聶傳慶,很有些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的模樣兒,《花凋》裡的鄭先生,那個「酒精裡泡著的孩屍」,擺明瞭就是張愛玲的舅舅黃定柱,據說小說出來後,這位舅舅大發雷霆,說,她問我什麼,我都告訴她,現在倒在文章裡罵起我來了。
寫小說的張愛玲,就有這種見佛滅佛的狠勁兒,在旖旎的文字間殺伐決斷,真得用她自己引用過的詩句:靜靜的殺機。
不過,若她的家族,只是作為她擷取寫作素材的自留地,那麼,她跟自己的被寫體之間,總歸是隔了一層,她的家族對她更深的意義是,起頭就影響了她的心靈,她呼吸感知著那種氛圍,形成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父親的溫度和遺少習氣,母親的激進與矯情,姑姑的真實和冷清,弟弟的可愛與軟弱,隨著時代的翻雲覆雨,都推到了極致,張愛玲一路走來,遇見這樣的親人,才有這樣的一個她,和這樣的一些作品。
湯瑪斯.沃爾夫說,每個作家的作品,都是他(她)本人的自傳,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她)本人的心靈史。回望張愛玲的家事,對於更深刻地理解張愛玲,是有好處的,我夢想通過她的親人,還原一個張愛玲的前世今生——別急著嘲笑我,我也知道是癡心妄想,我哪裡能夠做到還原呢?不過是用我自己的心,照一照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