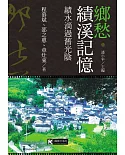推薦序
詹宏志
我坐在群山之中的環流台地,一字一句讀著陳俊志送來的書稿清樣,這裡離台北的喧囂十分遙遠,遠到像在不知名的外星球一樣。清晨露寒料峭,但我的心底忽冷忽熱,時間空間也不斷更替迭換,有一刻我彷彿回到冬曰雪封的紐約,另一刻我又回到盛夏熾熱的台灣鄉間……。我的閱讀心情也不平靜,有時候我心痛地想:「連這個你也說出來?你真的很勇敢,但太苦了吧!」有時候我卻情急得想大叫:「俊志俊志,你在幹什麼?你把好好一個故事都糟蹋了!」
讀完之後,我卻掏空虛脫一樣,稻草人似的呆坐在那裡,好像把情感感覺情緒思緒都耗用盡了,一時三刻不適宜回到人間,更不適合議論思考……。
這是什麼?這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這當然是一本勇敢而哀傷的書。
它勇敢而哀傷,我卻不能倒過來說它哀傷而勇敢。如果我說它哀傷而勇敢,就意味著故事雖然哀傷,最後卻讓我們感覺到書中人或書寫者的勇敢,那故事的未來就透露著光明與療癒的可能性,它就是一本提供希望與信念的書;但我說的是勇敢而哀傷,意思是,儘管書中人或書寫者如此勇敢,努力對抗某種沈重的命運,終究夜幕還是落黑下來掩沒一切,最後的結局只剩纏綿不去的哀傷和疼痛,這就成了一首反覆低迴、隱隱作痛、無法卒聽的絕望之歌。
為什麼如此勇敢卻又如此絕望?因為這個故事血肉相連,無從分割,一切割就血肉模糊,與汝偕亡,一點救贖的希望都沒有。
在中文世界的書寫傳統裡,懺悔錄式的告白書寫向來是不存在的,告白自剖所帶來的滌淨作用也是不被承認存在的。在中文傳統裡,書寫是用來教化和諧的,不是用來揭露衝突的;自省也是用結論來道德教訓別人的,很少是用過程來裸露鏡顯自己的。也許西方文學才有向上帝懺悔的傳統,上帝既然是全知的,你還沒說,祂已經完全明白,懺悔者當然沒有遮掩修飾的必要。即使到了現代化社會,上帝的連鎖事業營運已經過時,不能全面照應;精神分析與心理分析已取代上帝,繼續提供聆聽告白的收費服務,愈赤裸黑暗的自省,被視為是愈接近治療的告白。往自己內在暗處深掘、不畏創疤傷口的作品,因而成為西方文學一個令人戰慄佩服的傳統。
但我們屬於「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另一種傳統,我們不是誠實認真面對自己的民族,而是遮掩傷痕、粉飾太平的民族,也是傾向於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我們總是世故地抹去銳邊利角,隱去內心的真實慾望,虛情假意地配合別人。我們不愛真相,真相永遠是玻璃破片,割傷別人也刺痛自己,我們活著已經感到艱難,還要內在真相來折磨自己做什麼?
這樣,你就知道陳俊志這本書有多麼稀少和多麼驚世駭俗。
陳俊志的書有雙重告白,一是家族私史,一是情海翻騰。但前者更準確的說,是家族醜聞的私密回憶;後者則應該說,是同志世界的慾海翻騰。而兩者在書中也曾交會成一個高潮事件,那就是他的油漆工男友劈腿自己的親妹妹,比通俗劇更誇張戲謔的那一刻……。
這就是我說故事無法分割的緣故。你如何可以分割血緣?己身所從出,或從己身所出,通通無可選擇。生物父親是一個結果,不是願望,更非離奇身世可以改變或掩蓋;你可以被平凡或奇特的俗世父親養育成人(包括他是一位國王、園丁、或一匹叢林野狼在內),但你只可以有一位真正給你DNA的生物父親,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陳俊志是知道的,因為他在書中寫道:「……敦化南路家屋二樓逆光的廁所馬桶,童年的我無意中見到父親的陽具。在逆光中,在微粒飄浮的空氣塵埃中,在偶然閃現的記憶中,那模糊不清的陽具是賜予我生命的源頭。」)。
陳與父親的衝突也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父親因債逃家,沒有負起對妻子與兒女的責任;另一方面則是父親不接受兒子是同性戀者的事實,兒子的自我與家庭顯然是無法共存的。但這種不得理解的衝突無路可出,連爭辯甚至弒父都無法解決,除了自我放逐,流浪到另一個場域去做一個沒有來歷的鬼魂。
或者,你要像三太子哪吒一樣,割下你自身的骨頭還給你的生父,剜出你全身的肌肉奉還你的生母,只有把血肉都銀貨兩訖付畢還清了,我們再無瓜葛,你才能真正脫離血緣的牽連與家族的枷鎖。在此之前,你只能絕望地抱著一絲希望,一覺醒來,自己已經變成了毫無牽掛的孤兒……。
「地獄就是別人。」但當中最靠近地獄的一種別人,就是「家人」。自由意志與血肉牽連先天不相容,這件事一早就被存在主義者識破了。
如今陳俊志已經是個不懼牽掛、回首過去的鬼魂,他無限柔情地觸撫家屋寫真的映像廢墟、咀嚼往日片段的荒蔓記憶,再緩緩春蠶絲吐隻字片語的書寫過程,在我看來,猶如是一小塊一小塊凌遲地割骨剜肉還返雙親的寫照,也許完成這本書,他已經脫離親緣、超渡自己了。
用這樣斷絕殘酷的象徵,我也才能夠說明這本書的重要性和震撼性。但我也許還不能說出書寫家族暗黑史的意義,陳俊志不只在書寫過程中超渡了自己,其實他也通過一種俯瞰的觀照,超渡了其他家族成員。世俗給家族某些成員的評價描繪可能有敗家敗德、任性浪蕩,只有通過另一種理解,才能賦予超脫的形象,他們才超凡入聖了。
書中一段描述,可能會讓我回味多年。那是關於不守婦道的二姑姑的一場戲,眾人正在新店溪谷的土雞城為父親舉辦一個宴會,二姑姑帶著膩戀的男友前來,席中父親突然臉色鐵青開罵起來,場面正顯得不可收拾。但二姑姑「從來不是溫婉嫻淑的良家婦女」,大家正在勸嚷之中,這時候,卡拉OK樂聲響起,「二姑姑忿忿地拉起旺仔……前一步後一步婀娜多姿地跳起恰恰。」
黑暗溪谷泛著鬼魅燈火的土雞城,徐娘半老的黑貓二姑姑示威似的、不認份的、不服世俗禮教的,在卡拉OK委靡的樂聲,拉起一位中年台客,煙視媚行地跳起恰恰,這個勁爆場面俗擱有力,寫實到超現實的境地,耐人尋味到不行,也不負書寫者本是影像藝術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