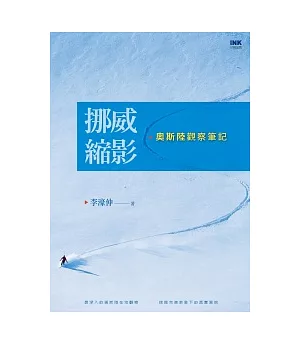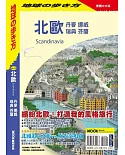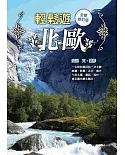推薦序
在Oslo唱solo的那個記者/王健壯
有一種人,生來就流著記者的血液,不論走到天涯海角,只要筆電還打得開,記者的宿命就不會終結。
李濠仲就是這種人。他辭去報館工作,「隨妻遠征」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後,才兩個多月,就架起了他的部落格,而且,直接了當就取了《記者》(solo journalist)這個名字,一個人在奧斯陸「重操舊業」。
在部落格發刊辭中,他調侃記者的工作:「有一種工作,入行開始就想轉行;幹了一輩子,還沒升遷就碰上資遣……;成就感遠遠不及挫折感;拿到的獎金,總是追不上交警開給你的罰單……;朋友相交都是達官貴人,自己的社會地位卻每下愈況……。他品頭論足,說三道四,沒一件事跟他相關,他卻關心每一件事……;他的新聞鼻嗅覺敏銳,臉上那個鼻子卻因為長期過敏噴嚏打個不停……。」字字句句雖有點犬儒味道,但也傳神至極。
solo journalist可以翻譯成「一個人的記者」、「獨唱的記者」。記者,本來就是「單幹戶」,在報館或雜誌社跑新聞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個人體驗,偶有獨家新聞佳作,那就是完美的solo,風光啊!
然而,階段性移居北國的濠仲,現在並沒有報紙或雜誌為後盾,他建構的唐吉軻德團隊:一個文字記者(他自己)、一位電子攝影(電池續航力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攝影機)、一位平面攝影(一台遇冷就無法正常開機作業的數位相機),還有得靠膠帶才能與相機或攝影機密合的腳架,但他還是solo得不亦樂乎。
這句話也是他自己說的:「有一種工作,廿年不升遷,還能讓你樂在其中,那應該是記者;有一種工作,卑微渺小中裝著宏圖大業,那正是記者。」說來說去,他就愛當記者,「記者」本色已經化進他的骨子裡。正因為如此,讓人在北國的他,不至於讓「獨唱」落入「獨白」,即使少了龐大的樂團,依舊能搞得熱熱鬧鬧。
濠仲是我在《新新聞》的老同事,按輩份算,《新新聞》創刊時的同事屬於「保定時期」,濠仲進《新新聞》較晚,屬於「黃埔時期」的小朋友。這個小朋友雖然木訥寡言,但採訪認真,讀書勤快,學習力強,我很早就看出他是天生當記者的料,而且有當好記者、大記者的潛力。
在《新新聞》當記者的人,不論是保定或黃埔時期的,或多或少都有點理想色彩,有點叛逆基因。但在《新新聞》當記者的人,也或多或少都有點鴻鵠之志,武功稍有所成,就想下山闖蕩江湖,二十多年來不知有多少星散流離各地的「新新聞退除役官兵」,棲身各家媒體,濠仲也是其中之一。
當過濠仲總編輯的楊照,曾經在悼念《新新聞》老同事羅葉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形容《新新聞》的同事:
「在一個意義上,《新新聞》扮演了那個年代新聞事業培訓的重要角色。《新新聞》的財力基礎始終單薄,不得不大量進用年輕的職場新鮮人,等到新人磨成熟了,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新新聞》微薄的薪水也就往往留不住人。這對《新新聞》一直是經營上的困擾、挑戰,但對整個台灣新聞界、台灣社會,卻或許不是壞事。
「很多年輕人在《新新聞》最早切身理解了什麼是新聞,什麼是編輯工作,甚至什麼是工作,什麼是理想,什麼是依違徘徊在現實與理想間的思考方式。總有一些原則、邏輯,透過《新新聞》留在他們身上,隨著他們帶到台灣新聞界,在最黑暗的情況下,仍然保存了一點專業與理想的閃爍光點。」
濠仲當然也是那些閃爍光點的其中之一。
一年半前的三月,台灣的天氣還沒擺脫晚冬的寒氣,濠仲在奧斯陸舉辦了《記者》的創刊酒會,邀請貴賓從馬克思、恩格斯、馮內果、赫塞……,大夥兒一字排開(全部站在他小而簡單的書架上),我(照濠仲的說法是凱撒最不愛的台灣老記者)何其有幸也是受邀貴賓之一。
一年半後,濠仲把他客居挪威的生活整理成書,這不是一般到此一遊的旅遊書,更不只是隨興散漫的網路作品,每一篇作品,都有他個人採訪的歷程,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與台灣關聯的密碼。
我對濠仲雖略知一二,但對挪威其實卻一無所知,因此只能當濠仲和讀者之間的介紹人,並且替他的新書寫幾句道賀的話;但有句話不得不提醒濠仲:在奧斯陸舉辦新書發表會的時候,千萬別再喝什麼雞精雞尾酒,太遜啦!
作者序
若非一九六九年發現石油,一個四分之三國土為不毛之地的窮困小國,今天如何能躋身世界富有國家之列。此地曾經一貧如洗,人民得靠配給牛奶、麵包度日,有幸得以脫胎換骨,真是老天眷顧。
既然國民平均所得高達八萬美金,想必各個本錢雄厚,誰都有資格搖身一變而為大財主或貴婦,街上的挪威人豈不全穿金戴銀,手掛鑽錶,一身銅臭,名車滿街跑;物價之高,全世界排名數一數二的首都奧斯陸,又難道不是夜夜笙歌、紙醉金迷、燈紅酒綠;華麗的摩天大樓也該櫛比鱗次,奢華的精品服飾,自當讓人目不暇給。
總之繁榮昌盛、國富民強,要不波瀾壯闊地攤在眼前,就是堂堂皇皇地掛在嘴邊,不然,光是掏錢埋單,豪氣干雲的手勢,大概也能顯露其不凡身價。
但,不,完全不是理所當然那麼回事。曾榮登地球上最適合人居住城市的奧斯陸,全城土里土氣,彷彿北歐的前衛、時尚完全與之無關,這群維京人的後代,反而是悠然自得於品味欠佳的服裝打扮,以及一如身處窮鄉僻壤的都市生活,單調、乏味、無聊,一成不變,克勤克儉,可惜了石油創造出的財富,鹹魚翻身後的挪威,關於打理門面、尋歡作樂,似乎還不懂得何謂一擲千金。
當其他國家競相爭逐世界第一高樓時,挪威人總是一副事不關己且興趣缺缺,從未想過有朝一日也要在奧斯陸如法炮製,儘管對他們來說並非難事。至於大夥兒所熱衷的,則是趁著周末鑽進遠離塵囂,那間沒水、沒電的度假小木屋裡,享受上個世紀克難卻逍遙自在的片刻,否則,在公園、湖邊赤裸著半身看懸疑小說,或在高低起伏的雪地上踩著滑雪板來回步行,亦能體會人生幸福的滋味。石油能為這群人打造出金山銀山,他們嚮往的依然是上個世紀閒雲野鶴的山居歲月。
當我以瞻仰的心情遊歷這童話般的王國,並對著當地人讚嘆其文明和進步時,挪威人的第一反應,經常是帶著狐疑的眼神回你一句「沒搞錯吧,這冷的要死的鬼地方哪裡好了?」從他們的語氣,我不覺得是自卑感作祟,或者是將驕傲喬裝成謙遜,我想我還分辨得出什麼是虛偽矯飾,什麼又是率直。
如果,位在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挪威,可被視為是現代文明國家的典範之一,那麼,我其實有點懷疑,它究竟憑的是哪一點?又到底這是世外桃源,或者根本是個外星世界?若我能藉由這一年多來不同的情節遭遇,拼湊出挪威的縮影,是否答案將離我不遠。
挪威雖美,畢竟不是天堂,偶爾我也會轉進陰暗的角落,一窺究竟,以至發現原來一切未如想像中那樣完美,但這或許更有助於我看清楚眼前「這冷的要死的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