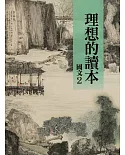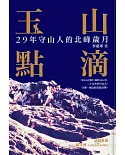新版推薦序
去年九月起,在東華大學當駐校作家。接近下學期末的一天清晨,中文系學生約我前往華湖。
華湖位於學校隱密的雜木林裡,一般人不易尋獲。千禧年左右,我在此遊蕩。腳踏車停靠路邊,沿著一條明亮的碧綠小徑蜿蜒進去,中途遇見一條蛇盤蜷著。退了十來步,折了個小彎,很快抵達湖邊。對岸有罕見的沼鷺,木訥地佇立著。腳色肉紅的緋秧雞,悄然從草叢探出身影。我蹲坐在草地,跟牠們一樣安靜。整個下午彷彿坐禪般,不覺時間之溜逝。
跟我相約前往的男同學叫詹宏博。去年在彰化溪湖高中聽過我的講演,意外地又在此結緣。
在集合點碰頭時,宏博手邊持了一把大鐮刀。我有些困惑地探問,「走進華湖需要這麼辛苦嗎?」
「上回吳明益老師帶我們進去,戴了一把山刀在前面開路。」
未幾,三位中文系女生按時到來。她們昨晚得知要去華湖,也興奮地跟來。宏博在前帶路,我們旋即走進了游泳池後隱密的林子。一進去,他就不斷地撥枝劈草。我才吃驚,十年前輕鬆遊蕩進來的情景已不復存在。
昨晚大雨滂沱,林木沾滿溼重的雨露,天色迄今仍陰翳如蒼鷺暗灰的背羽。在路跡不甚明顯的芒草小徑裡,我們有些吃力的往前鑽探。不過一小段,領頭的宏博衣領溼濡,黏附了不少草葉碎屑。我和三位女生也不斷被銳利的芒草割劃手臂,但大家甘之如飴。邊走邊聊才知道,她們都跟吳明益來過華湖。
既然進來過了,為何還要再次重訪?等再往前,我才恍然明白。
小徑上茵陳蒿叢生,不少植株開花了。我停下腳步介紹其生長特性,順便描述其藥用和可能的食用功能。一位女學生笑著說,「吳老師也介紹過,有位同學回去後,用茵陳蒿充當義大利麵醬料,很好吃呢!」
「既然吳老師講過了,我就不多說了。」
她們卻撒嬌,「你們講的不一樣,我們還是有很多吸收啊!」
我點點頭,繼續介紹。什麼山鹽青、紫株、咸豐草,再嘗試著以自己的認知描述。後來聆聽到周遭的鳥聲甚多,我們安靜地站在草原裡。我嘗試著想像這些啼叫的可能意義,描述自己的感覺。
他們認真地點頭,很想找出發聲的位置。那種對自然欽慕的單純眼神,隨即教人聯想,吳明益的教學勢必對他們影響不小。
走到一處空地,宏博介紹說,「這是吳老師露營的地方,他鼓勵我們,可以嘗試到這兒過夜,而且最好一個人單獨前來。」
一路上,他們繼續提到吳明益的種種。對他們而言,吳明益不只在讀書上,帶給他們各類知識的啟發,還在縱谷裡打開一片自然觀察的視窗。
接下來,路徑消失了,草叢比我想像的更加高大隱密。宏博一時找不到路,躊躇不前。女同學們雖來過,卻也記不得通往湖邊的小徑在哪?
宏博有些歉然地跟我說,「以前跟吳老師從這兒再走進去,草叢並不高,很快就找到路,但這次很奇怪,草叢都快變森林了。」
早上我還答應學校一堂講演,如果這時不快點找到華湖,萬一陷在此地,跟人家說在校園迷路,恐怕會成為笑柄。我有些心急地加入尋找,還好,很快就發現了路跡鮮明的小徑。
我帶頭在前一邊想著,啊,怎麼現在走往華湖變得如此辛苦,這不過是一個大學的湖泊呀!還有,待會兒看到的湖泊,會是過去邂逅的那等開闊亮麗嗎?
五六年前,吳明益應聘到東華時,我欣喜地郵寄一篇自己撰述此湖的小品,建議他日後何妨常來此走逛。雜木林是東華大學校園的自然特色,更是花東縱谷平地森林和曠野的指標。華湖則是此區雜木林的心臟,提供了周遭更多樣生物的豐富內容。
日後他即常來此湖觀察和上課,著作裡也提及。當年我來華湖,小徑開敞好走,或許到他走訪時即草木深掩,不易探路了。而走在後頭的學生們,跌跌撞撞地跟了上來,又彷彿某種幽微的隱喻。宏搏熱愛鄉野,也想嘗試自然書寫,這是他前來花蓮就讀的主因。在這兒遇到吳明益,想必更能達成其心願吧!
我們的出現激起一隻夜鷺和小白鷺竄飛,湖泊隨即進入寧靜的狀態,只有盤谷蟾蜍低沈地單鳴著。跟當年一樣,湖泊對岸依舊是幽黯的葳蕤森林,遠遠地才有學院的塔樓露出。湖泊雖無過去開闊,但依舊原始,生機隱隱。
我們沿著湖邊巡行,宏博又主動帶路,嘗試著從另一條小徑出去。小徑再往前,形成泥濘之地。每個人的腳都浸泡在污水裡,狼狽地跋涉著,最後再走進溼濡無人的森林。
面對藤蔓糾葛的林子,宏博再次找不到路。我再度上前,試著協尋。一邊探路時,突然間想起了吳明益的《迷蝶誌》。這是他自然書寫的第一本散文創作,甫出版即得接連得到不少讚譽,旋即被視為文學界重要的新秀。
昨天他寫信給我,想要再版此書,因而客氣地請託,是否能在之前的舊序添補些什麼。不知是重返此地,還是在找路,我竟想起此事。
也因這一突然聯想,萌生了很大的感概。這座我們前後都探看過的華湖,多麼像我們都熱愛的自然書寫一樣。但大家進來時,華湖展現了不同的風貌。我走進來較早,小徑路途明亮。吳明益稍晚抵臨的時日,想必辛苦許多,而且後來再帶學生進來探看,都得配備山刀除草了。我可以想像,他在東華大學執教,勢必也期待好些學生,日後能成為熱愛山川的創作者,跟我們一樣幸運地受到自然的眷顧。
以前寫過一序,贅述此書的優美質地。如今重新回顧,或者該定位在一個台灣自然寫作的光譜上。此書當年的結集,大抵是台灣自然寫作最為頂盛時,本土創作和翻譯作品備出。但《迷蝶誌》的出版,儼然預知了自然書寫作另一成熟面向的可能。
那時我以為,因為科普知識豐富了,自然觀察成為顯學了,這樣的寫作者恐怕會愈來愈多。豈知一個年代過去,自然書寫的高度卻停滯於此,幾不見新人。吳明益後來的著作,諸如《蝶道》或《家離水邊那麼近》早已擺脫《迷蝶誌》的青澀,卻也因其作品的成熟亮麗,更加突顯這一領域的後繼乏人。
那年的前序帶著很大欣喜,今之後序則頗有感傷。網路時代年輕寫作者多不願意走到戶外來吃苦,主流社會提供的生活價值亦少有這類空間,像宏博這樣持著鐮刀,在林子裡摸索去路的孩子委實不多。他依舊在前探路,身影愈有吳明益的堅持,我想他應該很快會找到方向。(2010)
劉克襄
初版,推薦序1
<台灣特有種:一個自然寫作的新面相>
一位陌生的年輕作家寄來他即將出版的散文集,隨著集子還有他精心手繪的插圖和micro鏡頭拍攝地照片做為內文的搭配。此外,郵袋裡還附了一本他的處女作《本日公休》。在這本短篇小說集裡,作家宋澤萊以「美麗的初航」稱允作者為未來的重要作家。
面對散文集,我卻相當遲疑,自己是否能寫好序。畢竟,對方是一個陌生的實體。我素來內向的個性夾雜著奇特的疏離和不安。生怕自己的感情無法融入,就對不起作者辛苦的創作了。
可是,開啟內容後,隨即被一種特有的熟悉情境所著迷和感動。整部集子所處理的題材,正是我這二十多年來信守的寫作主題和環境。他已經在我曾經走過的大地,試著以自己的腳步摸索一陣,而我竟習焉不察。從一篇篇的敘述,我一邊感慨自己的疏失,一邊則揣想著他的思維和體驗,不自覺地對照著自己年紀相仿時的遭遇。
藉由這塊土地的牽成,再透過這樣的野外生活共鳴,我慢慢地認識了他;並且隱隱掌握了一種來自然觀察的原力──我們彼此深知這種力量的特異,進而不揣淺陋,試著撰文闡述,也決定向讀者介紹吳明益。一個非小說領域的吳明益。我要試著就他這回作品的內容,素描他的散文背景和啟源,進而簡短地追溯我們這一群野外族群的發展過程。
蝴蝶是吳明益這本創作的主題。整個敘述的主軸亦緊緊環繞著蝴蝶的生態習性,以及由蝴蝶牽引出來的自然志和生態環境問題。有趣的是,這個主題和先前的小說並無任何瓜葛。若不掛上作者的名字,還真難以想像,兩種文類竟都是同一個人的創作。
純文學的前衛小說在前,自然觀察的散文在後,這是什麼樣的寫作意境和創作斷裂呢?恐怕也只有作者能體會箇中滋味。早年自己寫詩時,雖然也有過這樣的企圖和努力,文詞裡難免還夾雜著一些糾葛的情緒,始終無擺脫文藝青年的喃喃自語。吳明益竟無這層困境,讓我頗感稱奇。
賞蝶和其他自然觀察一樣,必須透過不斷地旅行,在跋涉山水中,長期錘鍊心志和書寫的內容。吳明益沒有忘記這個本份。他以我極為熟悉而親切的旅行方法,在台灣各地走動,記錄自己觀察蝴蝶的心得,而且充分發揮創作的想像和才華。儘管他走的還不夠遠,亦不綿長,但是已經呈現的作品卻充分展現了更深更廣的可能。
在蘭嶼,他尋找珠光鳳蝶。從”十塊鳳蝶”的故事裡,旁徵博引地提到了鳥居龍藏、夏曼.藍波安和蘭嶼的自然沿革,再以此穿針引線,生動地介紹捕蝶歷史、珠光鳳蝶的棲地。在國姓鄉,他追蹤小紫斑蝶的歷史,從四百年前荷蘭人的經營,到鄭成功的拓墾,再涉及德國人紹達的辛苦採集。一隻小小的普通蝴蝶,在他熟練的寫作技巧下,經常就有橫向地生態習性和環境變遷之敘述,兼有縱深地歷史和自然志的延伸。縱使在校園、都市之小天地,我們都看到他和蝴蝶熱情而精彩的互動。毫不起眼的蛇目蝶,在他眼裡竟飽滿了神話和哲學之味。笨拙的大白斑蝶在環境不同的對照下,也有了無以倫比的炫麗飛行。
吳明益創作所汲取的養分不僅廣泛且拿捏得宜,我不時讀出一陣歡喜和讚歎。這幾年來,台灣自然生態觀察和歷史人文所累積的豐富知識,都在他的旅行過程裡,成為隨手可汲取的養分。他不像八○年代的自然寫作者,犯了捉襟見肘的困窘,常要向西方取經,也不時露出那個時代教條式的道德威權;甚至仍無法擺脫口號式的報導。
由於在那個年代初,我即已投入自然題材的創作,對於當時正興起的自然寫作,以及後來的發展始終保持高度的關心。同時,對每一個階段自然寫作者展現的風貌,更充滿好奇。我亦不時積極尋找這類同好,相互切磋、請益。這幾年,在這個領域裡,我也遇見了不少”台灣特有種”。諸如鎮日迷戀老鷹的沈振中、倡議綠色旅行的陳世一,或者遇見孤高的古道學前輩楊南郡。尋找他們,一直是我從事自然觀察裡不可或缺的工作。我把它當成和觀察動植物一樣快樂的事情。
不過,吳明益明顯地和他們的出身不一樣。他和我一樣都是”科班”出身的。我的意思說,我們都是從文學出發,在創作的路上和自然生態的視窗照會了,從此就不再離開它。這樣的人並不少,在八○年代時,王家祥、洪素麗、凌拂和徐仁修等都是這類同好。
九○年代初也有零星的創作者,朝這個方向在努力創作和實踐生活。但直到最近我才又有明顯地感受,為數更多的另一批積極創作者,堅持著更成熟的生態觀,在自然寫作的範疇裡,尋找自己的風格和觀點。如果你常看報紙,應當不難看到杜虹、李曉菁、范欽慧、廖東坤等人的名字,以及他們的作品。
從他們的創作意圖和內容,我試著瞭解,那些經過整個年代生態環境運動洗禮,並且擷取更多西方自然寫作精華的創作者,對土地倫理有無我們的好奇和熱中?亦或是充滿新的生活價值?
早期的自然寫作者常被譏諷,只能以淺顯是非的道德和美學說服人。晚近的自然寫作者很少陷入這種啟蒙期的思維框架。吳明益更是,他所成長的環境讓他輕易地跳開這個八○年代環保的迷障,直接以更成熟的自然知識,在文學的場域奔放。他的行文,不僅看不到早年自然寫作者(包括我)的那種濫情了;同時,也無作家楊照在九○年代時認定的急切和焦慮。
他的創作內容展示了較為活潑的可能,以及更多文字鍛鍊後的繽紛。三種主要的面相交錯著,形成他書寫蝴蝶的內涵。一為自然誌的隨手捻來,豐富了他文章的深度,並顯示了他的聰慧和機敏。二是豐富的野外經驗,允當地揉合科學的生態知識,讓他的敘述更加有說服力。三係文學的技巧卓越,平淡的素材經過他的消化、轉換時,充滿了詩意的效果。
從自然寫作在台灣的發展來看,這一系列蝴蝶散文所蘊藏的成績和發展,恕我再襲用野外經常使用的語言:我又發現了另一個新品種。一個在這塊土地上經過許久才可能蘊育的種類。
晚近以自然為題材的創作,逐漸傾向工具圖書化的書寫,輕忽了文學長遠的功能和意義。很高興,作者對這樣的傾斜保持一個高度警覺的距離,繼續在自然寫作的園地上和我們一起深耕。
從吳明益的創作,我不免想到晚近,國內大量譯介進美國自然寫作者的創作經典,我們從梭羅、約翰.繆爾的早期生態文學作品,讀到晚近如戴安.艾克曼、亨利.貝斯頓等人的創作,每一個階段的自然寫作者都有他們的生活哲學和土地倫理觀。
台灣也有機會如此呈現成績。在短短二十年間,隨著生態意識的高漲,我們的自然寫作人才並不乏後進。生態主張逐漸多樣下,觀察也展現更多的細膩和成熟。薄薄地這本散文集雖不足以展現個人的強烈風格,但一種過去較少看到的新方向已然成形。
自然寫作也需要更多歷史的積累,透過一代接一代生活和哲思經驗的開創,緊密地和生態環境互動。這種特殊的文學類型方能豐收,成為台灣文學裡重要而獨特的一支。環顧過去,我們還走沒幾步。歡迎吳明益進入這條路線,而且能夠持續走下去!
對我而言,吳明益的初航不只是美麗,方向也很準確。(2000)
劉克襄
初版,推薦序2
<春芽的喜訊>
笈克是個憨厚的大男生,先前擔任我的研究助理,有天他問我,如何產生內化的自然情操,不經意的丟給他:「不妨夜間跑去大坑逛逛」(大坑是中台灣極其少數低海拔殘存的天然林區),隔幾天他跑來跟我說:「我終於明白關在鐵籠中,獼猴的心情!」
原來他暗夜走在大坑山稜上,極不熟稔的黑暗世界,仿如常人初瞎。最吵鬧的死寂中,突然樹梢響起急迫的窸窸窣窣,全身毛孔不及張豎的瞬間,樹葉猛浪狀一波波交錯傳導,推測是獼猴夜遊,驚嚇中隱約瞥見,一雙雙快速錯動的火眼金睛,虎視眈眈的瞄準他所有的舉動,脊髓剎那急凍的恐懼中,他跌撞奔逃下山。
此後,他或將明白陰陽對調、黑白交換、事理易位、同理心置換的系列纏綿,對待其他生命的另一面向反思,雖然他祇是告訴我,那種「被窺視的恐怖」。
吳明益,一位素昧平生,好像是泅泳在詩詞訓詁、唐字海洋的年青人,迷戀福爾摩莎的蝶影只是近二、三年事。在他隨著文明時髦浪潮,湧進現代化商機盎然的昆蟲館擔任解說員,充當「生態保育、傳遞生物知識」的尖兵之際,卻發現那是一座富麗堂皇的昆蟲集中營,囚禁的不僅是無助的天牛、大蝗、鍬形蟲、蝶與蛾,還有扭曲變形的自然驚艷,另類自然的殺戮戰場,只為了讓經營者張大嘴巴,奮力吸吮傳遞自肉商、菜販、魚攤、小吃店員手中,一張張皺縮、瀰漫腥臊的新台幣。
於是,不忍卒讀的尷尬下,吳明益逃離了生死攪拌器的活體展覽區,選擇與死屍為伍,並將他視覺網膜的顯影,沖洗出一段段溫柔的控訴,文章題為「寄蝶」,文中他敘述,抓自恆春半島的大白斑蝶,被夾在三角紙板,郵寄7小時,越過陰陽界,來到展覽館,充當「保護生命、恢復環境」最後剩餘價值的展現,讓魚貫而入的親子,綴在衣襟、勾在髮梢,拍下一張張愛死自然的遺照,這是否就是20世紀末,台灣的保育文化?
合此因緣,思惟細膩的吳明益,將他的口器深入不同生命之間探尋,而且漸次萌長羽翅,飛出了人本的藩籬,成了半個「迷人」,開始以筆,檢驗蛻變中的自己,於是,一篇篇時人稱之為自然文學的散文脫蛹而出。「十塊鳳蝶」、「死蛹」、「界線」、「陰黯的華麗」……,鋪陳他的生活,逐蝶、夢蝶,讀書心得,意識或非意識流衝撞的些微映照,反芻著生命現象宿命的迷惘,而且,就像初戀的第一次約會,強作從容的去赴一場內分泌的戰爭,直接的要把初吻的pH值,傳述給認識與不認識的人種,告知百年台灣生靈凋殘的悲劇。
不知有無記錯,他的一篇文章好像我曾經評審為某個獎項,當時無法給首獎的原因是「輕薄」了些,而出版社主編捎過來全書的文稿後,我才知道合該輕靈,因為他寫的是實際也該飛的意象。
斷續展讀吳明益君的散文,閃入腦海的第一印象,是我那被台灣獼猴嚇出領悟的助理,其次,聯想起高中時代,我在「當代中國十大哲人」強悍霸氣的「新儒家」氣旋中,落荒奔向自然科學的履歷,相對的,吳君卻從傳播廣告科系,投入中國文學研究所的浸染,意外的,側生迷蝶的胎變,丟給我春芽的喜悅,最重要的,他不像時下「成名的自然文學作家」,老是從怎麼吃、如何用的貧窮文化出發,玩弄些虛無縹緲的文字魔術,接受王永慶合成的塑膠桂冠,穩坐在都會叢林把玩「芬多精」。吳君接觸了真實的自然,也不得不自稱「溫和的人類中心主義」。
我無意評論吳君的文學造詣如何精緻,毋寧我較關切多少台灣人願意靜下心來,咀嚼「迷蝶誌」的影像、意象,以及文字之外的情操。畢竟,二千三百萬釐不清「省籍」的台灣人,正陷入「國籍」的錯亂中,吳明益君適時拋下了「地籍」的救生圈,只搶救願飛的人種。何其盼望,多一些台灣人,認同「地籍」之後,進一步一窺「靈籍」。
誠懇的向讀者推薦《迷蝶誌》。(2000)
陳玉峰
初版,推薦序3
<蝶之驚豔>
六十多年前當我初次到學校時,在校園內小灌木林上看到很像花蕾的東西,牠緊緊地附在枝條上,但用手摸時會擺動,當時我以為是會動的花蕾。有天清晨牠裂開了,當然開不出一朵會動的花,卻跑出一隻又肥,翅膀又皺的醜小蟲。當我失望而想打落牠時,那皺小的翅膀像一把扇出展開了,就變成很美的蝴蝶。我實在感動了,從此六十多年蝴蝶時時刻刻帶給我驚喜和快樂。
近二十年我也為了蝴蝶保育盡了我的心力。至今推展蝴蝶保育略有成效,然而我總覺得,我的努力就是不能廣泛的擴散到社會的每一角落,並深入眾多人們的內心中。因為我所能做的,僅限於以有關蝴蝶的生物學知識為基礎進行保育觀念的推展。因此長期以來真正期望有人能夠以藝術、文學的角度去解析蝴蝶美妙的內涵,藉以深入多元化社會中不同領域的人群中,使蝴蝶保育成為廣泛人們的共識。
這類做夢般的願望將由吳明益先生來實現。他雖然並非有關昆蟲科系畢業,然而他以專研而得的極為豐富的文學素養為基礎,再配合近多年來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中,直接與眾多蝴蝶接觸,擁抱優雅舞姿編織的美妙生態,並以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從牠們生活行為上的點點滴滴,終於成功的察覺再深入閱讀蝴蝶散發的情感。
他更能分析並綜合這些資料、感受,並將蝴蝶生涯中的喜怒哀樂以文學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這些有關蝴蝶的創作實為揉合生物學上的蝴蝶生態知識以及蝴蝶感情,用藝術手法呈現的嶄新嘗試。我深信,他能打開過去我努力進行蝴蝶保育推廣而無法滲入的另一群人們的心中,有助於全民關心象徵台灣的蝴蝶資源之保育推廣。(2000)
陳維壽
作者序
<死去的那些>
《迷蝶誌》出版十年了。意思就是說,當時二十歲讀到這本書的人,現在已經三十歲,當時四十歲讀到這本書的人,現在已經五十歲,當時才出生的孩子,現在已經可以到野外去結識蝴蝶。而那本書裡所提到的每一隻蝴蝶,其實都已經死去,幸運的則可能已繁衍了三十代。
這一年多來,有好幾位在出版界任職的朋友問我《迷蝶誌》重新出版的可能性,我總是婉拒,理由是,對一個寫作仍不成熟的人來說,不斷嘗試寫出過去未曾寫出的物事,才是最重要的事。畢竟,多數的公共圖書館,可能也都找得到這本書,對我而言,寫書的目的絕非是為了賣書而已,而《迷蝶誌》裡那個著魔、感情像藤蔓植物般容易失控的我,畢竟在本質上已大不相同,我得認真地想想,這本書重新出版有何意義。
早在六、七年前,就有讀者告訴我,《迷蝶誌》在市面上已經買不到了。我總是選擇忽略,建議他們找看看有沒有二手書。幾個月前,在一個演講場合裡,有一位讀者拿了《迷蝶誌》來找我簽名,她說這本書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另一位讀者則拿了我所有的書過來,說:「就只缺《迷蝶誌》了」。
在這樣的時間之流裡,還有人想起這本書,做為一個作者,應該知足了。年初我收到十年前《迷蝶誌》編輯的來信,提及這本書重新出版的可能性,我很乾脆地拒絕。幾個月之後,《蝶道》有了出版修訂版的機會,得以更正裡頭的錯誤。常給我適時忠告,陪我走過書裡每一處地點的M不經意地說,《迷蝶誌》重出也不錯,可以把裡頭的錯誤也一併改過。於是,我坐在書桌前,把當時初版的舊書拿了出來,回憶起《迷蝶誌》對我寫作的意義。
當年只出版了一本沒有什麼人關注的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1997)的我,因為任職麥田的編輯和我討論出書的可能性,才決定以當時我沒有發表,撰寫蝴蝶的作品來出書。當時她問我可以找誰寫序,我說我誰都不認識,但有三個人對我意義重大,分別是蝶類專家陳維壽老師,深深投入環境運動的陳玉峰教授,以及在我的印象裡,總是默默一個人到各處旅行、觀察自然的劉克襄先生。編輯把稿子寄給這三位我連一面都沒見過的老師們,出乎意料之外,他們都答應為《迷蝶誌》寫篇文章。某天黃昏,我正獨自走到校園附近一處荒地拍照時,呼叫器傳來回撥電話的訊息。我到公共電話亭回撥了電話,那頭即是劉克襄老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書出版以後,我預計應該會像小說集一樣無聲無息,沉沒在書海裡。那也無妨,本來我就是純粹喜歡用文字表達而已。不料不久就接到台北文學獎得獎的訊息。當時這個獎項是由出版社、學者、編輯推薦參加的,且是以一本書為單位,而非一般的單篇文章的文學獎。得獎自然開心,我上網查了一下,發現小說獎的得獎人是施叔青、朱天心和舞鶴,散文獎的得獎人是林文月(《飲膳札記》)、簡媜(《紅嬰仔》)和我,而評審裡則有我當然仍未曾謀面的陳芳明老師。實在很難精準地描述我當時的感受。當晚我第一次,主動撥電話回家,告知父母得獎的訊息,因為當時他們從未鼓勵我往寫作的路上去。我在電話裡跟父親說:「我寫蝴蝶那本書得獎了。」父親當然不會知道我得的是什麼獎,從電話裡也感覺不出他是否替我感到開心,不過彼此掛上電話後,肯定彼此都有些許激動。不一定是為了那本書,而是那短短的幾句話,因為,自念大學後,幾乎沒有獨自和父親說話過。一周後,父親就過世了。
這本書則活了下來。年底時它又獲得中央日報的年度十大好書獎,幾年後,裡頭的篇章在不少文學選本出現,有些還成了國高中或大學裡的教材,我自己則對這本書日益感到羞赧。一方面它在書店裡總是被放在「昆蟲」那排,而我書裡頭的昆蟲知識膚淺得很;另方面則是因為在野地愈久,愈覺得那本書裡的我,像極了第一次到溪邊的孩子,還不敢涉水、躺在溪底,或爬到大石頭上一躍而下,只是靜靜地坐在僅容屈膝的溪石上,靜靜地將腿伸入溪中,感受到溪床的質感,就眼眶潮濕地,貿然地對岸邊的人說:這真美好。
日後有一位譯者跟我說,《蝶道》裡的文章幾不可譯(於是至今《蝶道》只有一篇譯為日文),但《迷蝶誌》親近多了。有些讀者也說,比較喜歡《迷蝶誌》的「輕」。前者顯然跟語言,以及語言後頭的「影子」有關,後者或許可解釋為讀者的個人偏好。不過我想,說不定是書出版以後,人生稍稍偏移了一些方向。因此雖同是寫蝶,《蝶道》與《迷蝶誌》卻是在本質上絕不相同的兩本書。
我是一個對讀者很不體貼的人,即使在幾年前,我仍拒絕幫讀者簽書。直到現在,除非是演講單位報賬需要,我也不和人合照,也拒絕站著被拍照。既不在報紙與文學雜誌上發表創作,出版新書時也不開發表會,甚至建議出版社取消所有的行銷活動節約經費。因為我認為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喜歡寫作的人,理應就是默默寫作就好。只不過,後來我的職業,和投入的一些環境活動,都無法讓我「默默寫作就好」。
正如美國生態批評家史洛維克(Scott Slovic)所說的,這條道路,終究會出現多元地行動主義者(Polymorphously activist) 。雖然自己還離那裡很遠,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路上」,但確實我的人生移轉後的風景,和「默默寫作」截然不同。
從決定要出版的那天開始,我一面說服自己出版新版的理由,一面也說服自己不要參與太多意見:如果執著於這本十年前的作品應該以什麼樣的形式再版,或許會讓它失去原本的面貌也說不一定。畢竟,稚拙、粗略、零散都已成為它的一部分了。我保留了原書所有的文字(修改錯處),與當時的手繪圖(即使那些圖畫得實在不好),照片則保留部分,更新部分。仍然堅持紙張和油墨的選擇必須對環境友好,封面的視覺設計概念則由我提出,經編輯認可。除了請劉克襄老師為它再寫一篇序外,我建議編輯不必再邀請其他人或團體在書封上推薦這本書,畢竟自己對書市現今那種使用誇張標語與集體推薦的作法並不認同。除了這些顯得繁瑣的意見之外,我把多數的責任,交給了編輯,也要特別謝謝她與美編寬容我的想法和堅持。
那我拿什麼,給絕版後等待多年的讀者,表達微薄的謝意呢?編輯認為可以做個別冊,於是我開始動筆畫《迷蝶誌》每篇文章的蝴蝶,這麼一來,就會跟後來《蝶道》所畫的那些黑白標本圖,有某種意義上的聯繫。
極少蝶會像標本所呈現的型態一樣,完全展翅示人。我將這批手繪,試著做成彷彿一個個的標本圖框,以為這裡頭有某些暗示。不用捕蝶、殺蝶就能擁有標本,這事只有畫畫做得到,攝影也不可能把蝶拍得跟標本的姿態一樣,這是當時還勉強算是年輕的我,唯一學到的事。也是在《迷蝶誌》中,我所解決的一個重要的自我困結。或許,也和我日後帶學生到野地時,所希望帶給他們的一些微妙物事,有某種程度的相關。
毫無疑問,《迷蝶誌》裡所寫的每一隻蝴蝶,都必然已經死去許久。而我仍然希望,某些物事,能就此一直存活下去。
吳明益
2010/6/17 淡水河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