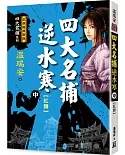作者自序
三十多年前,我認識了一個小女孩。她有多大了?我那會兒也不大,十一二歲的樣子,就模糊了她的年齡,覺得──總跟我差不多吧。那一年,她家裡險遭滅頂之災。
她的父親,那當然了,是她們全家的頂樑柱,在一個軍用渡口當主任,一個小小的尉級軍官,管著幾十艘木船和一群懶散的船工。他接到一紙軍令:大軍遠征即將過河,令他提前做好安全保障。這個父親平常工作不多,無聊又荒蕪,此時有事可幹,興奮異於尋常。他沽來好酒,與部下和船工們祭拜河神、船靈,還飲酒歡慶,一時間渡口彩旗飄舞,鑼鼓喧天,他們準備為大軍送行,預先熱鬧了好幾天。
當大軍兵臨渡口,這個渡口主管卻酩酊大醉,拍臉、澆水,怎麼也弄不醒來。船工無人指揮,河邊混亂一片。大軍長官是位著名上將,勃然大怒,當即命令對他實行戰場紀律:槍決,立即執行。女孩的家人全嚇壞了,他們嚎啕大哭:天啊,天塌了?!
這個女孩不同凡響,不願坐等父親死去,她抹掉眼淚,央求上將說:我父親為祈禱大軍出征獲勝而飲酒,他念及將軍的神威,想像大軍凱旋而歸的情景,一高興多喝幾杯就醉了;請將軍看在我父親年老、平時盡職盡責的面上,饒他一回。
上將拒絕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平日雖盡職,戰時誤大事,不槍斃他難以服眾啊。
女孩說:我請將軍將我同父親一道處死,因為我父親死了,我們也活不下去了。
上將說:可是這裡又沒有你的錯,我幹嘛槍斃你。
女孩又說:我求將軍等我父親酒醒之後再行刑,讓他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死。
這回上將答應了她。
女孩見醉臥不醒的父親暫時不會死了,她果敢毅然地轉身,大聲呼令船工們掌舵開船,她指揮若定,迅速有效地恢復了渡口秩序。她自己
也跳上一艘船,親手撐篙、搖櫓,運渡士兵。船行水中,她放聲歌唱:
河水啊你無窮盡地流,
我的爹爹卻要被砍頭。
我手握船櫓使勁地搖呀搖,
一心盼望將軍早日滅掉敵寇。
歌聲悠揚、淒清,飄蕩在河面上,河兩岸、船上的人們聽了歌,無不為之動容,都替她難受。屹立于萬軍之中的上將也十分感動,神情變得陰鬱。等大軍按時有序地全部渡了河,上將下令免除女孩父親的死罪。
隔日女孩的父親酒醒了,聽到旁人的敘述,他摸著自己的腦袋對女孩說:我的這顆人頭是你替我撿回來的呀,我的女兒!
女孩害羞地紅了臉,忸捏著說:我也不曉得我怎麼有那樣大的膽!
看到這裡,有些讀者要會心地微笑了:這不是一個現實中的故事吧。對,這是三十幾年前我讀到的故事。女孩名叫女娟,是有數的幾名能進入中國歷史文獻記載的少女之一,那位上將也是位歷史名人,他是春秋時期的晉國名將趙簡子(也是在著名的「東郭先生與狼」的故事裡,剿殺得中山狼無路可逃的那個狠人)。這自然是兩千多年前的舊事了。可是三十幾年前,通過閱讀,在我十一二歲的、純淨少年的心靈裡,女娟復甦了,她就像我生活中的朋友一樣親切、可敬。三十年來,她就呆在我的體內,伴隨著我的呼吸,她那被歷史記錄固定的生命,也像是在緩緩生長。她已漸漸變成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也不知是怎麼了,給《倪淑英》寫序,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女娟。女娟和倪淑英之間有必然的聯繫嗎?我可看不出來。實際上,她們間的差異那樣大,女娟幸運地救下了父親,倪淑英再怎麼拼命,也不可能救活她父親。她能做的,只是替父親報仇──在她還年幼的時候。女娟「撿回」了父親的頭,倪淑英卻帶著別人的頭行走了上千里路。
因此說,這是一個過於殘酷的故事。是一個小女孩在煎熬中快速成長的故事。她在半年的時間裡,擁有了別人可能一生才能有的生命提升。在這個故事裡,倪淑英由一個也有著純淨心靈的小女孩,變成一個殺人狂魔,然後她再試著一點點變回她自己──她當然不可能完全變回去,但她竭力想變得更靠近過去一些──我看著這個過程,就像我小時候看女娟站在船上,歌聲飛揚,我屏住了呼吸,我提心吊膽。雖然我明明知道,她們依據自己的生命之力,正在創造、而且也確實創造了奇跡。
這等於說,倪淑英跟女娟一樣,也是個傳奇人物。而在我們平庸的生命裡,那是我們傾注怎樣的渴慕之念才能一睹芳容的傳奇之人啊。我愛她們,以至於模糊了她們的乃至是我自己的年齡,我這時就像還是那個三十幾年前的小男孩,絕不再長大,我心地乾淨,滿懷善念,我需要她們活著並且幸福、美好。
這是個撥動心弦的故事。我的一個在電視臺做攝像師的朋友,偶然間讀了這個故事。他激動難寧,對我說:你一定不要讓它隨隨便便就拍了電影,你得等我的女兒長大,讓她扮演倪淑英。說這話時,他女兒才一歲半,距她長大到倪淑英那年齡,能承擔那麼殘酷的世事,還有誰也不知道世界會如何演變的十餘年。被他的大手緊握,我就明白了:這也是一個渴慕奇跡的人,是拒絕長大的人呵。他幾乎像我一樣愛倪淑英,真是好,這個世界有這種人,它就是還不算賴。
這就是我在故事開始前要說的話。我盼望著倪淑英也能進到你們的心田,就像三十幾年前女娟走進我的心間一樣,她呆在一個隱蔽的角落裡,無聲無息;歲月流逝,我們老去,可是她只緩緩生長。她以此確保住我們心底那一塊純淨的、渴望奇跡的、拒絕長大的空間,不會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