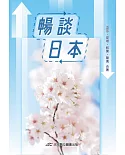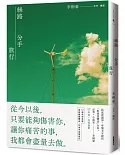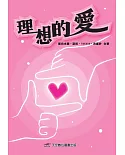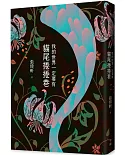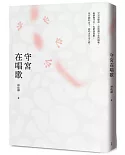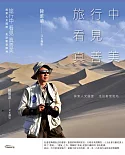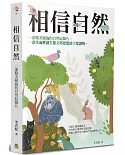記錄有意味的生命片段
年輕的時候,寫作很勤,曾經「立志」每年至少出版一本書。這個小小願望似乎不難達到;最多的時候,一年之間可以出四、五本新作,還不算再版、加印甚麼的。
然而,正如陶淵明所說,「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人很快就老起來,從一九九一年退休之後,我好像只出過一兩本書。將近廿年光陰,彈指而過。
倒並不是寫作的銳氣減退了,而是心境大大不同。以前,總是把文學創作看作是莊嚴的大事,老年的想法是,「真有那麼重要嗎?」如果說,「看得開」、「放得下」就是智慧,寫作又算得了甚麼呢?所謂「千古不朽」,真有那樣的事嗎?
可是,愛好寫作的人,畢竟有一種無可解釋的癡迷,一種「無可忘情」,一種「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
前蘇聯那位以寫詩揚名、卻因寫長篇小說《齊瓦哥醫生》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巴斯特納克,有一段話深得我心:
「……藝術不斷關注的有兩點:它永遠在為死亡默想,而且永遠在創造生命。一切偉大的真正的藝術,都是在模仿並延續聖若望的啟示。」
文學藝術關注的正是在生死之間的歷程,也彷彿是宗教:有一種超乎理性的、難以言詮的神祕感。
人生的若干奧祕,或正是要到了我這般風燭殘年的時候才能體會得深切吧,譬如友情。君子之交淡如水,要經歷很多很多年之後,才能充分品味出這「淡如水」的真滋味。盡在不言中。
中華民國筆會和春臺小集,是我無意中參與的兩個文學團體。沒想到在那兒結識的一些朋友,幾乎都成為我終身的友伴。那些朋友中,有幾位已走完了人生的旅途,有幾位皆入暮年,當年最年輕的我,也已年逾八旬,去日苦多。
那些朋友,身世各異,性格不同,僅有的共同志趣大概唯有文學。我們明白,有了文學,世界不見得就會變好;然而,從寫作中嘗試走出一條路,「報國淑世,我輩不辭其勞」。當然,現在想想,這也算是一種癡迷。一種少年期的不成熟的樂觀主義。
我譯皮爾博士《人生的光明面》那本書裡,他為「朋友」下的定義是:「你最好的朋友,乃是將你心中本來有的最好的東西引發出來的人。」
我很欣賞這句話,好朋友並不能「給」你甚麼,但他可以在有意無意之間,激勵提升,「引發」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死亡不意味著終結,文章也不見得真能不朽。但我寄望用這幾篇短文,記錄下有意味的生命片段,以感恩懷舊的心情,寫下那隨風而去的友情,超乎平常的悲悼之外。
彭 歌 二○○九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