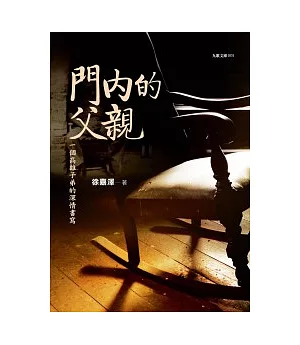推薦序一
我父之子 周芬伶
前些日子無意間聽到學生在聊一部直譯叫做「好傢伙,壞傢伙,怪傢伙」的電影,原本乍聽之下,以為那是義大利西部片時期的巨作「好傢伙,壞傢伙,醜傢伙」,沒想到追問之下這才發現這部「好傢伙,壞傢伙,怪傢伙」,是這兩年來韓國電影向西部片的諧擬致敬之作。
以往對文學的審美標準,如同「好傢伙,壞傢伙,醜傢伙」的片名一樣,追求的是善惡美醜之辨,後來美醜的標準被打破變成了怪,醜傢伙被怪傢伙取代,介入了善惡的二元,這股趨勢,最後形成了一種五分悲傷三分好笑兩分無語問蒼天的新風格。這些抱持著新審美趣味的作者,一方面迂迴的干擾著具有父我威嚴的文學典範,一方面也希望能以偽裝的姿態來杯葛我父。
這些期待自己能開展出新風格的作者,有些喜歡用寫手來稱呼自己勝過作家,很多都是聰明早慧,而且勤快於寫作,也認真。他們不排斥常參加比賽與同好切磋,也從不吝於與陌生人分享自己生命種種的私密角落,他們不只在學著表達自己,同時更在尋找一種適合那種表達的聲音。這些作者,有些跟東尼瀧谷一樣,靜靜躲在角落裡雕刻文字,他們表面上看似嫩呆,內心世界卻猶如一座世故迷宮,尋常人有進無出;而另一些則對於敘事與情節的轉折,卻顯現出極佳的敏感度,好替生活說故事。
認識徐嘉澤是在去年的聯合報散文獎的決審上,當時雖然很多人認為他的參賽作品〈有鬼〉的小說質地太強,最後還是因為文章中對父子情結與社會時勢,帶點黑色幽默的細膩刻畫,得到大部分評審的青睞。
延續著〈有鬼〉的父子主題與敘事功力,徐嘉澤這次出的散文集共分成兩卷,第一卷著重在描寫父子關係與男性的家族暗史,如〈有鬼〉、〈繭〉或〈無聲的舞台劇〉。用「有鬼」二字來形容整個台灣男性的家族暗史,似乎也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一對心裡有鬼的父子,彼此壓抑得連對話時的換氣都不順暢;或一對父子心裡有鬼,並肩走在南北的路上,卻總在盤算著東西。
這些似乎是台灣父子難以面對的真相。尤其當父子之間的代溝,已經從傳宗接代的基本消費問題,擴張到了性別認同的難題;此外,對於新一代文學的寫手而言,又將如何回應那些如父的經典?
卷一中許多篇散文如〈魔芋之丘〉、〈鐵匠的家〉或〈有鬼〉啟用了第二人稱觀點或魔幻寫實的書寫技巧,一面操著祈使口音,一面運用幻術將人催眠,疏離無聲的空鏡頭長鏡頭很多,既介入又在旁觀看,像一群迴游的魚。而近年來越來越受重視的民俗與地方書寫,偕同家族記憶的地理連結,也同樣展示在〈我的戲偶人生〉、〈無聲的舞台劇〉或〈沿著綠川街〉 等文之中。
本書的第二卷表面上是輕盈的城市書寫,實則側寫生命的諸行無常。
在〈我的小船長們〉或〈給見耑法師的一封信〉等文中,同屬家庭另外一半成員的母親與其他女性,在這裡多了一些出場的機會,希望將來我們能擁有更多認識她們的機會。而在集子的中段如〈靜默的高中時光〉或〈他們,曇花般的人生〉,作者帶著一點人情味的語調,同我們緬懷了他的學生時代與目前任教的生活困惑。
有趣的是,書的後半段筆鋒一轉,開始出現了一些與前面題材性質相異的性別書寫。好像過去真實的河流逆游而上,慢慢進入縹緲的未來,流入了一座潮溼虛構的平原。後面這些散文的主題,在時序上,似乎正好倒著迎頭趕上徐嘉澤上一本小說集《窺》的開頭。
如同受尼羅河滋養的埃及人,總是習慣將位於北部的尼羅河下游視為南方,記憶它有時也會如此的抵抗著現實的秩序,如調皮的男孩般撥亂了父親的時間。我們不妨將本散文集當成前作《窺》的濫觴,兩本書以虛實閃回的方式,交代了男孩的身世之謎,我們得以回溯的方式重新去認識一位男孩從父輩轉成母系,從社會回到家庭,由異性反望同性的心路歷程。
身為一名女性,其實我並無法完全理解男性的這種父子情結,倘若有人笑我對男性是如此無知,那也可能是因為我想長保這份好奇。但有時想想,記憶就像是一個結,當我們想把它解開時,卻常雙手不聽使喚,竟將它繫綁成另一個樣貌。也許當我們穿梭在這些明寫父子、暗寫性別的虛實閃回之間,自己所能期待的,只是在轉身的盡頭,看到彼此的背影。
.本文作者周芬伶女士,曾獲中山文藝獎,現為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跨足多種藝術創作形式。著有散文集《絕美》、《戀物人語》、《周芬伶精選集》、《青春一條街》等;小說《妹妹向左轉》、《影子情人》、《粉紅樓窗》等。
推薦序二
像皮球一樣彈跳的徐嘉澤 李儀婷
第一類接觸
在我真正認識嘉澤之前,我的耳朵先認識了他。
「徐嘉澤,是徐嘉澤,我要去跟他要簽名!」
二○○八年,我擔任耕莘搶救文壇新秀文藝營的導師,在營隊開始之前,輔導員在分組名單中,偶然看到了「徐嘉澤」這三個字,然後輔導員就像粉絲看到偶像那樣,大聲尖叫,然而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樣的含意。
營隊開始後,學員自我介紹,我發現讓輔導員尖叫的嘉澤,就恰好分到了我這組,於是我悄悄地留心他的言行舉止,想要探究他究竟藏著什麼不為人知的舉動,能讓輔導員對他為之瘋狂。
嘉澤在自我介紹時,他說:「大家好,我叫徐嘉澤,我住高雄,在屏東教書,喜歡寫作,我會來參加營隊的原因想認識更多寫作的朋友。」他說話時,臉上還帶著一抹奇特的靦腆笑容。那時,冷風從教室窗戶的縫隙中吹進來,冷風不冷,以一種奇特觸感吹撫著大家的心房。
「徐嘉澤」這個名字,直到營隊結束後,我才在記憶昏黑的角落,想起了幾年前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的名單中,寫的就是「徐嘉澤」這三個字。
熱情+努力,威力大於原子彈
我並不是故意要將嘉澤排除在我的記憶之外,只是人的記憶就像畫作一樣,是以一種被動的方式在累進上色,因此不管透過眼睛或透過耳朵,都必須一次又一次的讓人看(聽)見,然而當年的嘉澤,在得了時報文學獎之後,卻銷聲匿跡了好幾年。
營隊結束後,按照往例,導師必須推薦優秀的學員進入耕莘寫作會,作為文學種籽培育的對象,當時我的第一瞬間,當然浮起了嘉澤的名字,然而緊接在他名字之後跑進我腦海的,卻是他住在距離台北城將近四百公里的城市─高雄,換算火車車程,大約是5小時的距離,這樣一個世俗的距離,幾乎要成為放棄推薦他的理由。
然而事實總是遠遠超乎一般人所想像,因為當他第一次參加耕莘寫作會例行的作品賞析活動時,他說:「在高雄,我只能把作品給我姊姊看,以及一些不喜歡寫作閱讀的朋友看,那種感覺真的很寂寞,我很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讓我來到這裡,為了能和更多的寫作伙伴在一起,高雄和台北的距離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遠,所以我一定會常常來台北和大家切磋寫作。」
在那之後,嘉澤果然兌現了「高雄和台北一點都不遠」的說詞,在每次寫作作品討論會中,都可以看到他樂此不疲參與討論的身影。
在那之後的一年內,嘉澤開始以大規模地殼翻身的姿態,吸引了各大文學獎場域的目光,並且在二○○九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窺》,這證實了一件事,熱情加上努力,威力將會大於原子彈。
推己及人的寫作約束力
不能說嘉澤的寫作能力是在進入寫作會才培養成型的,那對他是一種恥辱,如果非要說他的大量得獎,與進入寫作會有著什麼樣勉強的關連,那麼我相信,那肯定是同儕一起寫作環境下,所產生的壓力推擠發生了效用。
然而在推擠效應發生之前,我先發現了一件我鮮少在年輕創作者身上看到的特質,那就是嘉澤出乎我意料的是個嚴格執行寫作紀律與時間進度的創作者。
不知道是工作還是性格的關係,他會將要寫的稿子,訂定寫作進度與完成時間,並且幾乎是以一種特快車的方式,不時地超前進度表,因此每篇稿子完成時,幾乎都距離他要投稿的時間長達半年以上,那對一個創作者來說,擁有著絕佳完美的審視和修改的時間,就像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在書寫長篇小說之前,總會先去練習長跑,儲備足夠的耐力與體力,因此嘉澤在寫作上,幾乎可以說擁有著寫作的完美體質。
然而這樣的嘉澤,繼時報文學獎之後,又掄下聯合報散文大獎之後,一邊思考著自己未來寫作方向之餘,一邊還卻不忘叮嚀同儕的年輕寫作者,一起共同努力創作:「大家不要偷懶,快寫作!」這是他現在掛在嘴上,最常說的一句激勵同儕創作者的話。
嘉澤將自己對創作的熱忱和執著,不僅表現在自己身上,更將此熱情回饋了寫作會這個團體的成員,就像一顆皮球一樣,拍面壓力越大,彈跳得越高,這是當初推薦他進寫作會時的我,始料未及的意外之喜。
嘉澤的首部個人散文集,也將於二○○九年出版,在創作的這條路上,我相信,從今而後,「徐嘉澤」這三個字,再也不會被任何一個人給輕易的遺忘了。
.本文作者李儀婷小姐,東華大學英文創作研究所畢業,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著有短篇小說《流動的郵局》、情欲小說《十個男人,十一個壞》。
推薦序三
與當下為友的書寫 徐譽誠
─關於徐嘉澤
關於凝看嘉澤的作品與人,我心底總有莫名的複雜感受。
那或許是因為:以各方面來說,我與嘉澤都算是頗為相似的寫作者。包括我們的實際歲數與寫作年齡(甚至姓氏),包括我們在文學路上的學習背景,最為疊合的,是我們共同關心的議題與書寫內容。這回細看嘉澤的散文作品,雖未細聊過往究竟,但心底推想:我們的家庭環境、成長過程,甚至感情經歷,應也大致相像。
因為兩人的相似背景,使我閱讀嘉澤作品時,總像在凝視另一組平行時空內的自己,書寫著屬於各自時間軸的悲歡喜樂;感覺如此陌生,轉瞬間卻又如此熟悉。那彷彿從同一路徑來的兩位旅行者,至某一山腳岔路後,選擇不同攀登方向前去,而後至半山腰隔著山谷遙遙觀望:那時若自己選擇的是另一個決定,在這個當下,面對的會是什麼不同風景。
譬如說:位在敘事盡頭的,那些溫暖與光亮。
嘉澤在第一本小說集《窺》中,將內文短篇分為「純愛」與「情色」前後兩輯。面對如此二分,我一如往常難以自制地從後輯「情色」開始閱讀,但映入心底的,卻滿是「純愛」感受,幾乎以為自己誤反前後篇章順序;回頭閱畢全部,始知情色、純愛僅為劇情表相,並非二元對立或互為裡外,它們較像是原始材料,由一股對於良善價值的堅定信仰,貫穿其中。於此特質,作家前輩潘弘輝為該書撰序時曾提及:身為一個好小說家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以人世之眼,描繪生之浮世繪、慾之修羅場,而心生慈悲。嘉澤在自序內亦曾言:「在這些小說裡,我希望裡頭主角可以多一點希望一點幸福,儘管微薄也可以溫暖人心。」
怎麼做到的?我是指:在那些實際的生命經歷之後,還如何能夠願意相信?
這般疑惑,在與嘉澤本人相處時,感覺尤其明顯。此次閱讀嘉澤將集結成冊的散文作品,亦有同樣感嘆,且或因散文本質更易直接了解創作者內心,也可能是我有稜有角的人生觀終於隨年歲增長而漸趨圓滑,這回心底竟有自己或許根本問錯問題的體悟。
仔細推敲,當我問:「怎麼做到的?」本身其實已意涵:怎麼由「某種狀態」進入「另外一種狀態」;由「A點」移動至「B點」。但,什麼是A點?可以確定的是:A點必然與過往回憶相關,且不是絕對值,是由回頭觀看時所選擇站定的位置去相對決定;如同大多數人經驗:在不同年紀回頭觀看某一時期的往事,總會得到不同的理解內容。A點是會變形的幻影,即此時此刻我們對於自己所想像定義的某種姿態。
大多數的文學,無可避免地是以曾經存在的過往為書寫基礎,尤其散文與小說(差異較遠的是詩;詩感覺較接近未來)。此特性與攝影相近:當快門按下,景框內的時空畫面即已註定成為過往;以本質而言,都是悼亡。而當悼念的內容,總是隨著我們觀看位置有所異動時,那麼,在書寫當下所描繪的那個A點,反映出來的究竟是什麼?那真能代表過往、如實重現?或者,只是對於某種狀態的執迷難捨、徘徊留戀?進一步說:當被書寫的A點模樣,總是萬事難解的苦痛姿態,那是否只代表位處當下的創作者,還不願從過往的痛楚感受中離開?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回味?甚至過度雕琢,成為某種表演?
依此論述來看:A點屬於過往,但總以「當下」的形式被召喚顯現,意即:A、B兩點其實互為疊合;換句話說,A點並不真正存在。所以我當然是問錯問題:並沒有所謂的由「某種狀態」進入「另外一種狀態」,只有當下的你,將此刻的自己定義為什麼狀態,如此而已。
嘉澤在散文作品〈藍色筆記書〉中,曾對自己創作提出如此疑惑:「我開始模糊了自己的人生,哪裡才是真的?哪裡是幻想的?」句後敘述所表喻的,是個人經驗與同志書寫歷史的混雜融合,如文內所言:「這是我自己的寫照!也有可能是你的!」以小喻大,某種揉合個人與整體的同志生存姿態之片段歷史,透由書寫因而存在。但,那被反覆描繪的姿態,代表什麼?或以上段推論的邏輯來問:什麼是A點?倘若A點並不實際存在,倘若真相只存在每個人自己心中,那麼書寫內容是真是假,或許都已不是重點;重點可能是:內文個體字句所匯集出的箭頭形狀,正朝向哪一遙遙遠方,默然指去。
我以為:始終能將各篇章的敘事文字,凝聚成對於良善價值的堅定信仰,清楚指明未來安樂境地之行進方向,便是嘉澤作品中最具價值的地方。過往發生的一切,無論歡喜傷痛、光明黝暗,至嘉澤手中,均可轉化為極具養分的因,而後結累出良善之果。這或許也是嘉澤屢獲文學大獎的原因之一:評審們在這些文本中,見到某種能與閱讀者內在本體互相呼應的「初衷」;並非指作品能多貼近真實或者人性,而是指能多符合一開始我們都想達到的簡單目標:不要再有傷害、讓無止無盡的恩怨輪迴就此止息。這般創作,與充滿文學機巧手法的作品相比,無疑是較具處世智慧的。
我在嘉澤作品中,體悟到創作的某種功能或許在於轉化因果,而創作者與書寫的關係,或許不只是追述回憶、重建過往的龐大工程,且在於定義當下、體驗當下,甚至是:成為與當下和平共處的重要媒介。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倘若讀者能夠明瞭創作者的慈悲初衷,自然會對該文學作品心生感動。
就文學書寫而言,「與當下為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嘉澤的作品卻已經達到此項目標。但願如此的書寫,能夠獲得更多的讀者認同;畢竟,這世界若再多幾個像嘉澤這樣時時刻刻開開心心的積進人物,或者說,文學界再多幾個像嘉澤這樣的陽光男孩,結果應該都只會更好;至少就我而言,會是增加不少心理輔導師的選擇對象,也該算是一件讓人愉悅之事吧!
.本文作者徐譽誠先生,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畢業。作品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寶島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著有小說集《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