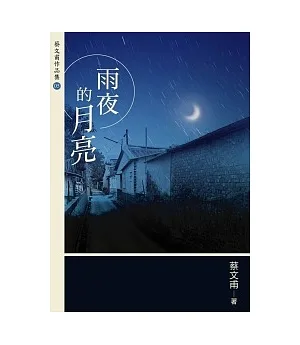愛與恨交織的情網──《雨夜的月亮》扣人心弦
蔡文甫的小說《雨夜的月亮》形式與內容並重,是一部十分傑出的長篇創作。早在今年七月九歌斥資重印之前,這部小說已由皇冠印行兩版,可惜我一時查考不出皇冠初版日期,無法得悉完稿年月(編校:皇冠初版日期是五十六年八月)。但由其他細節看來,小說的時間背景,應該在民國五十五年到六十年間的某夜。此時,正值台灣經濟衝破層層瓶頸,邁向高度繁榮之際,于雲雷踩踏的三輪車在街頭逐漸式微,唐升辰、黃兆蘭母女代表的拜金力量日漸茁壯,葛華達的大型企業制度建立不久,而台北大學生的世界,也由單調貧乏一變為充滿舞會耽樂的現象。這些種種,儘管不是蔡文甫主要的關懷,可是和故事息息相關;主人翁之一的劉培濱所以走投無路,原因之一即在喪失金錢以及拜金人物對他的打擊。
劉培濱早有妻室,但年輕時仗著富有,風流成癖,到處留情。故事開頭的于雲雷,是他和一酒女同居後的結晶,其後的唐升辰與黃兆蘭,一是于雲雷的同母弟弟,一是異母妹妹。由於劉培濱早棄骨肉不顧,離「家」出走,三個子女散居各處,彼此均不知相互關係。于雲雷由企業家葛華達收養長大,刻苦耐勞,個性剛直。唐升辰進入富家為養子,放蕩成性,儼然利祿之徒。黃兆蘭則深受母親影響,重視金錢,富於心計。故事起迄時間可能不到十二個時辰,僅僅一夜而已。劉培濱現身之時,已然垂垂老矣,體弱無錢,流落街頭,尋訪舊日親友。他的尋訪過程,同時參合三個兒女彼此之交往,以及于雲雷、葛強妮間之戀情,十分複雜。故事本身結合無數巧合與意外,但結尾時,由於作者的人生觀與道德感,免除可能形成的亂倫悲劇。
作者顯然非常重視小說技巧。事實上,一部長達十五章、三四四頁的小說,只描摹短短一夜發生的事件,也非出以高度技巧不可。在這一夜陳述中,作者藉倒敘、客觀鋪陳,以及時空交錯等手法來發展他的故事。一開始,他即苦心孤詣雕塑作品的整體氣氛:雨絲像一片巨大的網幕,緊緊罩住每一個片斷、每一位角色。陰鬱低沉的氣氛,正合乎故事之要求;錯綜複雜的情節,即如空中錯亂紛飛的雨絲。雨夜不但意味著老來頹唐的劉培濱的心境,也象徵三個子女的懵然無知。作者藉著繁複的技巧,把劉培濱和子女們的命運揉合在一起,再賦其自己的人生觀照,終於演發成一部扣人心弦的傑作。
懸疑的效用在小說中得到高度發揮,而且在開端第一章就緊緊攫獲讀者的注意力。于雲雷承葛華達一家恩惠,女公子強妮對他又一往情深;但這一切阻擋不了他執意離開葛宅的企圖,對恩人他甚且露出乖違常情的憎恨態度。于雲雷的個性固然可以解釋部分原因,但寄人籬下與恩情的束縛尚不足形成尖銳的「恨意」,表面之後必然有更強烈的理由。作者開頭留下這個懸疑後,筆鋒陡然他轉;在第十三章之前,此一懸疑及強妮、雲雷之關係,即一直迫使讀者往下探究故事。不錯,懸疑的擺設無法不使小說流向通俗的情節劇的形態,同時含有濃厚的生意味道,但作者的文字與敘述技巧適時扭轉此一傾向,未嘗不可看作成功之處。況且,懸疑揭發時,它的理由──葛華達加諸于雲雷的性變態──在中國人的道德觀念裡,確乎足以令人產生恨意。
葛強妮在小說中是一位難忘的角色;她個性強烈,敢恨敢愛,動作又復鮮明,恰與劉培濱的平面敘述相反。她對于雲雷的激情,在全書陰晦氣氛中特別顯眼,足令讀者烙下鮮明的印象。作者塑造出這位動態人物,甚至使小說結構產生動搖。按照董保中先生的看法,劉培濱和于雲雷的願望發展,係小說主要的情節,而于葛關係不過是支輔的次情節之一。可是,在故事結尾前數章中,我們發現葛強妮追求于雲雷一事,似乎重要性已超過主情節。劉培濱的命運不再是讀者最大的關懷。此一現象,我認為,主因在作者對劉培濱的敘述過於平面,而且他的一生實在引不起我們的同情,注意力因之減弱。再者,于雲雷尋求的動作由於鄭天福無惡意之阻撓,顯得不十分積極。父子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就不甚重要。主情節誘惑力一失,相對的,于葛之間,由於強妮個性雕造得相當凸出,這一份浪漫的情愛,反而在讀者內心形成極其強烈的撞擊力了。
《雨夜的月亮》布局富於巧合性,削弱小說的寫實色彩不少,難怪董保中先生在︿《雨夜的月亮》中兩種人生經驗﹀一文開頭,甚至急於否認小說的寫實性了。其實是否寫實,倒無關緊要,高明的小說家永遠不受特定文學流派的限制。我對這部小說的看重,除作者的技巧外,作品表現的人生觀亦是要因。蔡文甫先生透過一連串戲劇化情節,目的似乎要告訴我們:命運不是盲目的,有其因故有其果。劉培濱終不獲善終,就是例子。
──六十八.十二.四《中華日報》副刊
本文作者李奭學先生,文學評論家,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譯有《閱讀理論》及著有《書話東西文學地圖》、《書話台灣》、《書話中國與世界小說》,另編有九歌版《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二)評論卷》(與李瑞騰、范銘如合編)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