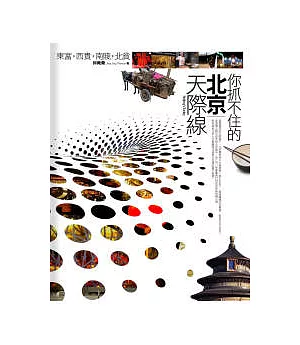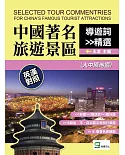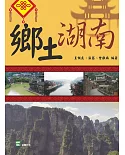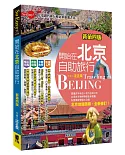作者序
那是一個trigger。
是的,trigger。這是個再恰當不過的詞了。對不起,因為一時在中文裡找不出什麼合適的詞,我只好借用英文,幸好地球村形式,整個世界早已不見母語與非母語的界限。將trigger中譯,字面上的意思是,引發,引爆器;或是由某些積蓄已久的事情引起反應(或一連串事件)的行動(或衝動等)。
二○○六年夏天的一個溽熱的下午,我們一家人在前門大街尋找全聚德烤鴨店的時候,突然意識到事情變得有點兒不那麼對頭。
這一切發生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絕,如此讓人措手不及。
真的是讓人措手不及。
如果那天我的兩個孩子不嚷嚷著要吃烤鴨,如果我先生不在附和之後提議去前門的全聚德吃烤鴨,如果我們到了前門大街後如願以償地吃上了烤鴨,那麼就不會有什麼「以後」了。
也自然,沒有「以後」,也就沒有接下來的動機要寫今天這本書了。
當然,這樣說也不那麼完全準確,人們不是完全沒有看到了周圍很多事情正在發生變化,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
近百年來,北京變得越來越像東京,越來越像紐約、香港、芝加哥等國際都市,玻璃帷幕的摩天大樓,寬闊平坦的行車大道,櫛比鱗次的商業大廈,彷彿一個恍惚,那個明黃色琉璃瓦上覆蓋著冬天厚厚的積雪和散發著烤白薯焦甜氣味的北方古都,便悄然而迅速地在人們的記憶裡,漸行漸遠了。
儘管我一直都住在國外,可我每年暑假回北京旅行的時候,都會吃驚地發現,北京正逐步變得不那麼北京了。
只是這種發現僅僅停留在感受的表層,還混合著些許沾沾自喜。
看到自己從小長大的城市開始變得時尚、繁榮,似乎自己的臉上也無形中塗上了一層光彩。
事實上,我們那天到了前門以後,並沒有吃到烤鴨,也沒有去到全聚德烤鴨店,而是還沒有推開出租車的門,便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OMG – Oh my
god!整個正陽門對面的東西兩側被粗糙搭建起來的巨型圍擋鋪天蓋地地遮掩著,已經在推土機的碾壓下變成廢墟和正在變成廢墟的老舊建築頹廢地四處散落,等待拆遷的大小店鋪在「血本無歸」的拍賣橫幅旁起勁地向路人兜售商品,乘機搶購的顧客拎著大包小包在人群中忙碌地鑽動,整個前門大街如同大難臨頭似的顯示出一派世界末日的衰敗景象。
我們不知所措地尋問路人,被告知,「連這都不知道。前門大街要進行大規模改造啊。」
方才恍然大悟。隨即又茫然,接著問,「大規模改造?那麼商店都關門嗎?全聚德還營業嗎?」
路邊馬上有人插嘴,「還營什麼業。都拆了。」
「那去哪兒吃烤鴨呢?」我們的孩子仍舊念念不忘此行的目的。
「有很多地方可以吃烤鴨呢。」路人全樂了。「你們是第一次來北京吧?如今在北京,吃烤鴨不僅僅去全聚德,有名的還有九華山,金百萬,利康,小王府,大董,長安壹號。」
「長安壹號?怎麼聽起來像是一艘火箭?」我沒敢聲明自己就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因為這些年北京的變化實在太大了,我不僅常常辨不清東西南北,而且還隔三差五地到處迷路。有一年回國,我甚至連我爸爸住的樓房也找不到了,原因是為了美化城市,他們住的那片住宅建築一律漆成了暗紅色,於是眨眼功夫,整個小區的原有相貌便面目全非了。我的一位從娘胎裡生下來就住在北京,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城市的朋友告訴我,別說是我這個背井離鄉的人,就是她,若是一年沒怎麼出門逛商店,也會徹底認不出某些曾經非常熟悉的地方。
我不得不相信,那些從外省各地遷徙到北京來的「北漂一族」,恐怕比我更認得北京呢。
「長安壹號就在王府井東方君悅酒店裡。火得很呢!」一個操著江南腔的平頭小夥子熱心地說。
就在王府井?既然如此,我先生說,不如去那兒,因為兒子正好要去王府井書店買書,一舉兩得。
我說不出什麼反對的理由,況且第二天就要乘飛機回荷蘭了,如果今天下午吃不上烤鴨,那意味著至少要等到明年度假回來的這個時候。於是便全家去了王府井。
自然,我們吃到了烤鴨,很美味,很滿足,但是心裡卻隱隱著一股說不出道不明的遺憾。是因為長安壹號?還是因為全聚德?還是因為前門大街?
我也不知道。
「長安壹號」無可挑剔。除了那名字,我無論如何也很難將它那或武器或坐標式的稱呼與香酥脆亮的烤鴨連繫到一起。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對它的深刻印象。
我確實喜歡它裡面西洋式開放廚房的設置。優雅的棕色和白色為主打的室內家具,剔透的玻璃隔牆裡通紅的爐膛和跳躍的火苗,襲人的香氣誘惑地彌漫在廳堂的每一處角落,衣香鬢影的人們正襟危坐淺酌慢飲,笑容可掬的侍者嫻熟地片出脆嫩的鴨肉並且同時娓娓道出它的來龍去脈,這使我不由得聯想到前年在法國銘悅酒莊裡,那為我們開啟香檳的面孔紅潤的年輕人,也是同樣的殷勤,也是同樣的親切,也是同樣的訓練有素。
那鴨子烤得恰到好處,不肥不瘦,柔韌有餘。配上凝脂般的甜麵醬,糯軟的薄餅,大紅漆盤托著的綿細白糖,精心切好的黃瓜、蔥絲、蒜泥,全都精心設計得讓人忍不住讚美。
可我心裡還是覺得有什麼不大對勁。
北京。
民國的時候叫做「北平」;清朝的時候叫做「京師」;明朝的時候叫做「北京」;元朝的時候叫做「大都」;宋遼金朝代的時候叫做「燕山府」;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時候叫做「幽郡」;秦漢朝代的時候叫做「廣陽」;春秋戰國的時候叫做「薊城」;史前的時候叫做周口店山頂洞人的「亂石崗子」。
從亂石崗子到氣勢恢宏的都市,北京經歷了五十萬餘年緩慢而又令人眼花撩亂的變化。山巒漸次趨向緩和,河流逐步蜿蜒匯集,大片大片的坡地被一代代飢餓的定居者開墾和占有,成群的房舍以令人驚奇的速度向四面伸展,縱橫交錯的街道宛若迷宮一般變幻莫測,斷斷續續的圍牆層層相護此起彼伏,然後有了城池,然後有了廟壇,然後有了宮闕,然後在迄今為止七百多年前的時候,從北方的大漠遊牧草原崛起的蒙古帝國,長驅直入占據了中原領土,建立了新一輪的統治王朝,規畫了新的國都,同時構架起了一條貫穿整個城市正心的中軸線。
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現存的最長的城市中軸線。
當然,巴黎,華盛頓,坎培拉,紐約也有中軸線,但它們都沒有北京的中軸線那麼綿延、那麼筆直、那麼中庸。
由南往北,中軸線上共有二十一座跌宕起伏的建築,依次是永定門、正陽門、大明門、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門、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神武門、景山門、萬春亭、壽皇殿、地安門、鼓樓、鍾樓。浩浩蕩蕩,前呼後擁。
中軸線的正中是皇帝和他的後妃們居住的地方,顯然,此種設計迎合了「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理念。這個被世界公認為最宏偉的皇家住宅,實際上是由無數的精緻的小四合院組成的巨大的四合院聯體宮殿,占地七十二萬平方米,周邊圍有森嚴的紅牆和四座高聳的城門,以及蕭瑟的護城河。歷時五百多年,中國最後兩個封建朝代的二十四個皇帝,在這個曾經被稱為「紫禁城」的皇宮裡度過了綺麗而又沉重的歲月。
護城河外面是皇城。以中軸線為界,左邊是太廟,右邊是社稷壇,後邊環繞著景山,北海,中南海等皇家禦園。其間隔部分遍布有管理皇家事務的眾多衙署和倉儲。據說在明朝時,曾經住有十萬多的太監和宮女,即使在清朝,也有四萬多宮廷內侍,終日忙碌於眾多的御用作坊和庫房裡。然後圍攏著皇城的是又一層壁壘森嚴的城牆和七座重兵把守的城門。
皇城之外,同樣以中軸線為界,是兩側如棋盤般齊整的街道胡同和排列對稱的青磚灰瓦的四合院民居,數以萬計的臣民百姓們,世代相安居住在一起,這就是老北京的內城,安全地包圍在周長二十四裡的城牆和九座敦實的城門的護衛之下。
內城之外,明朝的時候,又擴建了一圈外城。更多的街道和民居依然以中軸線為界,向東西兩側大面積地伸展出去。稍遠之處,是歷代皇帝每年冬至和夏至時分祭天祈穀的天壇和先農壇,曾經空寂遼闊。而後數百年之間,御道兩側逐漸開闢出來越來越多的熱鬧的街市:豬市口、鮮魚口、煤市街、糧食店、布巷子、觀音寺、珠寶市,以及銀號、錢莊、茶樓、旅店、飯館、戲園、妓院、各省會館,一度成為京師最繁華的地方。外城的城牆和七座城門,比起內城的略矮,用來鎮守北京。
這就是北京古城。
若是從空中俯瞰,它呈現出來的是非常整齊的格局,正北,正南,正東,正西,相互垂直,結構清晰,井然有序。
據說,這是七百多年前策畫城市設置時,依據古書《周禮.考工記》中「皇權至上,宮體為主」的準則,規範出來的。
古人的思維顯然自成邏輯。
中軸線最北端的鐘鼓樓,每當日暮時分,便傳出巨大而有規律的報時聲,內城和外城的十六座城門,遂在這鐘鼓齊鳴的悠長迴盪之中,將鍍銅鉚釘的雙扇大門分三次緩緩關閉。正在趕路的行人和馬車,於是匆匆加快腳步穿過城門,直至最後一次鐘聲,城門徹底合攏,交通漸漸終止,隨即開始淨街,然後全城陷入一片寂靜。
難怪,那時候沒有電燈,沒有電影電視,沒有夜總會,沒有歌廳酒吧,甚至沒有鐘錶,到了晚上,四周漆黑,在微弱的煤油燈伴陪下,實在也十分掃興,無事可做,自然就早早上床睡覺了。
所以那時候人的睡眠比現在充足,精神頭兒大,天剛亮就起床了,起床時聽到的第一個聲音,便是鐘鼓樓悠悠迴盪的鐘聲鼓聲,接下來所有的城門又重新開啟。趕大車的,挑擔子的,騎毛驢的,牽駱駝的,熙熙攘攘鬧鬧哄哄開始上路。城市重新甦醒,又開始了另一天的生活。
這是一幅多麼田園式的圖景。人們日升而出,日落而入,在悠遠蒼涼的鐘鼓聲中,過著周而復始單調而又平靜的生活。
可惜,這樣的情形,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了,已經永遠定格在發黃的黑白老照片裡了。
就像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十有八九都不盡人意。
自從上個世紀初以來,北京老城就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
先是延續了六個世紀的鐘鼓樓的報時聲音,隨著清朝最後一位皇帝被驅逐出紫禁城後,不宣而告地終止了;然後是中軸線上莫名奇妙地拆除掉了三座巍峨的建築,以及四周的城牆和城門不由分說地被陸續轟倒推平;接下來是古老的胡同和四合院瀕臨大面積的拆毀……而變化的理由,是為了讓道路寬闊平坦、為了讓鐵軌任意伸展、為了讓高樓遍及各個角落、為了讓周圍更加乏味無趣,於是,近百年來,北京已然再不是北京了。
我知道,我是在想念過去那北京老百姓們曾經最熟悉的「燒鴨子」。那配著大塊糖漬蒜頭、清白蔥、手(手幹)餅、老黃醬,以及棗木灸烤出來的焦黃迸脆的烤鴨,外加用青口白菜熬煮出來的濃郁的鴨骨湯,一股腦兒的在人聲鼎沸的老館子裡熱熱鬧鬧吃喝起來的地道勁兒。
我為前門大街全聚德老店的關門遺憾、為正在改造的前門大街遺憾,不知道在它們改頭換面之後,會是怎樣的一幅情形?也許比以前更好、也許比以前更壞,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再也不是原來那個百多年前建於明朝時的老前門大街了。
就像此時此刻在「長安壹號」裡料理出來的鴨子,好看、好吃,卻是另一種意味的好看好吃。
然後我突然意識到,北京城裡正在發生著某些讓人始料不及的變化。這變化其實早就發生了,只不過我一直都沒有在意,然而如果我再不在意,這些變化便很有可能從四面八方迅速淹沒過來,徹底地改變這個我曾經生活過的城市。
於是我想到了我蹣跚學步時住過的城北的狹窄小胡同、幼稚童年和青澀少年時住過的城南的曲折街巷、入社會工作後每天騎著自行車路過的覆蓋著濃密樹蔭的城東的寬大馬路,以及讀大學時……那些過往的點點滴滴。
如今它們都還在嗎?
我怎麼以前從來都沒有想過,回這些地方看看呢!信不信由你,這些年;我是說離開中國這二十年,甚至,離開中國以前,從我長大搬過幾次家,離開過去曾經住過的老房子老胡同以後,就真的再也沒有回去過。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概是這些地方我早已將它們埋藏在記憶深處,沒有trigger,它們就一直默默無息地塵封在那兒。
好在,冥冥之中,它們忽然躁動起來。
於是二○○六年夏季,暑假最後一天的傍晚,坐在「長安壹號」舒適的短靠背軟椅上,酒足飯飽之後,對著窗外的長安街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象時,我開始認真盤算起來,明年再回北京,一定要安排時間到我過去曾經住過的地方去看看,不然的話,也許就會像剛才我們在前門大街面對的景象那樣,我過去的生活軌跡很可能在推土機的碾壓下,徹底地消失了。
我不能再猶豫了。
誰知道以後再回北京的時候,周圍又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奧運會加速了北京古城脫胎換骨的速度,中國執意要向全世界展示一個經過重新打造過的現代化的閃閃發亮的國際大都會。
而我,也要執意去做的,是盡量趕在這之前,去看看那些我過去生活過的地方。
不光為我自己,還為了我的那一雙兒女。他們有一半是中國血統,所以不管怎麼說,他們應該知道更多一些的自己老祖宗的背景。再說他們也許會對那些老胡同老房子感興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