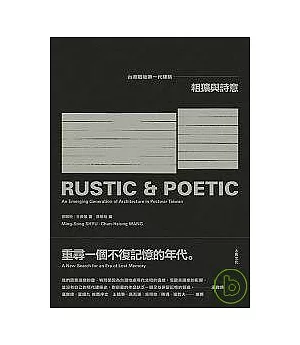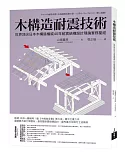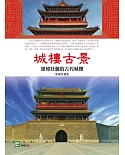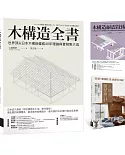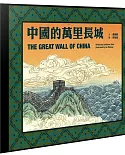序
首先,《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Rustic & Poetic: An Emerging Gener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Postwar
Taiwan)一書,以我所知,原來被出版社將書名誤寫為《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大師》,並邀我寫序。本書是建築史研究的資料收集工作,寫序是件榮耀的事。可是,有些關於建築史的方法論問題,還是需要先做提醒,也就“以發問為序”。目前,出版社已更正書名,我的質疑也失去了前提,不宜再做為序言,或許,原序言改做為書後代跋,也還有些建築史研究的提醒意義吧。
若書名稱為《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師》,“建築師”就很恰當了,何須考量市場銷售,稱為“大師”呢?或許,作者們認為書中不能窮盡所有建築師,所提到的建築師,皆為大師。以大師相稱,為示尊崇。可是,“大師”(master)這個詞,放在廣告措辭與語言浮誇的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脈絡裡,早就被用得過於浮濫,失去了master技能熟練,掌握全局的手藝“師傅”原意,而成為虛榮的冠冕。相信書中的建築師,有不少實實在在的專業者,並不見得樂意被這個台灣式詞語相稱。一位1990年代之後才出頭的,有些設計能力的台灣年輕建築師早就提過尖銳的質疑:“大師滿街走,台灣卻是這麼醜?”台灣這麼醜,而且不是普通的醜,國家的政策與角色應是關鍵,建築師也難辭其咎,這事倒值得細究。
作者們是在從事建築史的基礎資料收集工作,值得肯定。但是,本書一方面像是“建築師列傳”,一方面又像是“建築物作品”,這是建築史研究在方法論上的黑格爾右翼藝術史遺留,經歷過1960-70年代的社會運動與學院的理論反思,在21世紀很難再回到從前。沒有方法論上的警覺與干預,建築史寫作就很容易不自覺地在鞏固建築師個人神話與專業威望相關連的品牌利益。這樣,就沒有知識的條件來分析書中提到的難堪,僅能以“創作權的尷尬”待之。建築,本來就是一個集體團隊勞動的結晶,而建築師的證照,則給予了制度裡的法定代表人角色。是什麼樣的個人得失之心,造成了尷尬?這就是東海大學教堂的設計,竟在貝聿銘與陳其寬都已年老時,造成兩人間的不快。
其次,若以建築物作品為研究對象,則無法顯現作者們的疏漏,對建築類型視而不見。於是,研究對象泰半為公共建築與機構建築,卻不見民間的住宅討論?建物類型(building type)重要,但終究是功能主義產物,建築類型(architectural typology),或者說,營造類型(building
typology)的思考,可以提供更多的光線。譬如說,台灣社會在1960年代,歷史性地空間商品化而產生的“販厝”,也就是“透天厝”,這是重要的建築類型。它們經由加強磚造,簡易鋼筋混凝土與亂砌磚的技術力量,徹底將台灣的鄉土地景翻攪,成就為台灣民間版的“現代建築”。建築史研究者豈能視而不見?若視而不見,建築史研究脫離台灣社會現實的成見豈不可怕?
其次,四到五樓的步登公寓(walk-up apartment)
,這是台灣都市的重要建築類型,這是台灣都市生活中的城市典型居住元素,難道不是建築師的作品?王大閎設計步登公寓時,每個單元不在腰上設入口,而將動線移至外端,由陽台進入。建築師將共同樓梯的轉折平台調至內側,讓動線由外側入門,於是,使用者轉身至陽台入門之後,身體得以面對正中軸線的設計講究,是考量漢人傳統住宅祖先牌位與中軸線的產物。建築師的用心值得肯定。
至於最近的重要保存運動才凸顯在社會的注意力之中的,陽明山美軍宿舍,見證了1950年代台灣與美國之間的政治關係,這正是軍事與政治對領土的直接支配,也就是帝國主義與殖民依賴的關係,因此,劉自然與台北事件就有了更深層的反抗意義。同時,陽明山美軍宿舍還關係著沈祖海建築師的角色,沈祖海運用日本殖民時期引入台灣的美國鄉土建築元素,雨淋板(魚鱗板,Shingle)構造,建成美軍宿舍,還給他們一種似曾相識卻又陌生的經驗。對美軍宿視而不見,不正吻合了拆除者認為它們是沒有代表性的建物的說詞?
假如不是去政治的思考,又豈能不提到慈湖的仿閩南式建築物?慈湖在1959年建立,1962年命名慈湖,1975年更名為慈湖陵寢。這是1970年代中期。有政治代表意義的建築物。
進一步,中正紀念堂似乎僅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與楊卓成(和睦)條目下提及,似乎有所不足?誠然,中正紀念堂遲至1980年完工,但是,1975年籌備,1977年動工,這正是歷史斷代的不易之處。對戰後台灣的建築史言,這幾棟建築幾乎可以形成政治分水嶺的意義。
在建築史斷代的根本問題上暴露的是歷史的結構性轉化過程,本書基本上是1970年代初期以前的建築物與建築師。簡單地說,這是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之前,都市化所伴隨的都市、區域、與土地政策失控,台灣房地產狂飆之前的台灣社會產物。這些建築師,可以說是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移植(transplanted)台灣的制度性執行者,也是早期的建築專業者。因為殖民時期,輪不到被殖民者擔任建築師,所以稱為台灣的第一代現代建築師亦無不可。這時,我們確實需要歷史研究方法論上的提醒:現代論述的空間化(spatialization of modern discourse),以至於,認識現代建築論述(discourse of modern
architecture)的建構,有助於開拓我們對權力與知識關係的新視野,可以避免將建築論述視為建築師個人意識內在的轉化,這樣,建築的象徵表現也才得以揭示,建築的意義也才得以探討。它們在競爭現代性(contesting
modernity)。這樣,1950-1970年代的台灣建築學院、建築師專業、現代建築論述建構,以及,國家(state)的性質與作用,才會浮現在我們的視線裡。讓我們共同面對我們的歷史,現代建築在台灣的移植過程,以及,現代建築論述與機構(institution)的作用。這樣,我們才會發現,對建築形式與建築自主性的自我呢喃,就會像是說給自己聽的無聊低語。形式主義,追求建築形式的烏托邦,不但是現代建築師的致命吸引力,也是成為其制度共犯的建築評論者同樣的死穴。
最後,值得深思的是,在所謂的粗獷與詩意之外,已經成為當前廿一世紀建築專業者的共同價值觀,保存(conservation, or preservation),為何不曾見於昔日的現代建築先行者的詞語之中呢?這樣,我們才會懂得,最後,現代建築論述的空間化,排除的是什麼呢?傳統的建築與地景,徹底從台灣的土地與時間裡消失了!這是美麗之島成為現代建築的廢墟台灣的早期階段。
夏鑄九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0080920原稿
20080923修改
推薦文
漢寶德
最近的過去
在過去,我們總把歷史視為遙遠的過去所發生的故事。建築史上所留下來的作品如果不是供我們學習、欣賞的經典之作,至少是代表一個時代風格,可供我們憑吊、感喟的史蹟。這種歷史觀在上世紀的末葉已經逐漸改變,歷史已被體認為昨日的記憶了。
這種發展至少有兩個背景力量推動著。第一,時代的腳步飛快的移動,今天的世界在一年內發生的事,可能相當於過去的一個世紀,轉眼間,我們視為現在的,忽然就成為過去,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在我們的一生中,一直不斷的經歷時代的轉變。像古代那樣,時間像凝止一樣的停留數百年,已經不再回來了。建築的壽命大幅的縮短也是意料之事。第二個力量是資訊。今天是資料充斥的時代,實質的世界雖迅速改變,但影像中的世界卻一直存在著。建築可能很快自世上消失,影像卻有意無意的留下來了,使得我們回顧昨日,有記憶猶新之感。
有了這兩個背景的條件,一方面使我們不得不把歷史的紀錄拉到昨日,以免自我們的記憶中消失,另一方面我們也有條件建構一個甫消失的歷史。這就是近年來全世界都重視「最近的過去」的原因。即使是有些國家博物館的收藏政策也因此而改變了。
基於這樣的理由,很高興看到王俊雄與徐明松兩位教授合作完成了戰後的第一部建築史料的紀錄。在台灣的建築史上,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到今天的這一段,一般認為是「現在」,不是「過去」,然而不可諱言的,大家對上世紀中葉的記憶已經模糊了。年輕一代對當時特殊政經條件下的建築,已經完全沒有認識,已經十足稱得上歷史了。不只是年輕人,連我這樣在讀書時就親身經歷的見證者,對那一段歷史也已經逐漸淡忘。我們需要這樣的書,特別是因為台灣地處現代文明的邊緣,受歐美國家的影響,並沒有自己的現代建築史,對前輩的作品缺乏一個足以保留記憶的管道。那個時期的建築,不論有沒有保留的價值,都是我們當代建築的前身,都應該受到我們的尊重。
也許是這個理由吧,兩位作者花費精力,蒐集大量的資料,以保留記憶的心情編這本書,是以作品為主,以建築師的生平為副而寫出來的。這不是一本建築史,因此沒有發展的脈絡與歷史的觀點。這也不是作品精選集,所收納的作品,在建築價值上並不整齊。何況尚包括了若干外國建築師的作品,與台灣當時的建築顯然並無歷史淵源,也無比較的基礎。
很感謝作者以他們研究的精神,為我們收集了這麼詳盡的資料。坦白地說,這本書中呈現的有些作品,我的教書生涯雖活躍在那個時代,也並不熟知。連我自認為很熟悉的王大閎先生的作品,也賴他們的資料彌補缺漏。例如我以前不曾看過他為故宮競圖所作的設計。學者的工作,對學術的貢獻是長遠的。台灣早晚需要一部現代建築史,這本書也許是逐步認識台灣現代建築的第一頁。每一位關心台灣建築的朋友,都應該重視資料收集整理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