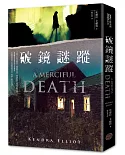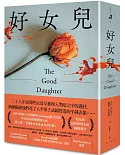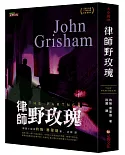旅美華裔作家哈金新作《自由生活》(A Free Life本書是美國國家書卷獎《等待》一書作者哈金2007年長篇新作,特別的是本書是哈金第一次將作品的故事背景搬離中國,直視美國。全書長達三十三萬字,描寫一個家庭不得不離開安穩
,尋求新的國度接受的故事,就像書中的那首詩所敘述的:「你必須去那裡,悄悄地出發。╱把你仍然珍惜的東西留在身後。╱當你進入那個領域,╱一路鮮花將在你腳下綻開。」
哈金讓主角一家身處在沒有親友人際網絡的陌生社會,家人得重新學習獨立,盡力維持生計。但武男始終不肯放棄成為詩人的夢想,後來總算以詩歌從困境中突圍。他在書中有感而發:「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運用自由,自由對你將毫無意義。」
作者簡介
哈金
本名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五年。在校主攻英美文學,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系,1984年獲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1985年,赴美留學,並於1992年獲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學位。現任教於美國波士頓大學。
著有三本詩集:《於無聲處》(Between Silence)、《面對陰影》(Facing
Shadows)和《殘骸》(Wreckage);另外有三本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好兵》和《新郎》;五部長篇小說:《池塘》、《等待》、《戰廢品》、《瘋狂》、《自由生活》。短篇小說集《好兵》獲得1997年「美國筆會∕海明威獎」。他的長篇小說《等待》獲得了1999年美國「國家書卷獎」和2000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為第一位同時獲此兩項美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
《新郎》一書獲得兩獎項:亞裔美國文學獎,及 The Townsend Prize 小說獎。《等待》一書則已譯成二十多國語言。
《戰廢品》一書入選2004年《紐約時報》十大好書。
譯者簡介
季思聰
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89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教育學碩士和圖書館學碩士,現在美國新澤西州某公立圖書館任職。著有《黃金時段的無冕女王》、與他人合著《推動美國的25雙手》、《格林斯潘傳》等書,翻譯獲美國筆會∕福克納獎的長篇小說《戰廢品》(哈金英文原著)。
內容簡介
內容連載
濤濤終於拿到了護照和簽證。幾個星期來,他爸爸媽媽心裡慌慌的,怕中國會閉關鎖國,限制公民出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鎮壓發生,除了聯合航空公司以外,所有的美國航空公司都取消了飛北京和上海的航班。聽到兒子的好消息,萍萍一下子淚如泉涌。她趕快沖乾淨給蘿蔔絲控水的漏鍋,扔下正在做著的海蜇拌蘿蔔,摘下圍裙,就和丈夫武男一起,直奔伍德蘭鎮中心的國際旅行社。
因為沒有提前三個星期預訂,飛機票比正常價要高出七成,但是武男夫婦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祇要濤濤能盡快安全地離開中國,他們什麼代價也不惜。兩人又買了自己從波士頓飛舊金山的雙程票。
萍萍和武男都不能回中國去接濤濤,濤濤跟著外公外婆萍萍的父母過了三年了。萍萍娘家人誰也沒有護照,更別說從美國大使館得到簽證有多難了,這孩子祇能自個兒坐飛機到美國來。萍萍的哥哥是中學物理老師,正好放暑假回到父母家,他說可以把外甥從濟南送到上海,再把濤濤交給空中小姐。濤濤還不到六歲,沒大人陪著,不能一個人轉機,所以濤濤的爸媽一定得去舊金山接他。旅行社那個橄欖色皮膚、長頭髮大胸脯的女營業員,幫武男在聯合廣場附近的一家旅館訂了間最便宜的房間,一家三口在返回波士頓之前要在那裡住一夜。這趟旅行總共花去了近三千美元,他倆還從來沒有這麼大手大腳過。
七月十一日一大早,他們飛到了舊金山。沒想到天氣這麼涼,料峭晨風吹亂了行人的頭髮,弄得人睜不開眼睛。昨天夜裡下了暴雨,打得商店的招牌七零八落,濕淋淋的;有幾處的交通燈不靈光了,不停地亂閃一氣。不過,一些高樓黑玻璃磚的牆面,倒被洗刷得又乾淨又光亮,大海的氣息隨著風撲面而來。萍萍的衣著單薄,去旅館的一路上,禁不住渾身發抖,一個勁地打呃。武男在她後脖頸子上不停地按摩,想幫她緩解痙攣,還冷不防在她背上拍一下,想讓她驚一下子,把呃噎回去。這些土法子過去挺靈的,可今天都不管用了。
武男已經給聯合航空公司打過兩次電話了,想打聽清楚濤濤是不是真的上了飛機,可是都沒得到準信兒。人家祇是告訴他,電腦裡查不到那孩子的名字。中國那邊的情況仍然很亂,很多旅客從其它被取消的航班轉到這架飛機上來,所以一時還沒有一份全部旅客的名單。「不用擔心,武先生,」一個愉快的女聲安慰他說,「您的兒子應該一切平安。」
「我們聽說他就在『澤』(這)班飛機上。」武男往往發不好中文裡沒有的咬舌音,總把「th」發成「z」。
「那他就應該在這班飛機上。」
「你有沒有別的辦法查一查?」
「恐怕我沒有別的辦法,先生。我說過了,他應該沒事。」
可是,對於孩子的父母來說,「應該」和「就是」之間,卻是天差地別的懸念。要是他們知道兒子確確實實在哪裡就好了!
萍萍的哥哥在電話裡說,他把濤濤交給幾個美國乘務員了,其中一位是個亞裔,可以講幾句中文。現在武男夫婦惟有希望他確實在飛機上。
辦好入住登記三個鐘頭後,他們又乘旅館的公車返回機場。飛機要中午十二點半才會到達。因為那是國際航班,武男夫婦不能進去接人,祇能站在海關外邊,緊盯著那扇似乎永遠不會敞開的栗色大門。他們在問訊台問了好幾次,濤濤是不是在這班飛機上,可問訊台的人也說不準。一個瘦瘦的、穿著深藍制服的寬臉女子過來了,長得像個中國人,可是祇會說英語。懷著多一條途徑打聽到兒子下落的希望,他們去請這個女子幫忙。她短壯的臉僵硬起來,搖著頭說:「要是問訊台的小姐都幫不了你們,我也幫不了。」
萍萍急得發狂,用半通不通的英語懇求:「你請幫我們查一查。我們這麼就一個孩子,剛六歲。我三年沒見他了。」
「我說過了--我真的沒法幫你。我有我的工作,聽見沒有?」
武男也想懇求她,可那女子看上去很不耐煩,他就忍住了。她那眼睛裡,眼白多於眼黑,讓武男捕捉到一絲輕蔑。也許因為她知道他們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懷疑他們到現在內心還是赤色的,如果不說赤到骨頭裡的話。
他伸出一條胳臂攬住萍萍,小聲用中文說:「咱們再多等一會兒。我覺得他馬上就會出來了,現在還不用著急。」他們倆人之間都是說中文的。
他妻子懇求那女人的樣子讓他好生不快。萍萍三十三歲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差不多要年輕十歲,大眼睛,高鼻樑,精緻的下巴,體形很好。也許那女人是嫉妒她漂亮的面容,喜歡看到她著急痛苦。
那門終於開了,吐出了一行旅客。多數人都是一臉疲憊,目光呆滯,有幾個人走得趔趔趄趄的,拖著箱子或提包。武男夫婦倆向前又走近些,緊盯著出來的人們。旅客一個個走過。一個穿運動衫的高個子黑人叫起來:「嘿,托妮,見到你真高興!」他伸出右臂,左肩上挎著個深色帆布吉他箱。托妮,一個極瘦的戴著鼻環的姑娘,滿頭短辮子,把臉埋進他一條胳臂的擁抱。除了這個歡快的時刻,大多數旅客似乎都頭昏眼花,而且情緒低落。幾個亞洲人東張西望的,似乎不知道該往哪裡去,也弄不清站在兩邊的人們中間有誰是來接他們的。
五分鐘之內,所有的旅客都出關了,那大門又慢慢關上了。武男心頭一涼;萍萍哭出了聲:「他們一定是把他丟了!他們肯定把他丟了!」她嗚咽著,一條胳臂捂著肚子。她扯著武男的手腕,繼續哭:「我跟你說了不要讓他冒險,可你就是不聽。」
「他不會有事的,你聽我的。」他的聲音遲疑,連他自己都不相信。
大廳裡又安靜下來,幾乎空無一人。武男不知道該怎麼辦,對萍萍說:「咱們再等一會兒,好不好?」
「今天從中國來的就這一趟航班。你別騙我了!他根本沒在這班飛機上。哎呀,要是讓他等到有人可以帶他來就好了,不該著急呀。」
「是啊。」
這時門又開了。兩個乘務員走出來,高個金髮的那個牽著一個小男孩的手,另外一個身材苗條,笑眉笑眼的,提著一個小紅箱子。「濤濤!」萍萍喊起來,衝了過去。她一把把兒子拉到懷裡,在他的臉上親起來。「急死我們了!你沒事吧?」
孩子穿著一件水手衫,滿臉笑著,嘴裡嘟囔著「媽媽,媽媽」,一邊把臉貼在她胸前,好像因為被別人看著而害羞。然後他轉向武男,可他的表情卻是一副認不出來的樣子。
「這是爸爸,濤濤。」他媽媽告訴他。
因為沒有提前三個星期預訂,飛機票比正常價要高出七成,但是武男夫婦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祇要濤濤能盡快安全地離開中國,他們什麼代價也不惜。兩人又買了自己從波士頓飛舊金山的雙程票。
萍萍和武男都不能回中國去接濤濤,濤濤跟著外公外婆萍萍的父母過了三年了。萍萍娘家人誰也沒有護照,更別說從美國大使館得到簽證有多難了,這孩子祇能自個兒坐飛機到美國來。萍萍的哥哥是中學物理老師,正好放暑假回到父母家,他說可以把外甥從濟南送到上海,再把濤濤交給空中小姐。濤濤還不到六歲,沒大人陪著,不能一個人轉機,所以濤濤的爸媽一定得去舊金山接他。旅行社那個橄欖色皮膚、長頭髮大胸脯的女營業員,幫武男在聯合廣場附近的一家旅館訂了間最便宜的房間,一家三口在返回波士頓之前要在那裡住一夜。這趟旅行總共花去了近三千美元,他倆還從來沒有這麼大手大腳過。
七月十一日一大早,他們飛到了舊金山。沒想到天氣這麼涼,料峭晨風吹亂了行人的頭髮,弄得人睜不開眼睛。昨天夜裡下了暴雨,打得商店的招牌七零八落,濕淋淋的;有幾處的交通燈不靈光了,不停地亂閃一氣。不過,一些高樓黑玻璃磚的牆面,倒被洗刷得又乾淨又光亮,大海的氣息隨著風撲面而來。萍萍的衣著單薄,去旅館的一路上,禁不住渾身發抖,一個勁地打呃。武男在她後脖頸子上不停地按摩,想幫她緩解痙攣,還冷不防在她背上拍一下,想讓她驚一下子,把呃噎回去。這些土法子過去挺靈的,可今天都不管用了。
武男已經給聯合航空公司打過兩次電話了,想打聽清楚濤濤是不是真的上了飛機,可是都沒得到準信兒。人家祇是告訴他,電腦裡查不到那孩子的名字。中國那邊的情況仍然很亂,很多旅客從其它被取消的航班轉到這架飛機上來,所以一時還沒有一份全部旅客的名單。「不用擔心,武先生,」一個愉快的女聲安慰他說,「您的兒子應該一切平安。」
「我們聽說他就在『澤』(這)班飛機上。」武男往往發不好中文裡沒有的咬舌音,總把「th」發成「z」。
「那他就應該在這班飛機上。」
「你有沒有別的辦法查一查?」
「恐怕我沒有別的辦法,先生。我說過了,他應該沒事。」
可是,對於孩子的父母來說,「應該」和「就是」之間,卻是天差地別的懸念。要是他們知道兒子確確實實在哪裡就好了!
萍萍的哥哥在電話裡說,他把濤濤交給幾個美國乘務員了,其中一位是個亞裔,可以講幾句中文。現在武男夫婦惟有希望他確實在飛機上。
辦好入住登記三個鐘頭後,他們又乘旅館的公車返回機場。飛機要中午十二點半才會到達。因為那是國際航班,武男夫婦不能進去接人,祇能站在海關外邊,緊盯著那扇似乎永遠不會敞開的栗色大門。他們在問訊台問了好幾次,濤濤是不是在這班飛機上,可問訊台的人也說不準。一個瘦瘦的、穿著深藍制服的寬臉女子過來了,長得像個中國人,可是祇會說英語。懷著多一條途徑打聽到兒子下落的希望,他們去請這個女子幫忙。她短壯的臉僵硬起來,搖著頭說:「要是問訊台的小姐都幫不了你們,我也幫不了。」
萍萍急得發狂,用半通不通的英語懇求:「你請幫我們查一查。我們這麼就一個孩子,剛六歲。我三年沒見他了。」
「我說過了--我真的沒法幫你。我有我的工作,聽見沒有?」
武男也想懇求她,可那女子看上去很不耐煩,他就忍住了。她那眼睛裡,眼白多於眼黑,讓武男捕捉到一絲輕蔑。也許因為她知道他們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懷疑他們到現在內心還是赤色的,如果不說赤到骨頭裡的話。
他伸出一條胳臂攬住萍萍,小聲用中文說:「咱們再多等一會兒。我覺得他馬上就會出來了,現在還不用著急。」他們倆人之間都是說中文的。
他妻子懇求那女人的樣子讓他好生不快。萍萍三十三歲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差不多要年輕十歲,大眼睛,高鼻樑,精緻的下巴,體形很好。也許那女人是嫉妒她漂亮的面容,喜歡看到她著急痛苦。
那門終於開了,吐出了一行旅客。多數人都是一臉疲憊,目光呆滯,有幾個人走得趔趔趄趄的,拖著箱子或提包。武男夫婦倆向前又走近些,緊盯著出來的人們。旅客一個個走過。一個穿運動衫的高個子黑人叫起來:「嘿,托妮,見到你真高興!」他伸出右臂,左肩上挎著個深色帆布吉他箱。托妮,一個極瘦的戴著鼻環的姑娘,滿頭短辮子,把臉埋進他一條胳臂的擁抱。除了這個歡快的時刻,大多數旅客似乎都頭昏眼花,而且情緒低落。幾個亞洲人東張西望的,似乎不知道該往哪裡去,也弄不清站在兩邊的人們中間有誰是來接他們的。
五分鐘之內,所有的旅客都出關了,那大門又慢慢關上了。武男心頭一涼;萍萍哭出了聲:「他們一定是把他丟了!他們肯定把他丟了!」她嗚咽著,一條胳臂捂著肚子。她扯著武男的手腕,繼續哭:「我跟你說了不要讓他冒險,可你就是不聽。」
「他不會有事的,你聽我的。」他的聲音遲疑,連他自己都不相信。
大廳裡又安靜下來,幾乎空無一人。武男不知道該怎麼辦,對萍萍說:「咱們再等一會兒,好不好?」
「今天從中國來的就這一趟航班。你別騙我了!他根本沒在這班飛機上。哎呀,要是讓他等到有人可以帶他來就好了,不該著急呀。」
「是啊。」
這時門又開了。兩個乘務員走出來,高個金髮的那個牽著一個小男孩的手,另外一個身材苗條,笑眉笑眼的,提著一個小紅箱子。「濤濤!」萍萍喊起來,衝了過去。她一把把兒子拉到懷裡,在他的臉上親起來。「急死我們了!你沒事吧?」
孩子穿著一件水手衫,滿臉笑著,嘴裡嘟囔著「媽媽,媽媽」,一邊把臉貼在她胸前,好像因為被別人看著而害羞。然後他轉向武男,可他的表情卻是一副認不出來的樣子。
「這是爸爸,濤濤。」他媽媽告訴他。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二手書47折$210
-
二手書47折$210
-
二手書49折$220
-
新書79折$356
-
新書79折$356
-
新書79折$356
-
新書8折$360
-
新書85折$383
-
新書88折$396
-
新書9折$405
-
新書9折$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