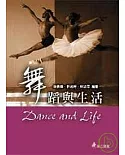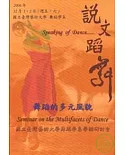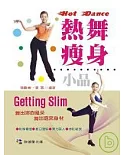序言 手舞足蹈面面觀
「無論是誰,不跳舞便不懂生命的方式」——西元二世紀基督教諾斯底教派的讚美詩如是說。古往今來,學習舞蹈、認識舞蹈,一直是人類認識和把握自身生命的最佳手段。
只要人類一息尚存,舞蹈作為一種最原初、最本能、最直接、最優雅、最有靈性、最有人性,同時也最具肉感和美感的「屬藝術」,便不會消亡,儘管作為其「種藝術」的民間舞、古典舞、現代舞、當代舞等屬於不同歷史時期產物的具體舞種,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遺傳變異、興衰枯榮。美國哲學家蘇珊?朗格(Susan Langer,
1895~1985)稱「舞蹈是一切藝術之母」;英國哲學家羅賓?科林伍德(Robin Geroge Collingwood)稱「舞蹈不僅是一切藝術之母,而且是一切語言之母」;中國文豪聞一多稱「舞是生命情調最直接、最實質、最強烈、最尖銳、最單純而又最充足的表現」,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從發生上看,人類早在對身外之物的聲音、形態、色澤、語言等多種符號形成規律性認識之前,便具有某種用動作直抒胸臆的本能,嬰兒在娘胎中的躁動和能說會道前的哭泣,便是最早的動作表情。而這一切,既是惟有母親才懂的語言,更是舞蹈發生的物質前提和觀眾理解的內在基礎;從廣義上說,就是最雛形的舞蹈。
從發展上看,舞蹈之所以成為人類物質與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因為作為對外界身心合一作出反應的藝術,它不僅能通過「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和「情動於中,故形於聲」(中國傳統樂舞思想中的「聲」和「樂」,均包括了舞蹈在內)的生成過程,表達人們此時此刻的思想感情,更能以藝術家特有的虔誠、超常的敏銳和無法扯謊的肢體(美國現代舞大師瑪莎?葛蘭姆的名言),真實而生動、直接或間接地反應當代生活的現實,甚至預示未來社會的發展走向,體現藝術應有的記錄歷史與預兆未來的雙重價值——民族矛盾白熱化時,它一馬當先,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踏著時代的脈搏而舞,為歷史留下血與火的腳印(如中國當代舞蹈泰斗吳曉邦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代表作《義勇軍進行曲》等);和平建設年代中,它則回歸自我,潛心探索自身的創作規律,推出心平氣和的純舞之作(如吳曉邦在和平年代創作的古曲新舞《梅花三弄》等),孕育通向未來的一代新風,真可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記》語),或者「有什麼樣的舞蹈,便有什麼樣的國王」(西方格言)。
從生理上看,人們不分老幼,均與生俱有視、聽、嗅、味、觸、動六種感覺,而在舞蹈表演與欣賞、傳播與溝通中,儘管視覺和聽覺不可或缺,眼睛的觸覺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觀賞性感而美妙人體的健康需要,但動覺確是更為重要的。所謂「動覺」,歸根結底,既是一種神經──肌肉系統的感覺,一種憑藉這種系統直接感受──反應的本能,也是一種在此基礎上保護自我──關愛他人的能力:生活中,當強者目睹弱者跌倒時,會不假思索地作出救助的動作,不經意中,流露出人類善良的本性;劇場裡,當舞者完成空轉後落地不穩,或單腳尖上平衡搖搖欲墜時,機能健全的觀眾會情不自禁地出現扶他(她)一把的衝動。對一個舞蹈,尤其是那些以肉體動作為主體,而未迷失在戲劇、文學和音樂泥淖中不可自拔的純舞蹈之理解,是否能當即觸發觀眾的動覺反應,而非是否能用文字語言翻譯清晰這種非文字語言,乃其「懂」與「不懂」的最直覺的裁判標準。正因為如此,觀眾才能在即使「不懂」的前提下,照樣明白自己是否對某個舞蹈情有獨鍾;正因為如此,舞蹈才能超越人種的差異和文化的限域,流芳千古,與世長存。
從心理上看,人們不分男女,均生而有之喜、怒、哀、懼、愛、惡、欲與生、死、耳、目、口、鼻這七情六欲,分別在暗處悄然發洩並在明處公然觀賞,可謂相得益彰的心理滿足乃至生理補償。「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這其中,無論是所謂的「瘋」,還是所謂的「傻」,表演者與觀賞者雙方得到心理的滿足和生理的補償,當是舞蹈最基本的功能,更是舞蹈宗教般魔力的源泉。正因為如此,舞蹈有史以來,從不缺心甘情願地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為其獻身的善男信女;正因為如此,舞蹈雖然長期缺乏便利的記錄工具,卻依舊能夠憑藉著口傳心授的方式傳延至今,並繼續存在下去。
從本質上看,舞蹈是一種既單純又複雜的藝術:單純到極限時,足以使你一眼見底,身心得到最大限度的放鬆和淨化;複雜到極端時,足以讓你陷入迷宮,眼花繚亂且邏輯不清。說它單純,是因為它是人類最清澄、最坦蕩的傳情達意手段;說它複雜,是因為它既能統一有形的肉體與無形的靈魂,又能協調無度的天然情欲與有節的道德倫理;既能高雅得令人肅然起敬,成為進入天國的禮儀規範,又能低俗得使人肉欲橫流,成為墮入地獄的魔鬼示範;既能用感情征服整個人類,又能用智慧表達人生哲理;既能折射人類發生發展史的整個歷程,又能凸顯不同歷史時期的時代特徵;既能通過感情宣洩排解心理疾患,又能通過肢體運動保全身體健康;既能強調群體生活的共同性,又能擴張個體生活的特異性;既能客觀地再現物質世界,又能主觀地表現精神世界;既能自由馳騁想像的無限空間,又能充分開發人體的有限結構;既能在國難當頭時為愛國主義的政治理想衝鋒陷陣,又能在國泰民安時使本體美學的純粹舞蹈興盛發展;既能充填生活與藝術的鴻溝,又能體現自然與舞蹈的區別;既能融合創作主體與創作物件,又能融合藝術家與藝術品;既存在於時間的節奏樣式之中,又存在於空間的造型樣式之中……。凡此種種,或許足以解釋,舞蹈理論緣何滯後於其他各門類藝術——它的複雜性恰好存在於它的綜合性之中。
從歷史上看,早在舞蹈成為一種高度發達的表演藝術之前,人們不分民族、膚色、宗教、語言,都能從左搖右擺、左旋右轉、騰空而起、跺地為節等動作中,自得其樂,發洩剩餘精力。當人們朦朧地意識到,動作乃宇宙間的萬事萬物莫不以運動為其主要存在和發展方式,便衍生出用舞蹈驅邪除疫、祈求平安、保證風調雨順、迎接五穀豐登的觀念和儀式。於是乎,舞蹈成為萬能之神:獵人出發前跳舞,勇士出征前跳舞,瘟疫橫行時跳舞,旱澇無常時跳舞,春播秋收時跳舞,出生成年時跳舞,婚喪喜慶時跳舞。舞蹈在先民的生活中可謂無處不在,更可謂神通廣大。
從宏觀上看,天上人間,氣象萬千,日月交替,鬥轉星移,江河奔流,潮漲潮落,四季迴圈,春華秋實,風吹草動,電閃雷鳴,運動不止,生命不息。這一切,便是舞蹈的底氣所在,便是舞蹈的能量所在,便是舞蹈的節律所在,便是舞蹈的美感所在。
從微觀上看,嬰兒從娘胎裡開始擁有規則的心跳,從落地後的第一聲啼哭開始有了正常的呼吸,這兩種最基本的、也是唯一貫穿生命全過程的動作,便是舞蹈舉手投足的動力,便是舞蹈俯仰向背的根基,便是舞蹈傳情達意的前提,便是舞蹈溝通你我的心渠。
這,就是本書即使竭盡全力,也只能描畫其萬分之一的不朽物件。這,就是異彩斑斕、風情萬種、變幻莫測、令人神往的世界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