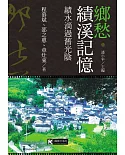是不為序 周棄子
我實在很不願意作序。因為平生東塗西抹,固然也糟蹋了不少筆墨紙張,但從來還沒有為人家的書作過序。現在快要到「焚筆硯」的時候了,八十歲學吹鼓手,不惟可笑,也屬多餘,以有涯逐無涯,大可不必。並且,序也不是人人能作的。依我揣想,大凡夠得上替人家作序的,其人必具相當「資格」。手頭一部《杜詩鏡銓》,翻開那篇序的末一行,就是「頭品頂戴總制四川使者盱眙吳棠序」,必如此,序者與被序者才都「像樣」。再不然,能夠在篇末帶上一筆「序於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之類的字樣,也可以使見者肅然。可惜的是,凡此等等我都辦不到。
在朋輩中,魯芹頗有懶散之名,他也顯然以此自負,曾經借用別人的話來描寫他自己:「什麼事都是『就要去做』;倒下頭來一事無成。」但事實上,他是不聲不響的在「做」,「有書為證」,怎麼可以說是「無成」呢?這就叫作「理想與實踐的不一致」,應該被「文學研究家」所瞧不起。也許正因為如此,作序的任務,乃落在「無成」如我者的頭上,這莫非就是所謂文字因緣麼?
書從雞尾酒命名,不僅開卷第一篇有此題目,大約也指其內容之雜湊,昔年俞平伯有書名「雜拌兒」,取義相同。雞尾酒因係多種羼合,甜酸苦辣的味道都有一點,所以難免於單調,但它的缺點就是「不純」,譬如書,如果是一本載道的偉大的著作,它的內容就一定要有「中心」,不可以紛歧錯雜。據聞,曾經有朋友依此觀點,建議把書名改一改,但不為作者所接受,他的理由是對這樣的一個書名有所偏愛,就憑這一點固執的性格,才會寫出這些篇大手筆所不屑的小文章吧。
說是小文章,當然略嫌不敬,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果如大手筆們所詔示,每一篇文章都得達成「偉大的使命」,那就非字字句句憂國憂民不可,依此標準,這一本裡恐怕沒有一篇是通得過的。試想,把跟小女兒打電話的情況以及隔壁人家的「竹戰」聲都寫出來,這真無法不認為是「身邊瑣事」之尤,其為渺小殆無疑義。不過,這世界上畢竟是渺小的人比偉大的人占多數,各取所需,小文章亦自有其讀者。而此中的是非得失,一時也未必說得清,或許是要「留待歷史判斷」的了。
如果不論大小只談優劣,則小文章要寫好亦非易事。誰沒有過「請客」和「說謊」的經驗呢?正因為這些題材太平常了,一切裝模作樣故示高深的文「法」,對此皆無從施展,「文藝腔」尤其行不通。這大概是要透過人性的理解、人生的觀照,調和智慧與情感,還得加上一點讀書行路的博聞多識,才會把這種文章寫得好。本書的作者並不自命已經達到這種境界,但是我相信如此說法並非溢美。
那麼,這種文章對於別人有什麼益處沒有呢?當然,類如廉頑立懦、福國利民那些妙用都是沒有的。不過我們讀了它,可以使得自己清醒一點、平靜一點。譬如我們聽到作者坦率自承是:「甘心落在『時代巨輪』後面吃灰塵的人」,也許會鬆一口氣,覺得人間落伍尚有同調,不必要抱太深重的罪惡感,也就毋庸勉強做種種努力。從遠處看,這也是頗有助於天下太平的。「以其無,當有之用」,如是而已。
作者的風格以幽默著稱,我對此不想加以禮讚。因為提到幽默,很多人以為只是說笑話。作者跟我一樣,既不敢開倒車,又無法飛躍邁進,顛頓於人生路上,徒然吃飽一肚子的時代灰塵,雖然現在大家都不穿長衫,但在「人物」類型上,總不出「小襟」一派,這還能夠有「幽默」的餘地麼?涉筆至此,越寫越不像序,只有趕緊結束,套一句濫調而略加變通—
是不為序。
丁酉(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初三日序於未埋庵
●本文作者周棄子先生,一九一一年生,一九八四年逝世。創作以舊詩為主,著有《未埋庵短書》、《周棄子先生集》。
前 記
本集共收散文十四篇。最早的一篇,係民國四十一年九、十月間所寫;最末一篇,寫於本年九月半。平均每年僅得萬餘字,寒酸極矣。
平心而論,就連萬餘字,也是意外之獲,得歸功或歸咎於編雜誌的幾位朋友。他們真是寧枉無縱,對一個與文字無甚淵源的人,亦不輕易放過。集中所輯,幾乎篇篇都是聶華苓、彭歌、夏濟安、徐訏諸先生催促下的急就章。其中且有雜誌已付排,尚缺頁數,臨時命題湊數者,質地低劣可知。我想在此對曾受我糟蹋過若干寶貴篇幅,現在又同意我彙印成冊的《自由中國》、《自由談》、《文學雜誌》、《論語》等刊物,敬致謝意。
取名「雞尾酒會」,一是因為斯篇乃集中最早寫的一篇;另一原因,乃是聽說雞尾酒係由威士忌或杜松子等酒加白糖、香料、苦酒、冰塊配成,是一種雜拌兒,與集中諸篇之內容蕪雜,頗為相稱。又據懂得酒的人說,此種酒,質地可以相差很遠,端視用的材料是否精純,調法是否得宜,此中高低,不啻霄壤,低的喝起來自然不十分夠勁;甚至於有人說可以歸入「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一類,這更是斯集諸文的最好註腳—當然下一句是對敝帚自珍的作者而言。
讀者到此,掩卷可也。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