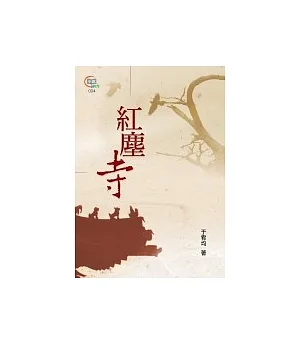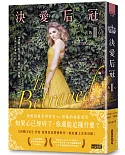後記or軌跡
我一直在寫小說,雖然一直沒機會出版。這同時,我也譯了幾本小說。
不管是寫的、譯的,只要出自我的文字,我都覺得是我的孩子。
我總跟友人打趣說,是我的孩子我都疼,雖然自己創作的,是自己生的,譯出來的,是領養的。
友人往往笑答,是啊!創作就跟生孩子一樣,不容易呀!
對我而言,《紅塵寺》又尤其不易,因為我從二○○三年就開始孕育他,好幾次差點流產,身心受盡創痛,直到二○○六年,這才終於讓他順利來到人間。
二○○二年,我的人生跌到谷底。當時,我剛寫完了一本沒人願意出版的小說,英文教學的工作因學校政策而崎嶇,內心深處被寂寞啃蝕得滿目瘡痍。我強迫自己降低慾求,以為這樣或能擺脫佛家所謂的四苦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蘊盛苦。但我困惑依舊,找不到出路。於是我決定,我要再開始寫一部小說,即便這很可能又是一部只能存放在我電腦裡的小說,但是透過書寫,我或有希望一點一滴撥開人生的霧瘴。
二○○二?二○○三跨年那晚,一名女性友人收到的簡訊震撼了我,就在那一天,「紅塵寺」進入了我的生命。那一則簡訊是寺裡一位女師父發給她的,女師父身在寺中,卻毫不掩飾的釋放自己的愛戀與掛念,而我這個紅塵中人,卻拚命地壓抑自己的慾念。「紅塵寺」這個名字來到我心中,我知道,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著手的小說了。我要在「紅塵寺」裡寫人生的似是而非、寫人生的執著與苦惱、寫悲歡離合、寫愛恨情仇,但我不敢貿然去寫,因為這些題目都太龐大。我陸續構思人物、故事、章節,半年過去了,我不斷地構思,就是沒動筆的勇氣。
二○○三年下半年,我在學校開了一門通識課程「小說研究」。我要求學生自訂主題,交出「人物」、「故事」、「情節」,好幾次,為了解答學生的疑慮,我以「紅塵寺」為例解說,教學相長,這幫我更確立了人物、故事的走向。這段期間,我也讀了柯慈的「《屈辱》」,深化了我想表達的意念。
轉眼一年過去,二○○四年的新年,我的筆蠢蠢欲動,終於開筆寫第一章,一路寫到第四章時,卻遇著瓶頸不知該怎麼寫下去。很巧、很幸運的,九歌新人計畫在這年九月開跑,我於是寄去了完成的前三章,一邊等候消息,一邊整理自己紊亂的思緒。
然後又是新的一年,二○○五年一月,彷彿「紅塵寺」的寫照,悲喜在我的人生裡交替。九歌馬大文小姐來電,請我一月七日前去面談,我欣喜若狂,買好車票後,撥了通電話到老朋友光的家裡。和光相識十六年,我們已多年不見。我一廂情願地盤算著在九歌面談之後,約他喝個咖啡,和他分享小說入選的喜悅。怎料到,這一通電話,卻讓我得知了他家人原不打算讓我知道的死訊。在大陸工作的他,已於十二月中旬,死於一場意外。一月七日忍著眼淚到九歌面談之後,我照著原訂計畫和他見面。我在細雨綿綿中,帶了束鮮花,坐計程車上金寶山去看他,沒有咖啡,只有我一個人演獨角戲似的說了一個半鐘頭的話。
回到宜蘭,我知道「紅塵寺」勢必要重寫,可一坐到桌前,就不停掉淚。最後我只好一邊哭、一邊寫,直到五月把重寫的前三章交給九歌,不得不暫先停筆。也不知為什麼,筆一停下,眼淚也就漸漸停下,那幾個月,我沒再動筆,大多時間待在家裡擦油漆、打鼓、陪兒子看許多卡通,直到九月,當我漸漸走出悲傷,素芳總編來了一封催促的信,終於,我再次執筆,再次重修。
二○○六年四月三日近午,當我不知不覺打下了「孤寂的真相」,發了好一會兒呆,這才發現小說居然已走到終點。接下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希望《紅塵寺》能以最好的面貌面世。感謝支持我的親友,更感謝九歌、感謝素芳總編,除了一再說謝謝,愚鈍的我實在不知自己還能如何表達心中的感謝。我知道,若沒有九歌,《紅塵寺》這部小說不但無法出版,恐怕就連完成都遙遙無期。
活在這個世間,我常有個感覺,覺得就在宇宙的什麼地方,好像有個人(或神?),他每天不停地在寫小說,而他筆下的人物,就是活在世間的我們。
李安說,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
我說,我們都住在紅塵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