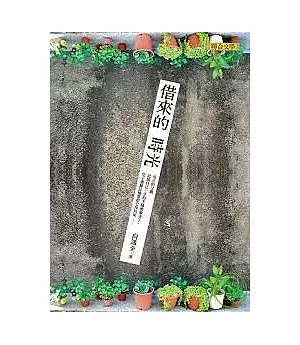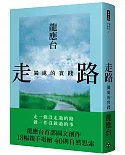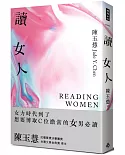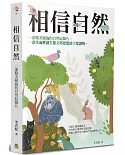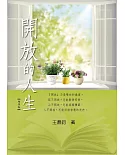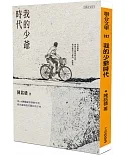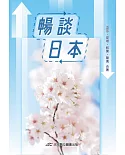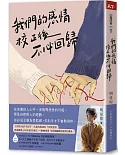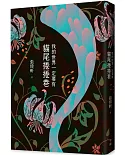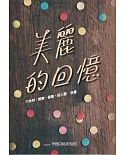【推薦序】
典雅、溫潤與寬容
——向鴻全散文《借來的時光》
郝譽翔
散文是最容易親近,但也是最難以掌握的一種文類。它易寫,但難工。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人人皆可以執筆為之,大自國族興衰的歷史大事,親人之間的生離死別,小至生活之中的花草蟲魚,柴米油鹽,無一不可入文。然而,散文越是如此的無所不包、漫無邊際,就越是令人難以去追索章法,別出新裁。
於是傳統的散文,走的多半是抒情美文的路線,著力在詞藻的華麗之上,努力透過文字,欲將情感渲染到唯美極致,傷春悲秋,末了卻往往不免要流於誇飾和空洞之弊。也因此,近二十年來台灣的散文,已經揚棄抒情美文的路線了,不再力求字斟句酌,雕琢詞彙,而要改以明快清楚的語句,書寫某一種主題類型:譬如音樂散文、醫藥散文、飲食散文、旅行散文、自然散文等等,而如此一來,散文寫作也儼然邁入了專業的範疇。這使得散文不再是無所不包了,更不再是訴諸一般所有的讀者,而是進入到一個知識化、分眾化、專門化的新階段。
然而,當我讀多了近年來高度知性化、專業化的散文,再讀到向鴻全的這本《借來的時光》時,卻不免要油然升起一股懷舊的溫馨感。向鴻全出身中文系,對於科幻小說不僅廣泛閱讀,還有深入的研究,但奇怪的是,在他的散文中卻似乎嗅不出一點科幻氣息,反倒是瀰漫著一股老派中文人的韻味,沈穩、紮實、不疾不徐,不炫耀,也不誇弄。因此,在散文已然越趨知性與分眾的今天,向鴻全的《借來的時光》便顯得十分的特別了,它寫的多是一己的小事,卻能在這一己的小小方圓之內,自滿又自足,開啟了一片靜謐的天地。也因此,它適合現代所有的讀者,在忙碌一天之餘,坐在燈下,手握一杯溫茶,展開書頁,靜下心去慢慢的品嚐。
?
?父親,是向鴻全反覆書寫的重要主題,而在《借來的時光》中,我們也讀到了憲兵出身的外省籍父親,如何給予他嚴謹的家教,讓他成長、啟蒙,並認識台灣這一段複雜的歷史與族群遷徙。不過,向鴻全並不隨意譴責那個族群,也不故作新新人類的張揚姿態,更沒有百科全書式的炫學焦慮,他只是出之以中文系的修養和他的家教,一貫採取溫潤寬容的語調,平靜宛如緩緩流水,出入於回憶之間,敘述他所曾經親眼目睹與感受到的一切。
在充滿政治激情、喧鬧不休的台灣,或許我們更需要的,正是他這一種老派的家教、風範與涵養吧,不慍不火,才能夠靜靜的穿越了時間的考驗,穿越了族群與語言之間的障礙,並從而找到了一種平心靜氣的態度,繼續生活在這座美麗的島嶼之上—一座從消失的時光中,重新找回來的美麗的福爾摩沙。
【作者序】
收在這本集子裡的作品,大多都是紀錄關於我父親和屬於他的那個世代的故事。或許是因為成長經驗的關係,從我開始嘗試寫作以來,環繞著父親所開展的想像,就變成是我寫作的重心;從原本可能是習作的對象,到後來變成自我生命的挖掘和叩問的無盡藏,到最後我忽然發現,父親竟然在我不斷摹寫中成為一則寓言。每當我重新懷想父親的種種行止,我似乎都能夠從中體會到和我自己的某種奇異預視或連結,因此每每恍然大悟於這種如孔子所說「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的永恆關聯。
當我幾乎就要掌握到許多問題的答案時,父親突然就倒下了;以致於所有可能的答案遂又變成另一個更大更難解的疑問。父親曾經親手撰寫一本自傳,藍色的封面,內裡是多孔的活頁紙,而穿繫過活頁孔洞的是類似皮鞋的黑色鞋帶,因此孔洞的邊緣多充滿破損的痕跡。父親學歷不高,但寫得一手好字,尤其字力穿透紙背,我經常撫摸那崎嶇不平的紙面,揣想那每一筆每一劃背後的心情;然而在父親過世不久的某一天清晨,我停放在家門外的車子被人撬開,拿走車內所有物件,我才發現父親的自傳竟也被人偷走,我自責不已但又無能為力,我遍尋不找後哭喊地說,為什麼連這個也要取走?傷心懊悔之餘,遂動起想藉由重新整理父親一生經歷,來重建那本自傳。
在回憶重寫的過程裡,我經常分不清那些是我自己的回憶,那些又是父親曾經告訴我的事情;我經常在書寫時不慎遺漏了關鍵的名字、或關鍵的情節後,突然又在某一天想起那個關鍵的名字或情節。恨自己記得太少,卻又忘得太多。那些與父親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竟然都是我現在最珍貴的記憶。我不想忘記也不要忘記......。
在電影《大魚老爸》(Big Fish)裡,有一個極善於說故事的父親,他的一生精彩如編造虛構一般,讓他的兒子總是覺得自己的父親不夠誠懇,直到父親離開,他才發現父親過去和他說的都是真的──那些奇幻的冒險歷程、不同於凡人的朋友,後來都出現在眼前。我的父親不是那麼善於說故事,但我相信他一定會很樂意聽他的兒子重新訴說他的故事。
感謝在寫作的路上不斷鼓勵我的李瑞騰老師、焦桐老師、李宜涯老師,還有聯合文學的悔之總編和編輯們溫暖慷慨的支持及協助。